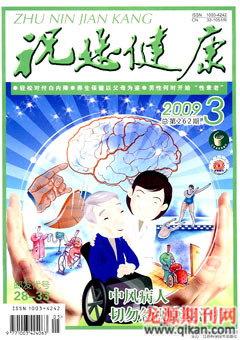我和你
2009-04-08 09:36:06李良旭
祝您健康 2009年3期
關鍵詞:人性
李良旭
我和你,多么溫暖,多么濕潤,感動得讓人眼睛里含滿婆娑淚光。塵世間,我們踽踽前行,茫然四顧,亦步亦趨。但是,我和你,這里面似乎有一種強大的力量。我們每一個人都不是獨立存在的生命個體。
每一個人,在某一時刻、某一階段,總是會要與生命中的某一個人、某一些人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冥冥之中,這種聯(lián)系和磁場,不僅是一種巧合,更是一種緣分。有了我和你,生命將更加雋永綿長,熠熠生輝。就是再卑微的生命,有了我和你,也會勇往直前不會言棄。這是一種真正的力量和強大。
腦海里,常常想起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那首奧運會主題歌——《我和你》。
歌聲以舒緩而溫情的方式,閃耀著人性與情義的光芒,使人如同沐浴在月光的清幽與浪漫中,在天籟之音中感受“地球村”的和諧之美。
有了我和你的理念,地球人就會心手相連,共浴和諧,演繹出“和平、友誼、團結”的精髓。我和你,彰顯出無窮的生命力和人性的光輝。
我和你,多么美麗;我和你,多么雋永;我和你,多么溫暖。那是一種最美的人生體驗和精彩,那是一種最美的心手相連,那是一種最美的愉悅和享受。生命中,有了我和你,就會奏響起最美的生命樂章,顯得格外溫暖和浪漫。
恍惚間,就有了一種天長地久的感動和穿越……
猜你喜歡
雜文月刊(2021年11期)2021-01-07 02:48:01
阿來研究(2020年1期)2020-10-28 08:10:14
攝影與攝像(2020年12期)2020-09-10 07:22:44
文苑(2019年24期)2020-01-06 12:06:58
新產經(2018年3期)2018-12-27 11:14:16
海峽姐妹(2018年4期)2018-05-19 02:12:54
影視與戲劇評論(2016年0期)2016-11-23 05:26:47
工業(yè)設計(2016年10期)2016-04-16 02:44:06
人間(2015年17期)2015-12-30 03:41:08
陜西教育·高教版(2015年8期)2015-02-28 15:0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