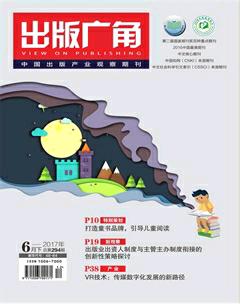1949年以來澳大利亞重要作家作品的漢譯與出版回顧
【摘 要】 澳大利亞文學在其四個發(fā)展階段分別出現(xiàn)了具有時代特色的代表性作家和經典作品。1949年后,我國的翻譯界、出版界對澳大利亞文學的譯介經歷了三個時期。這三個時期,我國出版了澳大利亞文學史上不同類型作家的代表性著作,每個時期的譯介作品依據時代發(fā)展主題、文學發(fā)展需要、讀者審美取向等,有不同的側重。
【關 鍵 詞】澳大利亞;英語文學;重要作家;漢譯;出版
【作者單位】程珊珊,南陽理工學院。
20世紀以來,澳大利亞作家多次獲得世界性文學大獎,澳大利亞文學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在澳大利亞文學欣欣向榮的背景下,澳大利亞的國家形象、文化形象、社會形象通過文學作品走出國門、走向世界。我國文化界在20世紀尤其是1949年以來,開始翻譯和出版澳大利亞文學,經歷了從無到有、由單一到多元、由表象到深層的譯介過程,使澳大利亞文學成為我國翻譯文學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澳大利亞文學分期及各個時期的代表性作家
從1788年英國移民和流放犯登上澳大利亞大陸開始,澳大利亞正式進入有文字記載的文明階段,澳大利亞文學也開始起步。在1788年到1888年這百年期間,澳大利亞處于殖民時期。這100年的前50年里,澳大利亞文學多為游記和故事,主要表達思鄉(xiāng)之情和介紹風土人情,因此從嚴格意義上說還不算文學,也沒涌現(xiàn)出可以載入文學史冊的作家。后50年期間,澳大利亞金礦的發(fā)現(xiàn)促進了當地經濟的繁榮發(fā)展,澳大利亞移民文學隨之誕生,作品主要由移民創(chuàng)作,反映移民在新大陸艱難的謀生與定居經歷。小說主要師法英國作家司各特,詩歌則效仿拜倫、雪萊、華茲華斯等詩人。殖民文學的代表作家有小說作家亨利·金斯利、羅爾夫·博爾特沃德和馬庫斯·克拉克,代表詩人有亞當·戈登、亨利·肯德爾和查爾斯·哈珀等。
從1889年開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前,澳大利亞進入民族主義運動時期,國家和民族的獨立要求文學服務于這一主題,于是澳大利亞民族文學應運而生。由于整個民族的使命在于擺脫英國殖民統(tǒng)治,建立獨立國家,因此文學上特別強調民族特色,弱化英國文學的傳統(tǒng)特色。這一時期的澳大利亞民族文學作品注重刻畫澳大利亞開拓者們的頑強性格,描寫澳大利亞生氣勃勃的景象,塑造各種具有澳大利亞氣質的人物形象,同時還注重表現(xiàn)民族獨立時代特別需要的“伙伴情誼”。在文學藝術形式上,民族作家們開創(chuàng)了具有澳大利亞特色的現(xiàn)實主義文學,開始走出模仿英國文學的套路,吸收澳大利亞民間叢林故事的各種藝術手法和形式。因此,澳大利亞文學正式誕生。短篇小說巨匠亨利·勞森就出現(xiàn)在這一時期,另外,約瑟夫·弗爾菲、邁爾斯·弗蘭克林、斯蒂爾·拉德、路易斯·斯通、亨利·理查遜也是同時期的著名小說作家。
從“一戰(zhàn)”開始到“二戰(zhàn)”結束這一時期,澳大利亞基本獲得了獨立,成為英聯(lián)邦的一個獨立國家。這一時期,澳大利亞文學走向成熟,其在風格上繼續(xù)沿襲現(xiàn)實主義,長篇小說開始繁榮,作品的視野更為廣闊,開始關注社會不平等和土著人受壓迫的現(xiàn)象。同時,一部分作家借鑒歐洲的自然主義和歐美的現(xiàn)代主義,為澳大利亞文學在現(xiàn)實主義之外開辟了新的文學道路。這一階段,主要作家有克里斯蒂娜·斯特德、亨利·理查遜、蘇姍娜·普里查德、萬斯·帕爾默、澤維爾·赫伯特等。
從“二戰(zhàn)”后至今,澳大利亞進入和平發(fā)展歷史新時期。這一時期,澳大利亞文學進入全面發(fā)展階段,各種派別爭奇斗艷,向澳大利亞甚至世界其他國家提供了不同類型的文學作品,而且佳作頻出。現(xiàn)實主義流派和“新派創(chuàng)作”是這一時期較為重要的文學派別。尤其是“新派創(chuàng)作”,這一派別力求敘事方式、敘事角度和敘事語氣的革新,積極采用拉美的超現(xiàn)實主義文學表現(xiàn)手法,把夢幻與現(xiàn)實緊密結合起來,大膽地描寫性、毒品等傳統(tǒng)文學嚴禁的題材。隨著澳大利亞作家帕特里克·懷特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澳大利亞文學開始走進全球視野。懷特引進并發(fā)展了歐美的現(xiàn)代主義,在澳大利亞文藝界掀起了一場藝術革命,改變了現(xiàn)實主義文學在澳大利亞獨霸天下的格局。在懷特的影響下,產生了一批優(yōu)秀的作家,比如倫道夫·斯托、托馬斯·基尼利和哈爾·波特等,他們的風格接近懷特,被稱為懷特派。新派小說家主要有弗蘭克·穆爾豪斯、邁克爾·懷爾丁、彼得·凱里和默里·貝爾等。澳大利亞當代現(xiàn)實主義作家的代表有馬丁·博伊德、艾倫·馬歇爾、佛朗克·哈代等。另外,20世紀七八十年代涌現(xiàn)出一批年輕作家,比如考琳·麥卡洛、戴維·馬洛夫、伊麗莎白·喬利、海倫·加納、蒂姆·溫頓和布蘭奇·達爾普蓋特等。
二、1949年后不同時期,我國對澳大利亞重要作家的譯介和出版
由于澳大利亞民族文學起步較晚,加之清末以來中國翻譯外國文學的重點在歐、美、日等國的作品,所以直到1949年后,中國才真正開始譯介和出版澳大利亞文學。國內知名澳大利亞文學研究專家彭青龍研究發(fā)現(xiàn),我國的澳大利亞文學譯介與研究可分為解凍(1949—1978)、起步 (1979—1988)、發(fā)展(1989—1998)和繁榮(1999至今)四個階段[1]。本文結合彭青龍的分期,從“1949年到‘文革結束”“‘文革結束到20世紀80年代末”“20世紀90年代到目前”三個階段回顧我國對澳大利亞重要作家及其作品的譯介和出版歷程。
1.1949年到“文革”結束:澳大利亞左翼作家及作品率先走進中國
1949年以前,我國學界和翻譯界幾乎沒有對澳大利亞文學的譯介,清末以來我國譯介的對象主要是歐美日文學,加上當時澳大利亞文學在世界文學格局中的地位不高,即使在西方國家,澳大利亞文學的譯介也很少。1949年到“文革”結束的近30年時間里,由于意識形態(tài)的需要,我國對國外文學的譯介側重于揭露資本主義罪惡、反映工人生活和民族運動等內容,因此澳大利亞的一批左翼作家率先進入中國學界和翻譯界的視野。1953年,上海出版公司出版了由劉芃如等翻譯的詹姆斯·阿爾德里奇的長篇小說《外交家》。阿爾德里奇曾獲列寧和平獎,因此進入中國學者的視線,這也是我國翻譯出版的首部澳大利亞文學作品。之后幾年,作為澳大利亞左翼作家的代表性人物,阿爾德里奇的另4部作品也被翻譯出版,分別是1955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海鷹》、1958 年新文藝出版社出版的《獵人》、1959 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光榮的戰(zhàn)斗》和《荒漠英雄》。
同時期中國重點譯介的另一位澳大利亞知名作家是弗蘭克·哈代。哈代曾加入澳大利亞共產黨,是一位在政治上較激進的左翼作家。1954年,哈代訪問蘇聯(lián)后寫的游記《幸福的明天:蘇游紀行》經于樹生翻譯由上海文藝聯(lián)合出版社出版。同年,他描寫澳大利亞政界權金交易黑幕的長篇小說《不光榮的權力》則由葉封、朱惠合譯,在上海新文藝出版社出版。1959年,由李名玉翻譯的哈代中篇小說集《我們的道路》在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發(fā)行,該社在1962年還出版了由朱惠等翻譯的哈代長篇小說《賽馬彩票:外六篇》。
這一時期,除阿爾德里奇和哈代之外,我國翻譯界翻譯較多的澳大利亞作家還有維爾福雷德·貝卻敵。1956年,貝卻敵的戲劇作品《變動中的潮流》由新文藝出版社出版;同年,世界知識出版社還出版了貝卻敵反映越南抗法戰(zhàn)爭的紀實報告文學作品《十七度線以北》;兩年后,該社又出版了貝卻敵采訪柬埔寨和老撾的紀實游記作品《沿湄公河而上》。還有一位不得不提的作家是第一位獲得國際聲譽的澳大利亞女作家凱瑟琳·普里查德,她是澳大利亞共產黨創(chuàng)始人,同時也是和平主義者,是20世紀20年代至50年代澳大利亞文學的中心人物。她創(chuàng)作的描寫金礦工人生活的《沸騰的九十年代》1959 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60 年,澳大利亞短篇小說巨匠亨利·勞森的《把帽子傳一傳》經著名翻譯家袁可嘉翻譯并由新文藝出版社出版,這是這位澳大利亞文學史上的經典作家首次走進中國。1949年到“文革”結束這一時期我國譯介和出版的澳大利亞重要作家除去亨利·勞森屬于民族運動時期的已故作家外,其他都是在世老作家或中青年作家。
2.“文革”結束到20世紀80年代末:各時期經典作家與流行作家作品的同步譯介
從1966年開始,由于“文革”的爆發(fā),我國的國外文學翻譯基本停止。“文革”結束到20世紀80年代末,我國的外國文學譯介和出版迎來了春天,澳大利亞文學的譯介也進入繁榮時期。1978年,由劉壽康等翻譯的《勞森短篇小說集》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這一時期的澳大利亞文學譯介不再受意識形態(tài)影響,既譯介現(xiàn)代的實驗文學和通俗的暢銷作品,也譯介如勞森這樣的傳統(tǒng)經典作家的作品。
在澳大利亞傳統(tǒng)經典作家的譯介方面,澳大利亞殖民主義后50年的重要作家馬庫斯·克拉克最著名的作品《無期徒刑》由陳正發(fā)和馬祖毅合譯,1985 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該小說通過講述無辜青年被流放到澳大利亞后所受的虐待,抨擊了澳大利亞早期流放制度的殘酷。這部澳大利亞文學史上的經典小說受到了中國讀者的歡迎,21世紀以來有4篇學術論文和1篇碩士論文對其進行解讀,這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它的經典性。另一部被譯介的經典作品是邁爾斯·弗蘭克林的《我的光輝生涯》,這部被譽為“第一部澳大利亞小說”的作品由黃源深等人翻譯,1989年在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2007年又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再版,其經典性和受歡迎程度由此可見一斑。20世紀三四十年代就已出名、1973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澳大利亞知名作家帕特里克·懷特及其作品由于“文革”等歷史因素,直到1986年才為中國讀者所知,其作品《風暴眼》由朱炯強等翻譯、由漓江出版社出版,此后多次再版并被不同譯者翻譯出版。從此,懷特的作品陸續(xù)被譯介到中國,其也成為在中國文學界知名度和《荊棘鳥》作者考琳·麥卡洛差不多的澳大利亞作家。1987年,“澳大利亞的第一部經典劇作”、杰克·希伯德的《想入非非》經胡文仲翻譯,在《外國文學》第8期發(fā)表。
1983年,澳大利亞文學作品中暢銷世界的長篇小說《荊棘鳥》被曉明等翻譯,由漓江出版社出版。《荊棘鳥》被譽為“澳大利亞的《飄》”,該書此后在中國出現(xiàn)多個譯本,小說“有關夢想、掙扎、郁積于胸的熱望和禁愛的家世傳奇故事”吸引了一代代中國讀者。其作者考琳·麥卡洛因為這部作品為中國文學愛好者熟悉。至此,澳大利亞的年輕作家及其作品也開始走進中國。20世紀80年代,澳大利亞文學在中國譯介史上具有重要價值的事件是《澳大利亞文學作品選讀》的出版,該書由我國澳大利亞文學研究專家黃源深編選,1986年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澳大利亞文學權威里奧尼·克拉默教授認為作者“是一位非常可靠的澳大利亞文學向導,他把主要作家都選入了書內”[2]。可以說,20世紀80年代,澳大利亞各個流派的主要作家及其作品被我國翻譯界通過代表性著作、摘譯、作品選讀等形式譯介過來。
3.20世紀90年代到目前:當代知名作家的全面譯介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外國文學譯介已經從意識形態(tài)和現(xiàn)代主義的框架中走出,開始全面譯介各國優(yōu)秀作品。澳大利亞文學在新時期的譯介既考慮文學傳統(tǒng)因素,又考慮最新文學流派因素,還考慮市場和讀者因素,因此,新時期的澳大利亞文學翻譯和出版就更為開放和多元。
懷特作為澳大利亞文學史上的“高峰”,其關注現(xiàn)代人精神危機的文學主題契合了轉型期中國人的精神和信仰現(xiàn)狀,因此其作品在中國的市場很大。20多年來,懷特的作品陸續(xù)被翻譯出版。1992年,懷特的中篇小說《死去的玫瑰》被中國文聯(lián)出版公司的“二十世紀外國中篇小說精選”叢書收入“亞·非·澳卷”中出版。1998年,懷特的回憶錄《鏡中瑕疵: 我的自畫像》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出版。同時期,《探險家沃斯》《人樹》《艾倫》《樹葉裙》《乘戰(zhàn)車的人》《歡樂谷》等作品也被翻譯出版,其中《風暴眼》《探險家沃斯》《人樹》《鏡中瑕疵: 我的自畫像》有兩次及以上再版的經歷。
隨著后現(xiàn)代主義被中國學界和翻譯界接受,澳大利亞的后現(xiàn)代文學成為新時期中國翻譯出版界的重點。70年代的“新寫作”、80年代的“新小說”以及90年代 的 “后現(xiàn)代文學小說”形成了澳大利亞獨有的后現(xiàn)代小說風貌,我國新時期譯介的重要作家也基本屬于這個范疇[3]。出生于1943年的當代作家彼得·凱里是澳大利亞“新派小說家”中最富有獨創(chuàng)性、最有才華的作家之一,也是新時期我國譯介的重要澳大利亞作家。1998年,重慶出版社出版了由曲衛(wèi)國翻譯的凱里最知名的小說《奧斯卡和露辛達》,人民文學出版社分別于2004年和2008年出版了凱里的《凱利幫真史》和《偷竊》。2010年后,凱里的《亡命天涯》《杰克·邁格斯》《主仆美國歷險記》《赫伯特的奇幻人生》分別出版。2017年,上海譯文出版社策劃了“彼得·凱里作品”叢書,于2017年2月出版了凱里的《眼淚的化學》和《偷香竊愛:一個愛情故事》,這是凱里的文學作品在中國傳播進程中的一個重要出版事件,也是我國出版界首次為澳大利亞作家策劃個人叢書。
在出版作家個人叢書前,我國出版界已為澳大利亞文學翻譯作品策劃了兩套叢書,囊括了澳大利亞當代文學界的主要作家及其代表作。第一套是由重慶出版社策劃的“澳大利亞文學作品選”,這套叢書從1995年開始,先后出版了7部作品,其中包括彼得·凱里的《奧斯卡和露辛達》、尼古拉斯·周思的《守望者》、羅斯·茲維的《納瑞斯金公園最后的散步》、吉姆·斯科特的《心中的明天》等,這些作者都是活躍在當代澳大利亞文壇的知名作家。第二套是2010年由上海譯文出版社策劃的“當代澳大利亞小說譯叢”,叢書共10冊,其中就包括彼得·凱里的《杰克·邁格斯》,其他作家有弗蘭克·穆爾豪斯、伊麗莎白·喬利、布賴恩·卡斯特羅、托馬斯·基尼利等,這些作家大多數獲得過澳大利亞最高文學獎——邁爾斯·弗蘭克林獎,彼得·凱里和托馬斯·基尼利還獲得過布克獎,后者的成名作是《辛德勒名單》。可以說,后一套叢書囊括的作家都是澳大利亞當代文壇的頂尖作家,代表了當代澳大利亞文學的最高水平。進入21世紀,我國翻譯和出版界開始系統(tǒng)地譯介澳大利亞文學史經典作家的經典著作和當代文壇代表性人物的知名著作,為讀者和研究者提供了優(yōu)質的澳大利亞文學文本。
三、結語
60多年來,不同時期我國翻譯界依據時代發(fā)展主題、我國文學發(fā)展需要、讀者審美取向、市場需求等,譯介了一批澳大利亞作家作品,呈現(xiàn)出較為明顯的時代特征。今后,我國一方面應該加強對澳大利亞詩歌和散文的譯介,使澳大利亞代表性詩人、散文家的作品能及時與我國讀者見面;另一方面,應在目前的基礎上以全集、文集、作品集等形式系統(tǒng)地譯介和出版澳大利亞文學史上經典作家、代表性作家的作品,使澳大利亞文學能為我國的文學發(fā)展提供更為全面和系統(tǒng)的參考。
|參考文獻|
[1]彭青龍. 學術史視閾下澳大利亞文學翻譯述評(1949—1978)[J]. 中國翻譯,2014(6).
[2]黃源深. 澳大利亞文學作品選讀[M]. 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7.
[3]王臘寶. 澳大利亞后現(xiàn)代小說述略[J]. 外國文學,20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