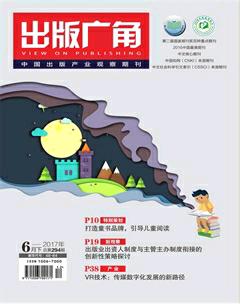《薛定諤之貓》的譯介與出版價值評析
【摘 要】 《薛定諤之貓》于2013年在法國伽里瑪出版社出版,2014年被譯介到中國,是法國當代作家菲利普·福雷斯特在中國出版的第四部小說。文章立足于主題學和敘事學,旨在從文學、文化、社會三個方面探討《薛定諤之貓》的譯介與出版價值。一方面,小說將量子力學的概念融入文學創作中,使讀者產生了“陌生化”的閱讀體驗;另一方面,文中隨處可見的中國元素表現出一個法國作家的中國幻象;此外,小說對新物理學背景下人類的身份以及生存意義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對讀者有深刻的啟發意義。
【關 鍵 詞】陌生化;中國幻象;混沌;出版價值
【作者單位】焦君怡,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沈陽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
小說《薛定諤之貓》從量子力學的薛定諤實驗開始寫起,將多條線索根植在敘事之中:在現實層面上,主要圍繞第一人的稱敘述者在鄉間別墅度假期間遇見、收養并最終失去一只貓的故事情節展開;在回憶層面上,摻雜了敘述者童年生活的碎片化記憶,以及痛失愛女的個人創傷;在夢境層面上,再現了敘述者過去生活的影像以及一個陌生人的夢境;在幻想層面上,混合了假想的中國寓言,薛定諤、艾弗雷特生前的生活片段,以及量子力學諸多概念的隱喻性描述。
在這部小說中,作者菲利普·福雷斯特延續了他的“自撰式寫作”,將個人經歷與寓言想象、科學幻想結合在一起,在虛構與非虛構之間完成了故事的講述和個人情感的抒發,并且在更為廣袤的宇宙中,實現了對人類身份問題的又一次探討。
一、文學價值——“陌生化”的小說
俄國文藝理論家什克洛夫斯基在《作為技法的藝術》中提出了“陌生化”的概念,指出藝術的存在就是“為了使人能夠恢復對生活的感知,為了讓人感覺事物,使石頭具有石頭的質地”;藝術的技法是“使事物‘陌生化,使形式變得困難,加大感知的難度和長度,因為感知過程就是審美目的,必須把它延長”。
在《薛定諤之貓》中,作者將量子力學的諸多概念植入了文學創作,使文學與科學相互交融。值得注意的是,這種交融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科幻小說,而是在一個新的維度為讀者帶來了顛覆性的閱讀體驗。此外,從小說的敘事角度看,小說的情節發展不再遵循傳統的線性時間邏輯,而是多條線索并置在一起,故事在表面破碎的敘述中逐步展開,空間取代了時間,為小說增添了立體感;從小說的表達方式上看,相對于傳統小說,《薛定諤之貓》的敘事性趨于弱化,語言具有詩化和散文化的傾向,這也為小說增添了“陌生化”的效果。
1.量子力學的文學演繹
《薛定諤之貓》是一部隨處夾雜著量子力學術語的小說,諸如“波包的坍塌”“退相干原理”“態矢量”“普朗克時間”等,這些深奧的科學概念,都在小說中被賦予了文學意義。小說中的這些科學元素,是“陌生化”效果產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小說從量子力學著名的薛定諤實驗開始,這個實驗在量子力學的科學著作中大致可以這樣概括:“在一個盒子里,用一個放射性原子的衰變來觸發一個裝有毒氣的瓶子的開關,毒氣可以毒死放在盒子里的貓。”“按哥本哈根學派的詮釋,放射性原子的衰變可以用波函數來描述。當用波函數描述不同狀態的組合時(如放射性元素‘衰變了或‘沒有衰變這兩種狀態的組合),我們稱之為‘波的疊加態。在沒有打開盒子時,放射性原子進入了衰變與沒有衰變的疊加態,由此貓也成了一只處于疊加態的貓,即又死又活、半死半活、處于地獄邊緣的貓。”
在小說中,作者并非致力于探討薛定諤實驗的科學意義,而是將這個物理學實驗的結果引向了對于存在本身的種種思考之中:在我們既有的認知里,生與死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狀態,非生即死;薛定諤這個假想的實驗,卻把我們的思維帶到了更遠的地方,如果盒子永遠不打開,就沒有人知道盒子里的貓是生是死,那么生與死就是疊加在一起的狀態。同樣,在與不在,是與不是,這些二元對立在某種情況下,就有可能是同時存在的,甚至死亡也變成了相對狀態。
在薛定諤實驗的基礎上,美國物理學家艾弗雷特進一步指出,活著的貓和死去的貓都是真實存在的,問題的關鍵在于,“當我們向盒子里看時,整個世界分裂成它自己的兩個版本。這兩個版本在其余的各個方面都是完全相同的,唯一的區別在于其中一個版本,原子衰變了,貓死了;而在另一個版本中,原子沒有衰變,貓還活著”,也就是說“這兩個世界將完全獨立、平行地演變下去,就像兩個平行的世界一樣”。
在小說中,作者也由此引出了對于平行世界的構想:“世間的每一個物體,根據函數的偶然性,都隨機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其中也包括像我們一樣有意識的生命,無一例外地不斷誕生自己的新版本。這些身份之間相互并不認識,每一個都對應一個不同的版本,而只有這些版本的總和才構成了一個不可思議的宇宙。在這里,所有可能存在的宇宙都是平行的。”
至此,回到小說的敘事層面,作者借助敘述者之口講述了一個感人至深的父愛故事:痛失愛女的敘述者在艾弗雷特所構想的平行世界中得到了慰藉,他與女兒或許能在未來的某一重合空間里再次重逢;或者在另外的空間,他從未有過一個女兒,也從未有過喪女之痛。在這一層面上,量子力學與人類情感達到了一種溝通。然而,故事并沒有就此打住,敘事者也并沒有在個人的痛苦中停止不前,而是進入了更高層次的思考中,即關于人類命運的思考。由此,小說進入到關于偶然性與宿命這一文學永恒的主題當中,作者進一步指出在薛定諤實驗中,如果盒子不被打開,那么各種情況都是可能的;然而,一旦盒子被打開,結局就變成了唯一的。在打開與不打開之間,究竟是偶然性的操縱還是一種既定的宿命,人們無從知曉。沿著這條線索,小說的主題,即關于人類身份問題的思考,逐漸變得清晰。
可以說,《薛定諤之貓》是對量子力學的一次文學演繹,在文學創作中注入的量子力學元素,使“陌生化”產生了巨大的效果。
2.從時間藝術到空間藝術
通常,人們認為雕塑、圖片、攝影藝術屬于空間藝術,而文學屬于時間藝術。在傳統的文學作品中,時間的線性邏輯成為絕大多數作品的敘事線索。然而,《空間敘事研究》中指出,“與傳統小說相比,現代小說運用時空交叉和時空并置的敘述方法,打破了傳統的單一時間順序,展露出一種追求空間化效果的趨勢。因此,現代小說總是呈現出某種空間形式”。也就是說,文學作品也可以呈現為一種空間的藝術。
在《薛定諤之貓》中,小說的敘事時間表現出含混與不確定的特征,缺乏明確的指向,任意在過去與現在之間來回穿梭:時而表現為現實的時間,如“太陽已經落山”“晚上”“吃過晚飯”等;時而表現為回憶的時間,如“從前”“五六歲的光景”“課間休息的時候”等。此外,小說中夾雜著大量的寓言故事與科學幻想,這使得敘述時間顯然更加無從追述。由此可見,小說的“寫作手法突破了線性時間觀念,把過去、現在和未來交織在一起”,使人“可以感覺到時間連續性的崩潰,而新的時間體驗不是一種清晰的現實性,而是模糊的混沌態”,“無論是物理時間還是心理時間都出現了混沌態的分形特征”。
相反,在時間隱去了痕跡之后,空間成為推進敘事的載體,承擔了一種傳統小說所不具備的敘事功能:將分散的情節組合起來,在表面碎片化的情節中,使小說的敘事有條不紊地在現實、回憶、夢境、想象四個層面上展開。在現實層面,空間的概念表現為海邊住所、屋后的花園、鄉間小道,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我”邂逅了一只貓,并與其發生了一段故事;在回憶層面,“我”與女兒的對話始終發生在“暗夜里”,在失去女兒之后,“我”也始終置身在黑暗之中;在夢境層面,有代表“我”童年回憶的一所“位于盧森堡公園和蒙帕納斯之間的一幢奧斯曼風格的樓房”,還有一個人夢里的鄉村、樹林、空地、空地中央的房子;在幻想層面,敘述者用大量篇幅描述了多個隱喻性空間,如盒子、平行世界、鏡子等等。
在小說中的敘事中,空間不斷發生轉換,從一個場景切換到另一個場景,在現實與回憶、真實與想象之間不斷跳躍;與此同時,變幻的空間又始終朝著一個既定的方向與情節的發展和主題的推進相呼應,表現出縱深方向的延展性,于是,跳躍的“點”形成了延展的“線”,延展的“線”又交織成一張錯綜復雜的“網”,最終,形成了小說完整而嚴密的空間結構。此外,小說還充滿了“各種戲擬的其他文本”,或是量子力學概念的隱喻性闡釋,或是具有東方色彩的寓言故事,每一個文本都有各自的空間背景。這些“戲擬的文本”與小說的主線形成呼應,“互為主體,互為語境,互相認知與闡釋”,使小說的空間變得立體。從藝術技巧來看,以空間代替時間的謀篇布局同樣為小說的創作增添了“陌生化”的效果。
3.詩化的小說
小說《薛定諤之貓》全篇分為四部分,每部分的章節并不固定,篇幅或長或短。從篇章結構上看,《薛定諤之貓》不同于傳統小說的謀篇布局,章節與章節之間沒有明顯的邏輯關系,敘事性也不再占據主要地位,情節趨于弱化,呈斷裂式推進。在小說被粉碎化的敘事中,“各種不同類型的文本扭結拼湊在一起”,量子力學的解釋性闡述、假托中國之名的寓言故事、個人感悟的直接宣泄等,與小說的敘事情節占據著同樣重要的地位。這種扭結與拼湊,“弱化了文本間的時序鏈接,通過有意識地引用或者是戲擬其他文本,使得文本與文本之間互為主體,互為語境,互相認知與闡釋,建構了一種文本拓撲空間”。在小說的寫作手法上,正如譯者黃葒在《薛定諤之貓》的譯本后記中所指出的,作者“越來越散,越來越自由,句子可長可短,隨心所欲,或夢囈,或兒語,或瑣碎具體,或簡約玄虛”。
從整體來看,情節的弱化、篇章布局的碎片化、戲擬文本的構建與語言表達的自由,使小說完全擺脫了傳統小說的寫作手法,在創作中加入了詩化與散文化的創作手法,從而為讀者帶來了一種全新的閱讀體驗。
二、文化價值——法國作家的中國幻象
在小說《薛定諤之貓》中,作者或是借助一系列的中國意象,或是假托中國之名,杜撰了與中國文化相聯系的寓言故事,透過它們,我們不難看到一個法國作家的中國幻象,以及兩種文化相互碰撞產生的深遠意境。
1.虛空與空
值得指出的是,《薛定諤之貓》中的故事始終處于漫無邊際的黑暗之中。敘述者與他收養的貓相遇在“透不出一絲光亮”的夜晚,在回顧兒時經歷時,黑夜也是永恒的背景,白天的一切“都被夜的墨汁涂得面目全非”,“鋪天蓋地的黑暗占據了一切”。甚至敘述者打發無聊的方式,也“只是傻傻地看著日落,看黑夜如何慢慢來襲,淹沒整個世界”。
與黑夜相對應的是“虛空”,黑色之上生出虛空,虛空“在眼前蔓延開來”,“無邊無際”,就像“一個洞,一個隧道的入口。隧道通往一個地方,一個最隱匿的所在,沒有任何出口;或者通往一個遙遠得如同創世之初的所在”。
事實上,小說中的虛空有著豐富的隱喻意義。劉鹿鳴在其文章中指出,在小說中“黑暗、黑色,虛空、無,隱喻存在之體,及其在時空的展開……所有關于生命本質或意義的思考都會追溯到生命的起源,宇宙時空的開端以及萬事萬物的生出、生長和不可避免的消亡、回歸空寂,這在哲學上成為本體論問題和宇宙論問題”。也就是說,虛空是一種隱喻,代表著作者對于萬物起源和宇宙開端的冥想。在小說中,虛空無處不在,無數的人生意義在虛空之上得以生發。《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有云:“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由此,小說中的“虛空”與佛學的“空”形成了一種對應。這種哲學思考奠定了整部小說的基調,作者試圖在廣袤的宇宙中追問人類的身份問題,最終在古老的東方智慧中找到了答案。
2.“黑夜里的黑貓”與中國皮影
《薛定諤之貓》的故事開始于貓:量子力學實驗中假想出的“薛定諤之貓”、在海邊別墅收養的貓,還有中國故事里眼睛能顯示時間的貓、虛空中“在時間的岔路口走向無處”的貓……事實上,貓在小說中具有非常重要的隱喻意義。其中,“黑夜里的黑貓”是貫穿整部小說的意象,在小說的開頭和結尾相互呼應。
小說在開篇的《序曲》部分,作者假托孔子之口,引用了一句莫須有的中國諺語:“在黑夜里逮一只黑貓”,并由此展開了意義追問。這是小說敘事的開始,同時也奠定了小說中的中國元素。“在黑夜里逮一只黑貓”,一方面是“智者不應追尋虛幻不實之物”,另一方面,敘述者提出了一種質疑,指出無論誰“都沒有言之鑿鑿地說此事斷無辦成之可能,他只說在黑夜里找一只黑貓是再難不過罷了”。敘述者正是以這種模糊了二元對立的思辨為整部小說開啟了一種充滿東方智慧的語境。
皮影戲是中國民間的傳統藝術,中國皮影也是小說中反復出現的一個意象。如同黑夜里的黑貓一樣,皮影也誕生在黑暗之中:在黑色的背景之下,“后面放一個光源,就可以把物體的形狀打在幕布或白紙上,你就能得到一個剪影”。
在小說中,充滿東方色彩的皮影顯得神秘莫測:“它不能告訴你光線下你拿在手里的物體有多厚實,用這種方式得到的影像可能完全是騙人的,同樣的剪影可以對應外形迥異的好幾個物體,或者說同一個物體也可以有幾個不同的剪影。”于是,作者在小說中圍繞皮影進行了一場關于“真”的思考。在這里,充滿中國風情的古老藝術與新物理學所構建的多重空間發生了碰撞:如果宇宙在每分每秒都能分裂成無數個平行空間,那么,當“我”置身于無數平行空間時,不同空間的“我”與現在的“我”哪一個才是真實的我。
3.“鏡中人”
除了構建豐富的中國意象,菲利普·福雷斯特還假托中國之名,在小說中穿插著講述了幾則寓言故事,借助所謂的“中國傳說”將一個法國作家的中國幻象具體化。其中,“鏡子世界”就是一個極富隱喻的寓言故事。傳說在很多年以前,我們和生活在鏡子中的人相處融洽,兩個世界可以任意穿梭,并且雙方并非彼此的倒影。直到有一天,鏡中人入侵了我們的世界,最終卻被我們打敗,于是我們豎起了無法穿越的鏡子,兩個世界彼此隔離開來,而且“戰勝者給戰敗者施了魔法,讓后者只能擁有前者的樣貌,被迫模仿他們的每一個動作”。在詳細講述了這則“中國傳說”之后,作者假托敘述者之口,提出了“馬上浮上心頭的疑問”:“到底哪一邊才是鏡子的世界?”
鏡子的故事再次隱喻了世界的真實性,包含著一種近乎宗教式的體驗,并且與莊周夢蝶的故事有異曲同工之妙。
同一個故事,作者還運用另一個版本加以闡釋:“我每天都跟我的‘貓師傅學習。在露臺上,我閉上眼,學它的樣子,在陽光下小睡。于是,我夢到自己是一只貓。然后,我醒了。我不知道自己是夢到貓的人,還是夢到人的貓。”最后,作者給出了一個不算明晰的充滿中國式思辨的答案:“我們沒有任何方法判斷哪邊是夢境,哪邊是現實。我是我,我是他,我是千千萬萬的他者,但同時又不是他們當中的任何一個。”
三、社會價值——混沌視域下的宇宙觀
混沌理論指出,看似無序的碎片可能會匯聚成一個有機的整體,而整體中一個因子的改變也可能會引起整個系統的改變,隨機性與先定性是同時存在的。“這一結論威脅了我們的話語一向賴以依靠的邏輯法則”,并且“這些錯綜復雜的問題引發了一個重要問題”,即“我們作為個體,能在多大程度上控制自己的命運或環境”。因此,人類的身份問題“比我們所設想的還要復雜得多”。《薛定諤之貓》的獨特之處就在此,故事背景的設定超出了既有的社會意識形態,人類被放逐在一個由新物理學所開拓的更為廣闊的宇宙空間之中。量子力學成為小說敘事的基點,故事始于薛定諤實驗,對固有的二元對立進行了顛覆性的解構,指出了在與不在,是與不是,甚至生與死都是可以疊加的。在事物的每一個節點上,都會由潛在的可能性分裂出無數的平行空間,每一個空間都有一個不同身份的自我。世界的真實性由此受到了質疑,生存的意義也變得模糊。在混沌與虛空的背景之下,敘述者生發出對混沌的宇宙之初、世界的有序與無序、真實與虛幻的冥想,在這場冥想中,人生的意義最終從消解走向了建構。
小說首先探討的是痛苦,事實上,正是在痛苦的體味中,人生的意義才得以重新構建。在這部情節淡化的小說中,核心的故事圍繞著敘述者的喪女之痛展開。
最初,痛苦是強烈的,在失去女兒之后,敘述者看見“漆黑的夜色已經在她身上升起,就像一塊令人心碎的虛無之布,被時光拉著,蓋住了她的身體和她的靈魂”。然而,即使是痛徹心扉的苦難也會隨著時間而流逝,“今天,我一點都不記得她曾經說過的話,也不記得我曾經對她說過的話。那些話仿佛漂浮在虛空中,不屬于任何人”。從表面上看,痛苦會被時間瓦解,“仿佛一滴墨落在清水里”,會被慢慢稀釋。痛苦在這一層面似乎得到了緩解,“絕望的力量會把你變得比以前更強大”,“你驚訝地發現自己已變得堅不可摧”。
至此,敘述完成了一次轉折,似乎時間足以消解痛苦。但是,當人們自以為痛苦已經走遠的時候,卻發現“諷刺的是,每一次哀悼都會使隱隱的傷口再次開裂,這些傷從來沒有完全結痂”,“所有的痛苦都原封不動地立在那里”。由此,痛苦達到了頂峰。如果故事在這里戛然而止,那么《薛定諤之貓》僅僅是一個關于消解的故事,人生的意義深陷在絕望之中,無法超脫。然而,小說很快進入了對痛苦的另一層解讀:“我完全不能,并且以后再也不能擺脫悲傷。但我又慶幸,因為與此同時我感受到我身上保留著一種鮮活的東西,我借助它依然可以體會到生而在世的可憐,而正是這種感受將我與過去的我維系在一起。”也就是說,當痛苦避無可避的時候,反而成為一種存在的證明。伴隨著痛苦被賦予了一種積極的意義,人生的意義也被重新構建。“有幾次當我想自殺的時候,我知道是什么讓我活了下來。和剩下的一切比起來,我的理由真的微乎其微,但它卻讓我一直活了下來:好奇、愚蠢地想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么,急切地想了解等待我的空虛的明天是什么樣子。最微不足道的理由卻可以促使你自殺,不過話說回來,同樣無關緊要的原因也可以救你的命。”
在宇宙的混沌與虛空中,“世界正好呈現出一個平淡無奇的迷宮的樣子,既陌生又熟悉,每一個新景致都和上一個相同,前方永遠找不到出口”。每個人的使命似乎就是在黑夜里追尋一只黑貓,可能一無所獲,但是“哪怕只是為了在黑暗里前行一點點”,這樣就足夠了,活著最偉大的意義不再是尋求一個偉大的理想,而是活著本身。
四、結語
小說《薛定諤之貓》將量子力學的諸多概念轉化為文學元素,以藝術的手法加以呈現。在敘事技巧上,以空間敘事代替了時間敘事;在表達手法上,將詩意投射在小說的行文之中,由此產生了“陌生化”的藝術效果,為讀者帶來了全新的閱讀體驗。在小說中,作者借助帶有中國文化色彩的意象以及戲擬的“中國傳說”將一個法國作家的中國幻象表現在文本之中,產生了獨特的文化意蘊。此外,隨著新物理學開拓了人類的視野,空間成為一個不斷延伸的概念,人類固有的邏輯發生了顛覆性的改變,小說中對生存意義的追問成為新宇宙觀視域下人類對自身身份思考的有益探索。總之,小說《薛定諤之貓》在中國的譯介與出版具有深刻的文學價值、文化價值和社會價值。
|參考文獻|
[1]菲利普·福雷斯特. 薛定諤之貓[M]. 黃葒,譯. 深圳:海天出版社,2015.
[2]楊建鄴. 窺探上帝的秘密——量子史話[M]. 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
[3]朱利安·沃爾弗雷斯. 21世紀批評述介[M]. 張瓊,張沖,譯. 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
[4]朱剛. 二十世紀西方文論[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5]龍迪勇. 空間敘事研究[M]. 北京:三聯書店,2014.
[6]方勇,譯注. 莊子[M]. 上海:中國書局,2015.
[7]弘一法師.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M]. 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
[8]柳文文. 跨越界限:后現代主義文學中的混沌圖景[J]. 安徽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3).
[9]劉鹿鳴. 通往“真”的路——讀《薛定諤之貓》[J]. 書城,201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