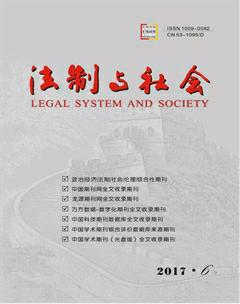對投資協定中可持續發展概念的性質探析
摘 要 為了進一步保護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可持續發展被國際環境法視為一項重要原則。然而,其并不是一個孤立的概念,其實現需要依賴于經濟、社會、文化等多方面的推動,因此可持續發展現被納入國際貿易、國際投資以及人權保護等領域是必然結果。然而可持續發展的內涵與外延難以界定,這為其定性帶來了困難。可持續發展已從當初僅包涵環保的狹義概念延伸為可包括勞工、人權等問題的綜合性概念,且從廣義上而言其內涵仍在擴大,此外,其在國際法中的地位仍不明朗,其應僅僅被視為一個法官在裁決時考量的價值因素,還是具有條約規范或習慣法的地位,亦或是國際軟法規范尚存爭議。
關鍵詞 可持續發展 性質 國際法
基金項目:本文系2014年度上海市教委科研創新重點項目“歐美投資條約可持續發展政策對上海企業海外投資的影響與對策”(14ZS006)的階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簡介:龐慧,復旦大學2014級國際法學專業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國際經濟法。
中圖分類號:D99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6.315
一、可持續發展的由來:國際軟法
可持續發展這一概念起源于一系列的國際性文件。1972年《斯德歌爾摩人類環境宣言》序言中強調了保護人類生存環境的重要性,并將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相結合,這被認定為可持續發展概念的雛形。此后,聯合國開始逐步關注和推廣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并在《布蘭特報告》中首次定義可持續發展,即“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 迄今為止被廣泛接納及援引。1992年的《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的21項原則被認為是進步的造法舉措(progressive law-making),是意圖將可持續發展概念提升至具有約束力的國際法規范的有益嘗試,并被認為是對正在形成的全球環境法原則的有力支持。 此后,可持續發展的概念開始被納入國際貿易協定和國際投資協定中。
由此可見,可持續發展源自不具有國際法強制約束力的文件,最初并不是一項法律概念或術語,而僅僅是一項人類普遍追求的目標,然而,國際爭議解決機制對可持續發展的援引及應用使其脫離了其軟法屬性而逐漸成為具有法律規范屬性的概念。
二、爭議解決中的可持續發展:法律概念
國際法院在Gab kovo-Nagymaros一案中將可持續發展作為一概念進行援引以協調“發展權”與“保護環境”之間的利益沖突。此案中可持續發展既有實質意義也具有程序意義:在實質層面,可持續發展要求實現雙方的利益平衡,此案中具體指合理分流,而在程序層面則是指雙方需重新審視大壩可能帶來的環境問題并通過友好協商的方式自行商議解決方式。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國際法院將可持續發展認定為一項概念,但當在論證可持續發展應被納入裁判因素時則稱:“近20年的文件中出現了些許新的規范和標準。在國家開展新的活動或是持續至今的先前活動中,該等規范應是被考量的內容,該等標準也應被予以重視。協調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需要充分體現在可持續發展的概念中”。 上述論證表明,可持續發展的概念是一項國際法規范或標準,具有一定的法律意義。雖然國際法院繞過了可持續發展的定性問題,但首次將可持續發展作為一個法律概念加以援引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在爭端解決中,WTO上訴機構為可持續發展概念在條約中的適用提供了重要參考依據。在US-Shrimp案中,WTO上訴機構明確指出,1994年成立世貿組織的《馬拉喀什協定》的序言中寫道“各成員國充分認識到環境保護作為一項國家及國際政策目標的重要性和合法性”,因此,這表明“各國在進行成立世貿組織的談判中已承認對世界資源的使用應符合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上訴機構進一步指出,依據《維也納條約法公約》對條約解釋的規定,在解釋GATT1994條款時應注意“參照條約之目的及宗旨”。 在此案中可持續發展被認定為各成員國在簽訂條約時所共同認可的目標之一,并以條約解釋的方式擴大了GATT 第20條(g)項的適用范圍,進而賦予了美國相關國內法一種域外效力。因此,有學者認為可持續發展概念具有部分法律規范的屬性,在實體方面具有擴大第20條(g)項管轄范圍的作用,而在程序方面則預示著可能賦予一國先進的環境保護規范一定的域外效力。 不過隨后WTO的貿易環境委員會則表示其并不贊同通過賦予先進國內環境保護規范域外效力的方式來推動可持續發展,而是建議各國應積極推進國際環境條約的制定及簽署已解決環境爭端。
綜上所述,可持續發展雖被國際法院和WTO上訴機構稱為“概念”或“目標”,但其具有一定的法律規范屬性,特別是其在條約解釋中的作用不容忽視。在Gab kovo-Nagymaros中國際法院之所以援引可持續發展的概念是因雙方在1977年簽訂的合作建立堰壩條約中明確規定“條約項下的行為不得違反保護自然的義務”, 而在US-Shrimp案中上訴機構適用可持續發展也可追溯到《馬拉喀什協定》的序言中,由此可見,條約中對環境保護義務的認知是爭議解決中裁判機構得以援引可持續發展的前提,因此,可持續發展須結合具體條款才具有明確的規范屬性。
三、投資協定中的可持續發展:習慣法或條約規范
對于可持續發展性質的爭論已持續近20年,針對其能否被認定為習慣法的爭論尤為激烈。筆者認為,可持續發展雖具有法律規范的屬性,但尚未發展成為一項國際習慣法。首先,其內涵尚不明確,若僅指環境保護義務,則依據現行國際環境法,已然可以確定為一項國際法原則,但在聯合國公布的“2030計劃”等文件中將可持續發展擴展為包含環境、經濟、人權、文化等諸多方面的概念,因此不能簡單的將可持續發展與環境保護原則等同。由于其內涵和外延仍在發展,因此該概念所涵蓋的范疇并不具有確定性,而依據國際法院在North Sea Continental Shelf案中對國際習慣法的認定,一項國際習慣法除應具有法律確信和國家實踐這兩個要素外,其本身還應具有“造法的根本屬性”(fundamentally norm-creating character)。雖然國際法院沒有正面回應什么是“造法的根本屬性”,但其從反面明確指出“若對其定義尚未達成共識,則不具有造法的根本屬性”。 由于可持續發展的范疇尚存爭議,且其超出環境保護的內容欠缺法律確信力及國家實踐,因此可持續發展概念本身不應被認定為國際習慣法。但這并不意味著其不具有法律規范屬性,可持續發展除出現在上述國際軟法外,在投資協定中也頻頻出現。例如,在歐盟與南非等5個SADC-EPA成員國簽訂的經濟發展協定中,可持續發展作為單獨一章不僅闡述了環境保護和勞工權益,更進一步規定了可持續發展與投資的關系。由于近期南非修訂了BIT范本,并高度強調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將其以專章專節予以規定,因此涉及南非的BIT在可持續發展方面具有先鋒作用。除此之外,在投資協定的序言中納入可持續發展目標,加之以具體環境條款、勞工條款或者是一般例外條款以明確上述目標的內涵大量出現在近些年的BIT之中。由此可見,雖然可持續發展目前尚不能被認定為一項國際習慣法,但其在國際投資協定中作為一項目標或宗旨指引相關條款已數見不鮮,表明可持續發展作為投資協定的重要政策已毋庸置疑,甚至可能通過條約中的國家實踐將其部分內容尤其是國際環境法的相關原則(如環評原則)逐步發展為國際習慣法。因此,我國應加以重視,研究如何在投資以及貿易領域融入可持續發展的政策,以便在相關投資協定談判中占據主動地位。
注釋:
Report of the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Our Common Future, Chapter 2, Part IV, para.1. http://www.un-documents.net/our-common-future.pdf, 2017-05-10.
Alan Boyle. Codif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and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Injurious Consequences Revisited. Alan Boyle and David Freestone. International Law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ast Achievements and Future Challeng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61-85.
David Hunter.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and Policy. New York: Foundation Press, 2015. 433-501
Gab kovo-Nagymaros Project, ICJ Reports 1997, 78(para.140) .http://www.icj-cij.org/docket/files/92/7375.pdf, 2017-05-10.
US-Shrimp AB-1998-4, 12 October 1998; ILM 33 (1999), para.129.
《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三十一條.
P. Sands,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3 Max Planck Yearbook of United Nations Law 389-407(1999).
Treaty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of the Gab?ikovo-Nagymaros Barrage System,16 September 1977, Art.19.
North Sea Continental Shelf, ICJ Reports 1969, 43(para.72) .http://www.icj-cij.org/docket/files/52/5561.pdf, 2017-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