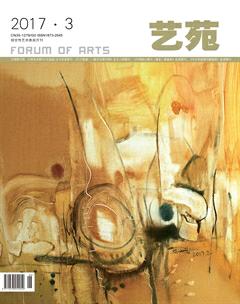在“個人”與“國家”之間
郝朝帥
【摘要】 《湄公河行動》的良好口碑,更多來自于影片對于“國家”與“個人”關系的全新表述,即國家為了保護國民而全力付出。這種表述策略突破了更多強調個人為國家做奉獻的“主旋律”傳統(tǒng)。而通過與另外兩部相關文本《集結號》和《十月圍城》的比較,在“國家認同”的理論視野中能夠將這一討論深化。
【關鍵詞】 《湄公河行動》;“個人”;“國家”;“國家認同”
[中圖分類號]J90 [文獻標識碼]A
林超賢導演的電影招牌就是真刀真槍的“硬”與“狠”,拍出勁爆的場面自然不在話下。但在2016年國慶檔期,事先并不張揚的《湄公河行動》能在短短幾天依靠口碑強勢逆襲,還真不是場面激烈燃情就能解釋的。若論場面,比這部影片更火爆的影片多得是。無論怎樣,緊湊的節(jié)奏,震撼的視聽,這些過硬的“面子”活只是《湄公河行動》成功的一個方面。而這部影片的“里子”——對于“國家”與“個人”之關系的全新表達和高調聲張,一種不走尋常路的“愛國主義”教育才是引發(fā)如潮好評的根本所在。
一
《湄公河行動》的故事并不復雜:中國普通船員異域蒙冤慘遭殺害,國家高層痛下決心查明真相,公安勇士深入敵穴九死一生,幕后敵酋瘋狂對抗終被全殲——但由于情節(jié)的主體部分取自真實事件,銀幕上的驚心動魄就格外令人感動。影片讓人們看到了國民尊嚴和國家尊嚴緊緊相連,“國家”也不再是遠離普通人生活的政治詞匯,它就在每個人身邊,作為堅強后盾護佑著自己的子民。影片也很注重突出這一點,在開頭和結尾兩段,都采用新聞紀實般鏡頭,配合以鄭重其事的畫外音和字幕來加強對觀眾的刻印。在這里“國家”和“個人”的關系被表述為:國家是國民安全感的來源和保證,國民如若在外受到侵犯,國家就會出頭討回公道,而且一追到底,不懼艱險不惜代價。影片的重心是國家對于個人的保護(或者說付出),而不再是僅僅注重渲染個人對國家無私無悔、甚至是充滿悲情的絕對奉獻。雖然電影中張涵予和彭于晏們的角色仍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鐵血英雄,肩負祖國的使命去流血犧牲,但影片并沒有過多筆墨留給人物塑造。
如此處理國家與個人的關系可謂耳目一新。如果將目光投向新中國電影的縱深處,能發(fā)現(xiàn)在“個人”與“國家”之間,一直更多強調的是“個人”對“國家”的奉獻:在戰(zhàn)爭電影一脈,從建國初的《英雄兒女》,到80年代《高山下的花環(huán)》,再到90年代的《大決戰(zhàn)》等,在不同歷史時期人們看到的都是為了建立、保衛(wèi)新中國而浴血奮戰(zhàn)、無畏獻身的英雄們。至于和平年代的英模影片,無論是80年代《人到中年》、《蔣筑英》,還是90年代《焦裕祿》、《孔繁森》……也都是充滿“位卑未敢忘憂國”的樸素情懷和獻身事業(yè)的崇高道德。與此同時,影片也充分(甚至是刻意)展示出主角們在個人生活狀況上的拮據(jù)、困窘,以至于難以維持基本生活的艱辛(如《高山下的花環(huán)》中梁三喜一家)。兩廂對比之下,從視覺到心靈的沖擊力都讓人不勝感慨——電影主創(chuàng)者們也深信這種創(chuàng)作思路的力量,在各種影片中都一再突出這點,似乎只有通過這種強烈的反差,用惡劣的物質條件才能更有力地襯托出主人公精神的純粹高拔。克服了“沉重的肉身”,超越了一己之私欲后,個人才能最終升華至圣賢之列。
對于紅色中國來說,“愛國主義”的內涵就在于強調個人為國家的付出。然而一個滿腔赤誠為國奉獻的人,何以自己得到的待遇卻如此令人遺憾?或許當時的人們并不會產生這樣的疑問。對于物質基礎“一窮二白”的新中國來說,從建立之初到其后很長一段時間里,一直生存于兩個軍事大國的武力威脅下,國家只能將更多投入側重于重工業(yè)基礎的建設。與此相應就是生活資料供給短缺,長時期處于物質高度匱乏狀態(tài)。這種情形之下,無論是從現(xiàn)實上,還是從理論上,如果發(fā)出“個人能從國家那里得到什么”的提問都顯得缺乏足夠的合法性。當然,更應該看到的是,新中國的成立和發(fā)展壯大本身就是對“個人”權利最強有力的護佑:如果沒有這樣一個全新的主權國家,在風雨飄搖的舊中國,作為普通百姓從財產到生命的一切更是毫無保障。更何況建國后在公共衛(wèi)生醫(yī)療水平、基礎教育覆蓋等方面的大幅度提高,也都是新中國為了“個人”所提供的最有價值的尊嚴和權益。只是,這一點不如具體的物質待遇那么容易讓人有切身感觸罷了。
在21世紀到來后,經歷了80年代知識界對“人性”的大力伸張、90年代社會的整體經濟轉向,在全球化和市場化的時代,新世紀已然是“個人”話語全面高揚、“集體”話語徹底退縮的時代。橫亙在“個人”與“國家”之間的價值觀,經歷了比較明顯的全面反轉。“國家”這樣的宏大概念失去了在既往艱難時日中的詢喚/規(guī)訓功能。以“人性”的名義,個人的利益理直氣壯地超越國家這種更“政治”的話語。
在這種時代氛圍中,新世紀的主旋律電影關于“國家”與“個人”的表述空間與策略難度必然會大大增加。2007年馮小剛導演的戰(zhàn)爭片《集結號》成為一時爭議話題正因為此。一個連的志愿軍戰(zhàn)士為了掩護大部隊撤退投身到一場實力懸殊、勢將全體犧牲的消耗戰(zhàn)中,這是一種個人對國家的徹底奉獻。男主角谷子地和他的弟兄們不會去懷疑自己苦守陣地、在強敵面前必然的死亡值不值,不會去懷疑上級的指揮合理不合理。他們不怕死,因為他們相信自己的死亡有意義,國家所授予的“烈士”名分就是他們慷慨赴死的價值和報償。所以,當唯一幸存的連長谷子地在得知死去的47個弟兄被認定為“失蹤”而不是“犧牲”后,他狂怒而悲痛,用自己的后半生不屈不撓地為他們尋求“正名”——這里,能明顯看出超越傳統(tǒng)戰(zhàn)爭片的是“個人”的聲音得到了強調。而這“個人”的聲音又不是處于和“國家”對立的姿態(tài),就像對影片激烈的質疑者所批評的那樣,影片不去拷問戰(zhàn)爭本身對眾多生命剝奪的合理性,尤其是對于淮海戰(zhàn)役這樣同一民族的內戰(zhàn)(但是,若果真這樣處理的話也并不高明,架空歷史情境反思戰(zhàn)爭更是一種淺薄)。影片宣傳海報上的那句話“每一個犧牲都是永垂不朽的”,其前提就是并不懷疑個人是否應該為殘酷的戰(zhàn)爭獻出生命,只是每個人獻出的生命都應該得到應有的尊嚴、國家的認可,盡管他們“無名”,但他們的生命將會受到國家和后人莊嚴的祭奠。“個人生命的短暫被‘歷史的永恒所書寫,這種‘無名的狀態(tài)也就得到了自身最終的報答和價值的肯定。”[1]7-10“無名”者存在過的痕跡不會被歷史所抹擦,因此影片沒有用質疑“戰(zhàn)爭”本身來表達“國家”對“個人”的遮蔽。連長谷子地所不能接受的,只是九連的全體犧牲既“無名”且“無分”(“失蹤”就是一種徹底的痕跡“抹擦”),是“個人”的獻身行為受到了遮蔽。
圍繞《集結號》的爭議,非常典型地反映出傳統(tǒng)“國家”話語與“個人”話語面臨沖突時的弱勢困境。而影片對故事的最終處理(烈士們遺體被找到,得到了追認的榮譽),則顯示了主創(chuàng)們彌合裂痕的努力。
二
然而相對于《集結號》的小心翼翼,一年之后,另一部“準大片”級別的電影《十月圍城》(陳德森導演,2009年)卻在“國家與個人”命題上來了次正面強攻。這部影片似乎毫不顧忌今天人們早已敏感地將“個人”與作為政治架構的“國家”劃分開來的自覺,而是將“家國大義”表達得淋漓盡致。雖然不乏有人詬病這部電影敘事邏輯不夠嚴密,前后脫節(jié),但它難得的是通過眾多濃墨重彩的小人物,將自己的“國家”敘事與草根微末的“個人”連接起來。尤為詫異的是,這部“舍‘小我為‘大我”的 “類主旋律”在當下語境竟然取得了當年歲末的良好口碑。
同樣是關于個人的犧牲,而且是很多人為了一個人的犧牲,是一群非軍事人員在非戰(zhàn)爭狀態(tài)下、甚至在不知自己為誰而犧牲的情況下犧牲,影片面臨“說服”觀眾的難度可想而知。為此,影片非常細致地剝繭抽絲,通過不同的人物的命運和心理,一點點地在情感和理論上進行鋪墊堆積,給觀眾們切身理解了“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整個中國都被卷進來了,我能避免嗎?”等所謂切身的“大道理”與“小道理”的融合,在不知不覺忘記了“個人”話語在心里先驗的優(yōu)勢地位,接受了“每一個犧牲都是永垂不朽的”。而且到了影片最終,還用孫中山的口吻對于個人的犧牲與建立一個新的國家之間關系做了深沉的總結,對為了保護他而犧牲的所有人進行意義提升:“十年以前,衢云兄在此跟我討論何為革命?我告訴他,革命,就是要讓四萬萬同胞人人有恒業(yè),不啼饑,不號寒。十年過去了,與我志同者相繼犧牲,我從他鄉(xiāng)漂泊重臨,革命兩字于我而言不可同日而語。今天,再道何為革命,我會說: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經文明之痛苦。這痛苦,就叫作革命。”——十年前,他想的更多的是革命的終極目標,而歷經挫折磨難后,十年中他更多體會到的是革命過程中付出流血犧牲的代價。深沉的總結再次將影片中所有“個人”的犧牲整合進“國家”話語中。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這種“草根的奮戰(zhàn),庶民的勝利”[2]10之外,這部影片還有一個重要的制勝策略就是,它將現(xiàn)代中國的“國家”話語上溯至它的源頭——孫中山先生,從而得到了世界范圍內更多華語地區(qū)的共同認可。而且,將故事的發(fā)生背景設定在英帝國統(tǒng)治下的香港,這樣,影片中“國家”的訴求也同時還是一個擺脫外侮、主權獨立的新的中國。這是一個最能激發(fā)起所有人愛國情感的命題,救亡圖存意義上的“中國認同”是最不具備爭議的社會群體心理。
由《十月圍城》的口碑成功可見,關于“國家”與“個人”,后者未必就有不言自明的優(yōu)勢地位,二者之間誰更應優(yōu)先,個體的心理認同至關重要。在此可以從“國家認同”理論上進行深入探究。
何為國家,為何“愛國”, 在近年來的公眾話語場中似乎變得很復雜。作為個體的“國民”和作為體制的“國家”應該是什么樣的關系,“國家”與“政府”不能混為一談,“愛國”與“狹隘民族主義”也需要切割清楚……很多知識者都在苦口婆心告誡大眾,一個國家,只有在它能充分保證你的人權,能滿足你生存和發(fā)展的空間時,你才可以去愛它,否則無需單方面奉上自己的耿耿忠心——在這種衡量標準中,簡單地說句“我原意為國家無條件付出”似乎成了無法理直氣壯的蒙昧。
應該說,上述說法中除去最后偏頗而輕浮的精英化自我標榜外,對于社會的進步與制度的完善、公民意識的覺醒與維護的確有著正面促進意義。不過,將國家和個人關系進行如此定位也并不算什么深刻。早就有學者進行過細致的梳理:討論“國家認同”,首先將“國家”指涉一切治權獨立的“政治共同體”,“每一個統(tǒng)治權大致完整,對內足以號令成員、對外足以抵御侵犯的政治實體,即為國家。”而對個人而言的國家認同則是“分析一個如何決定其國家歸屬,如何看待國家歸屬與私人生活秩序的問題”,“姑且定義為國家認同為‘一個人確認自己屬于那個國家,以及這個國家究竟是怎樣一個國家的心靈活動”。而在當代政治哲學中,對“國家認同”也有兩種不同的論述系統(tǒng):“民族主義理路”與“自由主義理路”。“民族主義理路”的支持者認為國家是維護民族文化、實現(xiàn)民族使命的制度性組織,而認同是個別成員認清自己所屬脈絡,從而產生歸屬感的心路歷程,認同的基礎是血緣種姓、歷史神話、語言宗教、生活習俗等等民族文化,認同表現(xiàn)為回溯式、尋根式的活動。正如艾青詩句所言,“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著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而“自由主義理路”的支持者則認為國家是一群人為了保障私人利益、防止彼此侵犯而組成的政治共同體,他們的認同比較不強調歸屬與情感,而多了意志選擇的成分,認同的是產生共識的基礎,包括憲政制度、程序規(guī)則、基本人權保障以及公平正義原則等等。[3]5-22
結合生活現(xiàn)實,或可說,“民族主義理路”的國家認同更多和中國傳統(tǒng)接通,中國人所謂“家國一體”,所謂“修齊治平”,就是將個人、家庭、國家、天下完全同構,是完美人格和完美人生的實現(xiàn)路徑。——這種中式傳統(tǒng)倫理培育出的就是一代代國人“位卑未敢忘憂國” 的拳拳之心,更多強調了個人的歸屬與情感付出。而“自由主義理路”的國家認同,體現(xiàn)的則是西方傳統(tǒng),源其概念核心是個人的基本權利必須得到保護,個人作為最高價值受到國家的尊重。要我愛國,首先是要這個國家足夠愛我才成,彰顯了“契約原則”在社會建構中的作用。
兩種國家體認,兩種愛國精神,在認知上本無高下之分,體現(xiàn)出的只是文化差異。無論個人持有哪一種觀點,在一個開放包容的社會中都應該予以接受理解。在上世紀80年代初,就曾出現(xiàn)過一部經典禁片《苦戀》,非常直觀的在父女兩代人身上展開了兩種“愛國”觀念的交鋒。然而,今天國內人文和社會科學領域中占據(jù)主導的話語體系基本舶自西方,尤其是對于現(xiàn)代國家、現(xiàn)代政治的理解上。于是一茬茬讀書人就更多的愿意在上述“自由主義理路”中考量、修訂自己的愛國情感,會更加傾向于個人權利本位的國家認同了(與此相應的是,在掌握話語權的相對“精英”的人群之外,廣大國民依然普遍保持著情感付出型的樸素的愛國熱情)——這也就是今天在公共話語場中關于“愛國主義”分歧對立的主要原因。
而《湄公河行動》自帶光環(huán),既無需《集結號》那樣困惑糾結,也無需《十月圍城》那樣求諸于個人心理認同。這種“國家為個人付出”的典型案例一方面投合當下盛行的“自由主義理路”的廣大擁躉,而另一邊“民族主義理路”的推崇者也會更加欣慰于祖國對人民的關懷。在社會共識嚴重撕裂的當下,這部由香港導演出品的“主旋律”頗為難得的統(tǒng)合了針鋒相對的兩種立場。
三
當然,近年來并非只有上述三部影片涉及到“個人”與“國家”命題,但這三部影片反響之大,非常具有代表性。能夠看到,在近十年的跨度里,在不同表述策略的轉變中,最終還是銀幕外的生活現(xiàn)實為銀幕里的故事空間提供了突破的動力。正所謂“形勢比人強”,近年來隨著綜合國力的日漸提升,中國在國際空間里更為充分地展示了國家力量、彰顯出大國形象,也讓國民感受到切實有力的庇護,感受到對于國家的認同感和歸屬感。這樣,才會有《湄公河行動》的應時而生。
當然更應看到,關于“國家”與“個人”,完全可以將二者理解為高度同構的,是“現(xiàn)代性”追求與實現(xiàn)過程的一體兩面。所謂“現(xiàn)代性”追求,既包括在國家層面建立起主權獨立與領土完整的現(xiàn)代民族國家,也包括個人層面享有充分的個人權利、生存和發(fā)展的機遇。對于中國而言,在整個20世紀前半期,一直是在努力建立一個現(xiàn)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為此付出艱辛巨大的代價才告別了羸弱衰敗主權凋零的舊中國。而新中國成立后,經過前三十年大力建設國家的重工業(yè)基地、完成國家財富積累和再投資的過程、夯實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基礎后,近三十年實現(xiàn)的高速發(fā)展,使得國家在逐步走上強盛、重新崛起的過程中,個人層面的現(xiàn)代性追求也得到了越來越多實現(xiàn)的可能。人們不僅得到了越來越富足的生活,發(fā)展的空間也日漸開闊。而反過來說,國家之所以實現(xiàn)高速發(fā)展,更離不開一代代國人的拳拳赤子心,殷殷報國情。——這正是一個彼此促進、互相成全的過程。
在今天,在非戰(zhàn)爭年代,在傳統(tǒng)的“愛國主義”教育面臨“個人主義”話語挑戰(zhàn)的時候,通過國家全力維護普通國民的故事,打造全新的“個人”與“國家”雙位一體的愛國主義內涵,更是一個非常必要而且有效的舉措。尤其在目前“逆全球化”趨向日漸興起、“國家認同”重新成為凝聚人心的強勢話語、產生著巨大號召力的時候。
“湄公河”的成功應該視為一個始料未及的啟示,讓陷入技術迷信、偶像迷信、IP迷信的國內影壇多一種思路,在充分理解當下“個人”話語與“國家”話語高度同構的基礎上,在官方主導文化和人們的社會心理之間發(fā)掘出廣闊的價值交集,從而講述出真正“叫好又叫座”的中國故事。據(jù)報導,嘗到了甜頭的林超賢目前正在緊鑼密鼓地拍攝另一部相類似的影片《紅海行動》,這次的創(chuàng)作藍本是曾經讓世界刮目相看的利比亞大撤僑事件。對此,我們有理由充滿期待。
參考文獻:
[1]張頤武.集結號:對20世紀中國歷史的憑吊[J].當代電影,2008(3).
[2]趙寧宇.十月圍城:草根的奮戰(zhàn),庶民的勝利[J].大眾電影,2010(2).
[3]江宜樺.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M].臺北:揚智文化事業(yè)股份有限公司,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