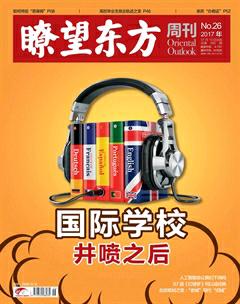公立學(xué)校國(guó)際部:再試試看
王輝輝
“國(guó)家只是要求規(guī)范發(fā)展,而沒(méi)有‘一錘子打死,就是要再試試看”
“可以登錄了!”秦浩(化名)的聲音里透著期待和緊張。
2017年7月3日,北京市2017年中考成績(jī)查詢系統(tǒng)正式開通。初中畢業(yè)生秦浩和母親早早地坐在電腦前,輸入查詢網(wǎng)址,一遍遍地刷新。終于在中午12點(diǎn)05分刷出了查詢頁(yè)面。

北京某學(xué)校國(guó)際部學(xué)生在學(xué)抖空竹
中考前,成績(jī)優(yōu)異的秦浩就打算選擇上國(guó)際學(xué)校,將來(lái)出國(guó)留學(xué)。家境普通的秦浩還有另外一條路可以走——選擇公立學(xué)校的國(guó)際部。
“如果孩子中考成績(jī)好,就可以讀公立學(xué)校的國(guó)際部,這樣能減輕不少經(jīng)濟(jì)負(fù)擔(dān)。”秦浩的母親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如果說(shuō)國(guó)際學(xué)校正在成為社會(huì)追捧的對(duì)象,那么公立學(xué)校的國(guó)際部,則因費(fèi)用相對(duì)較低以及隸屬于公立學(xué)校相對(duì)可靠,更受家長(zhǎng)青睞。
然而,與火爆的市場(chǎng)需求相反的是,隨著政策收緊,目前公立學(xué)校的國(guó)際部,未能持續(xù)增加供給。
這塊中國(guó)教育改革的“試驗(yàn)田”,究竟經(jīng)歷了什么?
從隔靴搔癢到親身體驗(yàn)
1983年,鄧小平為北京景山中學(xué)題詞“教育要面向現(xiàn)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lái)”。
“這就是中國(guó)現(xiàn)代教育國(guó)際化的開端。”中科致知國(guó)際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總校長(zhǎng)安瀛告訴《瞭望東方周刊》。此前,他曾擔(dān)任北京四中國(guó)際部負(fù)責(zé)人。
安瀛認(rèn)為,很長(zhǎng)一段時(shí)期,在基礎(chǔ)教育階段,公立學(xué)校承擔(dān)著教育國(guó)際化的主要責(zé)任,“只是當(dāng)時(shí)它并不是以創(chuàng)建國(guó)際部、引進(jìn)國(guó)際課程的方式來(lái)實(shí)現(xiàn)的。”
狄邦教育管理集團(tuán)(以下簡(jiǎn)稱狄邦教育)副總裁王娣告訴《瞭望東方周刊》,當(dāng)時(shí)公立學(xué)校推進(jìn)教育國(guó)際化主要是通過(guò)師生與國(guó)外學(xué)校互訪,與國(guó)外學(xué)校建立友好學(xué)校、姊妹學(xué)校等方式實(shí)現(xiàn)的。
創(chuàng)辦于上世紀(jì)90年代的狄邦教育,正是為了滿足當(dāng)時(shí)公立學(xué)校對(duì)外交流的需求。“主要是為公立學(xué)校的國(guó)際交流牽線搭橋。”王娣說(shuō)。
2003年以后,在政策的刺激下,一些公立學(xué)校開始試水國(guó)際班,引入國(guó)際課程。
“北京有一些走在國(guó)際化前列的學(xué)校,通過(guò)與國(guó)外學(xué)校合作,引入了國(guó)際課程。”安瀛說(shuō)。
比如,2005年前后,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附屬中學(xué)就引入了中英合作劍橋國(guó)際高中課程(A-LEVEL)。
但據(jù)知情人士透露,當(dāng)時(shí)的國(guó)際課程體系質(zhì)量并不高,從國(guó)際班的錄取分?jǐn)?shù)便可見一斑。當(dāng)時(shí)人大附中國(guó)際班的錄取分?jǐn)?shù)線要比學(xué)校本部低20分。但近些年有些學(xué)校國(guó)際班的錄取分?jǐn)?shù)已經(jīng)超過(guò)了本部。
“所以,就當(dāng)時(shí)來(lái)說(shuō),能上本部的學(xué)生幾乎不會(huì)去讀國(guó)際班。”上述人士稱。
安瀛認(rèn)為,國(guó)際班可以看作是公立學(xué)校教育國(guó)際化的升級(jí),其對(duì)國(guó)外教育的學(xué)習(xí),從“隔靴搔癢”的外部觀察階段,升級(jí)到了親身體驗(yàn)和參與的高級(jí)階段。
丟不掉的“拐棍”
在公立學(xué)校國(guó)際部發(fā)展的時(shí)間軸上,2010年是一個(gè)重要的年份。在此之前,全國(guó)范圍內(nèi)的公立學(xué)校國(guó)際部?jī)H有10所。
2010年后,公立學(xué)校國(guó)際部快速發(fā)展,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jié)果。
當(dāng)年,國(guó)家開始更明確地鼓勵(lì)推進(jìn)教育國(guó)際化。
2010年7月發(fā)布的《國(guó)家中長(zhǎng)期教育改革和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2010-2020年)》提出,要鼓勵(lì)各級(jí)各類學(xué)校開展多種形式的國(guó)際交流與合作,加強(qiáng)中小學(xué)對(duì)外交流與合作,提高我國(guó)教育國(guó)際化水平。
同年,美國(guó)留學(xué)簽證政策開始放寬,國(guó)際學(xué)校的發(fā)展也逐漸駛?cè)肟燔嚨馈?/p>
2010年之后,包括北京四中、北京實(shí)驗(yàn)中學(xué)等公立學(xué)校在內(nèi)的9所北京市級(jí)示范高中首先創(chuàng)立了國(guó)際部。
至2014年北京市教委宣布不再審批新的公立學(xué)校國(guó)際部為止,北京市共有21所公立學(xué)校創(chuàng)辦了國(guó)際部。截至2016年10月,全國(guó)范圍內(nèi)的這一數(shù)字是218所。
在北京市收緊審批之前,2013年,教育部出臺(tái)《高中階段國(guó)際項(xiàng)目暫行管理辦法》草案,明確要對(duì)各類高中的“國(guó)際部”和“國(guó)際班”,從招生、收費(fèi)等多方面予以規(guī)范。此后,各地紛紛收緊公立學(xué)校國(guó)際部的發(fā)展政策。
安瀛認(rèn)為,政策的收緊,一方面涉及教育公平,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公立學(xué)校國(guó)際部的運(yùn)行模式。
整體來(lái)看,目前開設(shè)國(guó)際部的公立學(xué)校大多為各地的名校。但這些學(xué)校并不具備獨(dú)自運(yùn)營(yíng)國(guó)際部的能力。“有的學(xué)校在剛開設(shè)時(shí)甚至沒(méi)有一個(gè)真正懂國(guó)際教育、國(guó)際課程的人。”一位要求匿名的業(yè)內(nèi)人士坦言。
此間,許多學(xué)校采取了與社會(huì)機(jī)構(gòu)合作辦學(xué)的模式。一般是公立學(xué)校負(fù)責(zé)提供校舍、教學(xué)設(shè)備和中方師資,社會(huì)機(jī)構(gòu)負(fù)責(zé)招生、課程引進(jìn)和外教招聘等。“國(guó)際部的管理有些由校方主導(dǎo),大多數(shù)則是由社會(huì)機(jī)構(gòu)主導(dǎo)。”安瀛說(shuō)。
王娣介紹說(shuō),目前已與全國(guó)26所公立學(xué)校建立合作關(guān)系的狄邦教育,在具體的合作中,負(fù)責(zé)國(guó)際課程體系的引進(jìn)和搭建、外教的招聘和管理、升學(xué)輔導(dǎo)體系的構(gòu)建。“引進(jìn)哪些課程,課時(shí)如何安排,采用何種教學(xué)方法與評(píng)價(jià)體系,都由我們負(fù)責(zé)。”
據(jù)王娣介紹,截至目前,狄邦教育共引進(jìn)了中英合作劍橋國(guó)際高中課程(A-LEVEL)、中美合作課程(AP)、國(guó)際文憑課程(IB)和中加課程、中澳課程,“不同的區(qū)域,不同的學(xué)校,我們會(huì)引進(jìn)不同的課程體系。”
前述匿名人士認(rèn)為,這種合作雖然可以在短時(shí)間內(nèi)彌補(bǔ)公立學(xué)校國(guó)際教育人才不足的缺陷,但如果長(zhǎng)期采用這種模式,既不利于公立學(xué)校國(guó)際部的發(fā)展,也最終會(huì)限制其教育改革“試驗(yàn)田”作用的發(fā)揮。
“實(shí)際上,熟悉國(guó)際教育的社會(huì)機(jī)構(gòu)應(yīng)該發(fā)揮的是‘拐棍作用,最終公立學(xué)校應(yīng)該扔掉‘拐棍,獨(dú)立行走。”匿名行業(yè)人士表示。
但現(xiàn)實(shí)卻是,一些公立學(xué)校國(guó)際部至今還未能丟掉這根“拐棍”。
而有些社會(huì)機(jī)構(gòu)為了追求經(jīng)濟(jì)利益,難免會(huì)盲目擴(kuò)大招生規(guī)模、隨意提高收費(fèi)水平,使公立學(xué)校國(guó)際部發(fā)展失序。

北京某學(xué)校國(guó)際部學(xué)生在上繪畫課
教學(xué)質(zhì)量:公立學(xué)校國(guó)際部未必高
一個(gè)事實(shí)是,公立學(xué)校國(guó)際部正在成為留學(xué)生的主要輸出地。
依照行業(yè)服務(wù)機(jī)構(gòu)新學(xué)說(shuō)提供給本刊的數(shù)據(jù),截至2016年10月,公立學(xué)校國(guó)際部在國(guó)際學(xué)校總數(shù)中的占比只有33%,其在校生規(guī)模也僅占國(guó)際生總數(shù)的10%左右。
但王娣告訴本刊記者,這10%的學(xué)生,占據(jù)了每年從國(guó)內(nèi)考上國(guó)外大學(xué)本科的留學(xué)生的半壁江山。
安瀛坦言,就畢業(yè)生的整體質(zhì)量而言,公立學(xué)校國(guó)際部遠(yuǎn)遠(yuǎn)高于民辦國(guó)際學(xué)校,但這并不是說(shuō)公立學(xué)校國(guó)際部的教學(xué)質(zhì)量要大大優(yōu)于民辦國(guó)際學(xué)校。
“相反,公立學(xué)校國(guó)際部的辦學(xué)歷史遠(yuǎn)不如民辦國(guó)際學(xué)校時(shí)間長(zhǎng),而且許多公立學(xué)校國(guó)際部的投入也遠(yuǎn)遠(yuǎn)沒(méi)有民辦國(guó)際學(xué)校多。但家長(zhǎng)和學(xué)生對(duì)創(chuàng)辦國(guó)際部的公立名校有天然的信任感,因此,其生源質(zhì)量是民辦學(xué)校無(wú)法比擬的。”安瀛說(shuō)。
同時(shí),國(guó)外大學(xué)的招生官很大程度上也更重視學(xué)校的聲譽(yù)。一些國(guó)外大學(xué)在中國(guó)設(shè)有專門的招生官,他們的重要責(zé)任就是對(duì)申請(qǐng)者的資料進(jìn)行審核,確保招收的學(xué)生能夠順利完成大學(xué)學(xué)業(yè)。
“在中國(guó),可能每所世界一流大學(xué)的招生官每年都會(huì)收到成千上萬(wàn)份申請(qǐng)材料,他沒(méi)有辦法詳細(xì)地去了解每一個(gè)學(xué)生。因此,只能說(shuō)往年某些學(xué)校的學(xué)生都不錯(cuò),他就更偏向于挑選這些學(xué)校的學(xué)生。在這方面,顯然公立名校更有優(yōu)勢(shì)。”安瀛告訴本刊記者。
能否成為教改“試驗(yàn)田”
對(duì)于許多公立學(xué)校來(lái)說(shuō),設(shè)立國(guó)際部的初衷不僅僅是為了推進(jìn)教育國(guó)際化,還要為教育教學(xué)改革探路。
“我們希望國(guó)際部可以成為高中課程改革的‘試驗(yàn)田。”安瀛在提及北京四中設(shè)立國(guó)際部的初衷時(shí)說(shuō)。
“如果公立學(xué)校不改革,仍走以前‘填鴨式教學(xué)的老路,那就面臨著失去競(jìng)爭(zhēng)力的風(fēng)險(xiǎn)。”國(guó)際化學(xué)校專業(yè)委員會(huì)專職副會(huì)長(zhǎng)賈大明在接受《瞭望東方周刊》采訪時(shí)說(shuō)。
而國(guó)際部的創(chuàng)立和運(yùn)行,使得中國(guó)公立學(xué)校的管理者有機(jī)會(huì)參與到國(guó)際課程的教學(xué)中去,深刻地理解國(guó)際教育的精神和內(nèi)涵,并從理念出發(fā),尋找適合中國(guó)的教學(xué)方法和評(píng)價(jià)體系。
“也正是因?yàn)槿绱耍?013年看到有些公立學(xué)校國(guó)際部發(fā)展失序,國(guó)家只是要求規(guī)范發(fā)展,而沒(méi)有‘一錘子打死,就是要再試試看。”賈大明說(shuō)。
安瀛認(rèn)為,從長(zhǎng)遠(yuǎn)來(lái)看,只有公立學(xué)校真正重視國(guó)際教育的發(fā)展,加深對(duì)國(guó)際課程的理解,未來(lái)國(guó)際部才能真正成為教育改革的“試驗(yàn)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