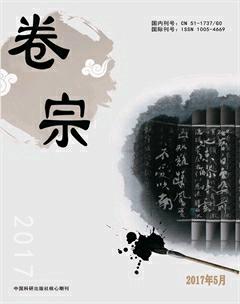“網絡水軍”的社會危害與刑法適用的若干研究
摘 要:隨著互聯(lián)網的發(fā)展和普及,在網絡上催生了一些新的“職業(yè)”,“網絡水軍”就是其中之一。“網絡水軍”通過注水發(fā)帖獲取報酬,這一新型職業(yè)的靈活性、隱蔽性、不可控性的特征非常明顯。從目前來看,“網絡水軍”這一“職業(yè)”給我們國家的網絡安全社會秩序等帶來一些危害。應在刑事法視野下,從完善法律依據,積極實行網絡過濾,規(guī)范網絡行為。
關鍵詞:網絡水軍;社會危害;刑法規(guī)制
1 網絡水軍產生的原因
1.1 網絡水軍產生的客觀原因
首先,互聯(lián)網的發(fā)展和普及方便了“網絡水軍”的這一“職業(yè)”的產生和擴大。據統(tǒng)計,截至到2016年6月,我國網民規(guī)模達到7.10億,互聯(lián)網普及率達到51.7%。伴隨著互聯(lián)網逐漸成為中國經濟社會運行的重要基礎設施和影響巨大的新型媒體,網絡經濟的發(fā)展成為一種必然,這也成就了“網絡水軍”這些網絡鐘點工的兼職工作。其次,網絡技術的迅猛發(fā)展為網絡水軍的產生提供了條件。再次,當今越來越多的企業(yè)進行網絡宣傳,這就為“網絡水軍”提供了生存的機會。僅僅有了載體和條件還不足以促使網絡水軍的產生,網絡水軍之所以如此迅猛的產生和發(fā)展,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現代企業(yè)宣傳向深度、廣度的發(fā)展。
1.2 網絡水軍產生的主觀原因
首先,我國互聯(lián)網監(jiān)管體系不健全。雖然,我國現有的法律法規(guī)當中已經有對于互聯(lián)網的規(guī)制,但是整體來講并不十分的完善。其次,缺乏行業(yè)自律。行業(yè)自律缺乏、企業(yè)誠信缺失是導致網絡水軍大量出現的重要原因。三是網民整體素質有待提高。由于我們國家的網民眾多,網民素質層次不齊,對于當前網絡中的各種現象缺乏一定的辨識度。無論是傳說中來自官方的“五毛黨”還是來自商界的“推手”都可以很容易地找到自己的獵物。
2 網絡水軍的社會危害性
2.1 危害國家安全
這是“網絡水軍”潛在的最大危害。當前,網絡上存在這樣一些“網絡水軍”,他們收到國外相關機構的資金支持,為國外服務,在國內的各大網站、貼吧等發(fā)布反動、恐怖言論,擾亂網絡秩序,制造網絡恐慌,威海了我們國家的安全。不少“網絡水軍”不惜違反國家法律,發(fā)布攻擊社會主義制度、分裂國家等反動言論和虛假信息,制造謊言、混淆視聽,從而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網絡水軍”的這些行為雖然是在虛擬的網絡空間所為,但是這種行為侵犯到了我們國家的安全穩(wěn)定,是觸犯刑法的,嚴重的會構成危害國家安全罪中的煽動分裂國家罪、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等。
2.2 破壞市場經濟秩序
對于市場經濟的破壞,體現在“網絡水軍”為一些無良的商家進行炒作,讓其在多時間內擠垮競爭對手,損壞對方的聲譽。這在蒙牛“誹謗門”事件和圣元“性早熟”風波中都有著較為明顯的體現。此外,“網絡水軍”為了個人利益,在網絡上無所不作,為各種新產品、新網游、網絡劇等進行大肆炒作、夸大宣傳,以此來提高關注度。“網絡水軍”的這種行為是對我國市場經濟秩序的嚴重破壞。
2.3 擾亂正常的社會秩序
“網絡水軍”的危害性還表現在利用其快速、迅猛的影響力,通過編造、宣揚民族間的仇恨和歧視的虛假言論、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等,擾亂正常的社會秩序。此外,“網絡水軍”出于雇主和公關公司的要求,針對現實生活中的司法問題和案件,發(fā)表一些顛倒黑白、擾亂司法的言論,蒙蔽不明真相的網民,使公眾對司法產生不信任和對抗情緒,給執(zhí)行造成嚴重阻力。
3 網絡水軍的刑事法規(guī)制建議
3.1 依據現行刑法從源頭展開是治理“網絡水軍”的基石
根據網絡水軍的運轉模式,其源頭和根基在于背后的雇主及組織“網絡水軍”的公關公司,正是雇主和網絡公關公司在商業(yè)利益的刺激下,雇傭“網絡水軍”進行非法行為產生了一系列的社會危害。刑法對雇主及網絡公關公司的行為處罰有明確的規(guī)定,依據現行刑法二者的非法行為可以得到有效治理。《刑法》第287條規(guī)定:“利用計算機實施金融詐騙、盜竊、貪污、挪用公款、竊取國家秘密或者其他犯罪的,依照本法有關規(guī)定定罪處罰。可見,利用計算機實施的犯罪符合什么罪的特征就構成什么罪,而不是計算機犯罪。考慮到當前我我們國家“網絡水軍”所帶來的社會危害,而且其行為具有多樣化,可能觸犯的刑法罪名也比較多:煽動分裂國家罪、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侵犯商業(yè)秘密罪,損害商業(yè)信譽、商品聲譽罪,虛假廣告罪,非法經營罪,誣告陷害罪,侮辱罪,誹謗罪,煽動民族仇恨、民族歧視罪,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煽動軍人逃離部隊罪等等。對于在幕后支持操縱“網絡水軍”的雇主和相關機構,對于他們也要按照刑法的相關規(guī)定進行處罰,達到治標治本的效果。
3.2 完善法律依據是治理“網絡水軍”的法律正當性要求
僅僅從源頭上治理尚不能保證“網絡水軍”危害性得到全面有效地遏制。必須對“網絡水軍”群體本身施以一定的處罰,才能從根本上消除其社會危害。然而由于缺乏明確的法律規(guī)定,“網絡水軍”群體本身的行為依據現行刑事法無法得到懲治。因此,必須完善現行刑事法,為治理“網絡水軍”提供正當的法律依據。筆者認為,有兩條路徑可以選擇,一是通過完善刑事實體法,將網絡水軍本身的行為規(guī)定為新型犯罪進行懲治,二是通過完善刑事程序法,規(guī)定新的刑事偵查措施—網絡過濾進行治理。對上述兩種路徑進行對比,筆者認為,第二條路徑對于“網絡水軍”的治理更為合理有效。首先,刑法是保障法,懲罰措施是最嚴格的,只有十分有必要訴諸刑法進行處罰規(guī)制的才能寫入刑法;其次,“網絡水軍”群體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但具體到每個“網絡水軍”個體,其行為并沒有嚴重到必須由刑法處罰的必要;再次,通過刑法對其背后企業(yè)的相關責任人及組織“網絡水軍”的公關公司的相關責任人的懲治,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刑罰預防和懲罰的功能;最后,“網絡水軍”群體龐大,調查取證難度極大,加之其中不乏無辜的“網民”實無耗費巨大的司法資源的必要。因此,筆者贊同通過制定新的刑事偵查措施——網絡過濾予以治理。
參考文獻
[1]黃學賢、陳峰:互聯(lián)網管制背景下的網絡人權保障體系初探.法治叢,2008(2).
[2]韓嘯.刑法的價值選擇機制.中國刑事法雜志.2010(06).
[3]周光清、屌宗鵬:“網絡水軍”的社會危害及刑法適用.傳媒,2016(10).
[4]葛傲天:警惕“網絡水軍”綁架網民民意.人民日報,2010—12(01).
作者簡介
解雅虹(1990-),女,山東青島,研究生,研究方向:刑事實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