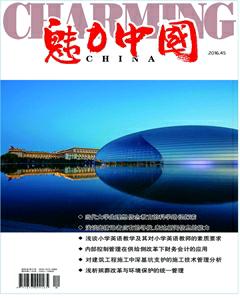黨項羌興亡及其與周邊民族政權的關系
孫秀君
【摘要】黨項羌的興盛與它構建的強大民族政權有關,而消亡則受該民族政權的毀滅、人口遷徙、通婚、民族政策等因素的影響。在這些因素影響下,民族的風俗習慣、歷史記憶及民族認同等逐漸改變,導致該族民族族稱與民族實體消亡,部分遺留于今的黨項羌遺民無法構成民族實體。
【關鍵詞】黨項羌;民族政權;關系
黨項是西羌諸部之一,其民族名稱“始于南北朝時期”。“黨項羌南北朝時分布于今青海省東南部,唐代分布范圍擴大,東至今四川省松潘,西接今新疆,南到今青海省南部,北連吐谷渾(今青海省北部)”。它不是單一的民族,而是以黨項羌為主體,融合沙陀、六州胡、回紇、氐、羌、吐蕃等族而形成的。
黨項羌按姓氏結成部落,姓氏部落有“細封氏、費聽氏,往利氏、頗超氏、野辭氏、房當氏、米擒氏、拓跋氏”。唐代時,大批黨項人內遷歸唐。到唐朝后期黨項人分居于甘肅東部的東山部、夏州的平夏部、陜北的南山部。未遷徙的黨項人最后融入到藏族中。五代時夏州李氏占據河西走廊的交通要道,成為了絲綢之路上的重要民族。到元代黨項人被改名為唐兀成為色目人之一,已不是正式的民族。此后經過不斷地民族融合,該民族逐漸消亡。
一、黨項羌政權與周邊民族政權關系
五代十國是中原內亂、政權更迭頻繁的時期,由于當時黨項族偏居西北一隅,他們利用中原王朝戰亂的有利形勢,先后與后梁、后唐、后漢等政權保持名義上的臣屬關系,但實際上利用自己獨立的政治地位乘機發展壯大,最終形成了自己的民族政權——西夏。
自唐以來黨項羌占據著河西走廊,對絲綢之路附近的民族及其政權有重要影響力。五代至宋,其東與遼、宋,南與唃廝啰,西與高昌回鶻等政權接壤,河西內部還有六谷蕃部等敵對勢力,加之該族對絲綢之路的阻斷、且長期奉行西掠吐蕃健馬,北收回鶻銳兵,后長驅南牧的對外侵略政策,因此西夏樹敵多,對外民族關系呈現復雜性、動態性與針對性的特點。
憑借占據絲綢之路必經之道的優勢,黨項羌對經過此道的回鶻商人收取重稅,“自河西回鶻朝貢中國,道其部落,輒邀劫之,執其使者,賣之他族以易牛馬”,在這些情況下,回鶻人利益受限,因此他們對黨項羌政權不滿越演愈烈。兩者曾對涼州等地反復爭奪,期間甘州回鶻始終與宋保持友好關系,而居住在涼州(今甘肅武威)附近的六谷蕃部在軍事上與北宋互為犄角共同抵御西夏。“到大首領潘羅支和廝鐸督時,曾聯合宋朝及甘州回鶻,共同對敵,抗擊西夏的侵擾,保護絲綢之路的暢通”,在這種情況下,西夏對潘羅支采取誘降措施,歸還部分投奔西夏的六谷部眾并送鐵箭利誘六谷諸首領。后潘羅支偽降,使西夏軍大敗,李繼遷在中箭逃走中死亡。但后期西夏打敗廝鐸督和甘州回鶻,涼州被奪,西夏最終取得了河西走廊整體的控制權。
河西走廊上民族戰爭不斷,致使大食等國的商人和貢使多從海上來宋貿易與朝貢,而部分走陸路的中亞商人和貢使多繞開西夏所據的河西走廊,“經過流沙迷漫的柴達木盆地,到達鄯州(今青海西寧市),然后自鄯州沿著湟水而到達宋朝的秦州(今天水市)”。這種貿易路線的更改,促進了唃廝啰政權統治地區的經濟發展,也引起黨項族的不滿。在李元昊當政期間,“就準備南侵,為解除后顧之憂,河湟地區的唃廝羅政權,首當其沖成了他的進攻目標”,而宋朝為牽制西夏多次用官位與賞賜籠絡唃廝啰首領,唃廝啰自身采取與宋結好以抗拒西夏的策略,這促使宋、唃廝啰、西夏之間的民族交織在一起,民族關系復雜化。
黨項人所居的特殊地理位置及多樹敵的現狀決定了要外尋軍事外援來謀求自身生存發展。由于契丹與宋交兵,西夏認為與遼結為外援可行,因此主動向遼稱臣,而遼又欲以西夏來牽制宋,因此兩者結成軍事外援,并通過聯姻維持民族關系。譬如遼主讓義成公主嫁李繼遷,成安公主嫁乾順等密切了遼夏關系。遼朝還幫助西夏國主乾順藥死梁氏,使其掌握國家實權。兩者之間頻繁的貿易往來更是錦上添花。譬如遼在西京、云中等地置交易場所與西夏貿易,促進了兩民族間的友好關系。
遼夏關系以和為主但也有沖突與戰爭,譬如興平公主的死亡事件使遼夏友好關系出現裂痕,此后宋夏戰爭,遼興宗表面答應李元昊對宋出兵,但實際上只駐兵幽州堅守致使李元昊不滿。加之遼境內部分黨項部落返西夏,兩民族政權由此引發民族爭端問題,關系更加不穩。譬如公元1044年,部分黨項部落離遼遷夏,元昊出兵援助并殺死遼招討使蕭普達等,由此引發河曲之戰。兩民族政權之間還因對其他民族的策略上產生過矛盾。如對宋態度上,李元昊曾為了自身的經濟利益關系考慮對遼違背盟約,單獨與宋和好。而唃廝啰與遼的聯姻,也造成了遼、西夏民族關系的不穩定。
由于西夏一直對宋圖謀不軌,宋與西夏戰爭沖突不斷。小則擄掠財物人口,大則侵奪封疆土地正是西夏對宋的戰略。因此宋夏戰爭多是西夏主動挑起,譬如三川口之戰、好水川之戰。戰爭多帶來的諸多后果如停止互市、禁青白鹽等,使兩國人民困苦不堪。如戰后西夏“死亡創痍者相半,人困于點集,財力不給,國中為‘十不如之謠以怨之”。黨項與宋的軍事對比及經濟上的互補關系等決定了誰也取代不了誰,誰也離不開誰的局面。因此和平交往才對兩族真正有利。
在與金的對外關系上,黨項羌依附于金向金朝貢,雙方建立軍事外援關系。但后期蒙古攻西夏,金棄西夏求援于不顧,言“敵人相攻,吾國之福”。因此激化兩族矛盾,彼此軍事報復不斷。兩國言和后,但因彼此消耗都成為強弩之末,隨著蒙古人的征伐,西夏先于金被蒙古人消滅。
二、民族的融合、同化與消亡
自以黨項族為主體的西夏政權崩潰以來,黨項人成為蒙古的屬民。蒙元時期,黨項羌的族稱逐漸被唐兀代替,已有去民族近族群化的傾向,成為色目人諸部之一。但蒙元時期唐兀并不完全指黨項族。“在元代,人們稱西夏為唐兀,在元人的觀念中,‘西夏人‘河西人‘唐兀人含義相近,都是泛指生活在河西地區的諸民族人,而非專指西夏的統治民族黨項人”因此唐兀人仍然是以黨項人為主體,包含生活在河西地區的其它民族。隨著戰爭、移民、民族分化政策的實施,黨項人逐漸喪失了其民族特征,嚴格的說已不是一個正式的民族“色目人并非民族、部族概念,而是人為界定的具有相近政治、法律待遇的若干族群”。
在西夏滅亡前后,黨項族處處受蒙古人牽制。由于自身的生存堪憂,該民族選擇主動融入他族以求生存。蒙古攻打西夏時,就存在部分唐兀人主動融入蒙古人的狀況,譬如“也蒲甘卜,唐兀氏。歲辛巳(1221年),率眾歸太祖,隸蒙古軍籍”。這種率眾投靠蒙古并隸屬蒙古軍籍的唐兀人并不在少數,這部分人后來大多數融入到了蒙古人當中。
在蒙古統一全國后疆域空前廣闊,蒙古人采取大規模移民措施來防控周邊民族聚族作亂,維持邊疆穩定。黨項羌作為被征服民族亦受該政策的影響。從蒙古對西夏的移民活動來看,西夏的主體民族黨項族(唐兀)仍主要留居在西夏故地,同時為了就近控制和分散監管,元朝政府多次簽發河西人到全國部分省區屯墾或鎮守,包括安徽、山東、河北,河南、浙江、江蘇、江西、四川、廣東等地都有唐兀人的存在。譬如“元初昂吉兒率領河西軍長期屯駐廬州,后他又請于兩淮屯田”。這些分散在全國各處的河西軍大部分與當地民族融合在一起,而“唐兀軍中西夏黨項人除少數上層融合到蒙古族外,絕大多數融合進漢族中”。另外由于西夏故地飽受戰爭摧殘導致農牧區荒蕪,元朝開始大量往河西地區移民屯田,屯田戶有大量來自中原與江南的漢族軍民,蒙古貴族的封地也有在河西的。中亞的回回軍在隨蒙古軍征服西夏后部分留駐在河西一帶,畏兀兒亦都護自火州遷徙到甘肅的永昌,經過這些遷徙活動,河西一帶的漢族、吐蕃、唐兀、畏兀兒等族人交錯雜居,導致民族融合進程加快,最終唐兀人被同化消亡。
家族內部的遷移活動也是導致唐兀人分散各地同化到各民族中的原因。譬如唐兀昔里氏家族,在蒙古入侵西夏的時候,就降服蒙古,“一支留居西夏故地肅州,兩支遷入中原漢地,世守大名”這種舉族式的遷徙在元代比較多,這加速了該民族的分散瓦解。族際通婚是導致唐兀人消亡的另一重要原因。譬如“唐兀賀蘭於彌氏人李世安,娶顏氏、張氏”、“察罕娶蒙古弘吉剌氏”,唐兀人改漢姓“拉吉爾威的后代以史為姓”通過族際通婚,民族間得到了深層次的交往,族群邊界得以打破,社會群體的包容性增強,族際間得到了優化重組,社會的整合度進一步增強。“自元朝中期以后,唐兀作為一個民族已經走上了民族同化、民族消亡的道路”。
明朝成為唐兀人最終被同化的關鍵階段。明朝亦采取移民措施,積極招募遷徙內地流民、罪犯前往河西屯田。還實施較多優惠政策,如在河西屯田者永不起科,世為己業等致使往河西屯田著甚眾。明朝還實行商囤,商囤移民在河西走廊加速民族融合方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明朝還從政策上強制民族同化,譬如明代還對少數民族采取了“以夏變夷的民族儒化政策”通過大力推行儒學教育同化唐兀人。明朝《大明律》規定“凡蒙古、色目人,聽與中國人婚姻。不許本類自相嫁娶,違者杖八十,男女入官為奴”。這其中的色目人就有唐兀人存在,但是相關的歷史文獻記載已經很少了。現今,還存在安徽合肥、安慶、河南濮陽、浚縣、四川、云南等地的西夏后裔,已不具備黨項族的民族特征,民族實體消亡。
三、結語
一個民族融合并同化進另一個民族的過程實際上就是民族緩慢消失的過程。這種消亡是因民族接觸層次加深、民族政權崩潰、互相通婚、更改風俗姓氏等多種因素造成的。而民族政權的崩潰在民族消亡過程中起重大作用。民族政權瓦解,民族成員的生存就會陷入困境,面臨被迫接受改變的窘境,會產生遷徙或移風易俗等諸多改變,民族的血緣關系和組織關系隨之得到稀釋,原有的民族認同就會弱化,并在不斷與其他民族的接觸中而消解。從這個方面來說,喪失了民族的文化符號和歷史記憶,民族情感就會逐漸淡薄,民族實體會逐漸消失,這無疑是滅頂之災。由此可見,把握好民族間互動與交往的度至關重要。只要把握好度,一定程度的融合不會把原有民族的相關文化特征抹去,而是在民族交往中得到某種程度上的共生共存,甚至能取長補短獲得更高層次的發展。
參考文獻:
[1]樊保良.中國古代少數民族與絲綢之路[M].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7頁,第158頁,第164頁。
[2]李蔚.簡明西夏史[M].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02—303頁。
[3]【宋】薛居正等撰.二十四史簡體字本《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八《黨項傳》)[M].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1279頁。
[4]【元】脫脫等撰.二十四史簡體字本《宋史》卷四百八十五《夏國傳上》[M].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10810頁。
[5]【明】宋濂等撰.二十四史簡體字本《元史》卷一百二十三《也蒲甘卜傳》[M].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1999頁。
[6]蔡志純.《略論元代屯田與民族遷徙》[J],民族研究,2002年第4期,第84頁。
[7]翁獨健.中國民族關系史綱要(下)[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418頁。
[8]羅賢佑著.中國歷代民族史-元代民族史[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第188頁
[9]史金波.西夏社會下[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42頁,第875—886頁。
[10]韓儒林.元朝史(上)[M].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4頁。
[11]羅賢佑.中國民族史綱要[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05頁,第270頁。
[12]張沛之.元代色目人家族及其文化傾向研究[M].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88頁,第90頁,第294頁。
[13]王鐘翰.中國民族史概要[M].山西出版集團、山西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01—202頁。
[14]劉淑紅.以夏變夷和因俗而治:明代民族文教政策的一體兩面[J],廣西民族研究,2012年第3期,第13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