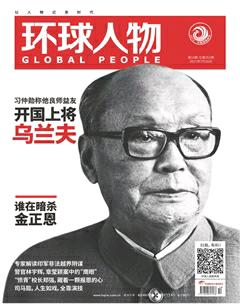特朗普被默克爾“降級”
溫憲
國際關系與人際關系大同小異,都有一個親疏分寸問題。朋友與伙伴,前者較后者多了幾分親密與倚仗,后者較前者增了幾許客氣和矜持。從伙伴結為朋友,那是雙方關系質的增進;從朋友變為伙伴,其中必有頗多難言之隱。
63歲的德國總理默克爾被媒體稱為世界上最有權勢的女性。現在,她正全力備戰9月大選。2013年,她所在政黨的競選綱領稱美國是德國在歐洲以外“最重要的朋友”,德美友誼是德國國際關系的“基石”。但今年7月3日,默克爾所在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及基督教社會聯盟在共同競選綱領中,引人注目地刪除了對美國的“朋友”“友誼”等描述,只稱美國是德國在歐洲以外“最重要的伙伴”。換言之,默克爾已經沉下臉來將美國請出了朋友圈。
德國與美國的友誼小船還真不是說翻就翻,而是經歷了相當長時間的搖晃。從更大的歷史背景來看,德美關系變化是整個世界格局正在經歷的大變動、大調整的一個方面。默克爾自稱面臨著“自兩德統一以來最艱難的局面”,她對德美關系新的定性體現出其對整個世界變化的認知與決斷。
從二戰中重新站起來的德國在很長時間內不敢怠慢美國,冷戰期間的西德更是緊緊將自己與美國綁在同一輛戰車上。朋友和朋友也不一樣。在德國的“朋友圈”中,美國一直扮演著頤指氣使的群主角色,自尊心很強的德國之所以在很長時間內不敢說“不”,皆因時勢所迫。今年5月底,默克爾說:“我們完全依賴別人的時代已過去。我們歐洲人必須比過去更牢地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言外之意便是,在剛剛過去的那個時代,德國的命運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美國人手中。如默克爾再次連任,她對美國將該斗便斗,該懟則懟,但不會撕破臉皮,畢竟還是伙伴。
在默克爾的領導下,德國是順利時力促、艱難時力挺歐盟前進的頂梁柱。在這樣一個歷史發展進程中,德國逐漸從一個對美國言聽計從的“小朋友”成長為強烈要求自立、自強、自主的平等伙伴,德美之間疙疙瘩瘩的事越來越多。早在2003年,德國便對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公開說“不”。奧巴馬當政期間,美國情報機構監聽默克爾手機的事情也鬧得沸沸揚揚,這哪里像是好朋友間應該發生的事情?
入主白宮的特朗普催化了德美關系漸行漸遠。如果尋根,特朗普的祖上還是從德國來到新大陸的呢,但特朗普對德國在北約防務負擔、貿易、難民、氣候變化等問題上的立場抨擊得讓默克爾很沒有面子,他甚至說出“德國很壞”這樣的話來。今年早些時候,默克爾耐著性子到白宮與特朗普面談,最后想握個手還遭到尷尬,當時默克爾的臉便沉了下來。此后,默克爾怒懟特朗普的烈度明顯上升。不久前,她在抨擊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政策時說:“如果有誰認為這個世界上的問題可以通過保護主義和孤立主義來解決,這個人顯然存在巨大誤解。”
有位看熱鬧不嫌大的美國雜志主編說:“1945年以來,蘇聯和之后的俄羅斯追求的最高目標,就是破壞美德聯盟。現在讓特朗普做到了。”更有人注意到,在特朗普政府孤立主義傾向日益明顯的背景下,德國和中國正在迅速接近。對于德國而言,現在最大的貿易對象是中國。對于中國而言,歐盟是最大的貿易伙伴。
西方不亮東方亮。在地球村中生活,還是朋友越多越好。無論對德國、美國還是中國,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