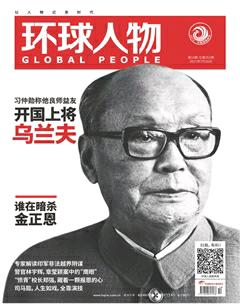畢奐午,被遺忘的詩(shī)人
李輝

“鞋匠/以麻縷系其生命/摸索于人類之足底/向炎夏走去。”上世紀(jì)30年代,他曾這樣感嘆人生、描寫“春城”。
“天一亮我將再隨著牛群/走出去/為牛群找一塊青青的草地/也為我自己/獲得一點(diǎn)點(diǎn)短暫時(shí)刻的晨曦。”上世紀(jì)80年代,他這樣吟誦“初出牛棚”的心情。
他就是畢奐午先生,于2000年2月29日逝世,享年92歲,高壽。
我與畢先生相識(shí)于1980年初。那時(shí)我還在上海復(fù)旦大學(xué)念書,每次假期回湖北老家時(shí),都會(huì)途經(jīng)武漢。那年在作家、翻譯家賈植芳先生的介紹下,我?guī)еZ先生新出版的《契訶夫手記》,第一次走進(jìn)畢先生在武漢大學(xué)珞珈山的寓所。
畢奐午是與巴金同時(shí)代的作家,而我那時(shí)正和陳思和一起研究巴金,因此,巴金成了我們初次見(jiàn)面的主要話題。
上世紀(jì)30年代,畢奐午在天津南開(kāi)中學(xué)任教,與詩(shī)人何其芳和巴金二哥李堯林共事。當(dāng)年巴金來(lái)南開(kāi)中學(xué)看望李堯林時(shí),認(rèn)識(shí)了畢奐午。巴金對(duì)畢奐午的創(chuàng)作非常欣賞和關(guān)心,不僅親自搜集、編選了畢奐午的作品,出版了《掘金記》《雨夕》兩本作品集,還為《雨夕》題寫了后記。兩本書頗受好評(píng),巴金也成了畢奐午的“知音人”。說(shuō)起這些往事,畢先生淚盈于眶。看得出,他是個(gè)極易動(dòng)情的人,苦難磨礪并未銷蝕他的純真和激情。
他和師母趙嵐待我這個(gè)初訪者非常熱情。告別時(shí),畢先生執(zhí)意把我送到公交車站,一直等我擠上汽車才遠(yuǎn)去。回到復(fù)旦后,我很快收到他的來(lái)信:
那天送你走,看到擠車的情況,真令人放心不下。你回到學(xué)校,一路舟車,還順利嗎?
……
頃有一點(diǎn)意外收獲,即我早年一本小書《雨夕》,在北京友人處有一殘本,但他不愿借出(他也是喜愛(ài)巴金著作的人),僅復(fù)制了封面與后記寄我兩份。茲寄一份給你,或可填補(bǔ)一點(diǎn)《巴金年譜》的資料。后記甚短但可看到一個(gè)大作家對(duì)他所接觸的當(dāng)年的年輕作者是多么熱情。
等到那年暑假我再去看他時(shí),他又遞給我一本巴金翻譯的赫爾岑的《一個(gè)家庭的戲劇》,1936年出版。這本書原是巴金送給他的,扉頁(yè)上還有題字“贈(zèng)奐午兄,巴金”,但在戰(zhàn)亂與漂泊中遺失了。巧的是,畢先生在朋友為他淘的一批舊書中,與這本書意外重逢。他當(dāng)即在巴金的題詞旁寫道:“1980年春節(jié),北京親友將他們新購(gòu)到的一些舊書寄來(lái)。其中居然有這樣一些書。亦悲,亦喜。”
從我讀大學(xué)、參加工作到結(jié)婚,畢先生一直通過(guò)書信給予我關(guān)懷和鼓勵(lì)。還記得我準(zhǔn)備嘗試翻譯時(shí),他在信中寫道:“翻譯工作如開(kāi)始即不要間斷,這對(duì)外語(yǔ)的提高是最有好處的。自然也不能耽誤其他學(xué)科的學(xué)習(xí)。”過(guò)了一年,他又在信中強(qiáng)調(diào):“外語(yǔ)望萬(wàn)勿丟掉。”我雖未曾在武大求學(xué),卻幸運(yùn)獲得一位武大老教授的指導(dǎo)。
1982年,我被分配到《北京晚報(bào)》工作。這份報(bào)紙畢先生和師母也有訂閱,于是好幾年間,讀晚報(bào)、談上面的作者、談老北京,成了他信中必不可少的內(nèi)容:“信接讀。我們都很惦記你。常讀到你在報(bào)紙上寫的簡(jiǎn)明而有文采的報(bào)道。師母讀報(bào)時(shí)總是先找晚報(bào)上你寫的文章看。”每當(dāng)在信中談到北京,畢先生就有說(shuō)不完的故事:
我愛(ài)人是北京城里人,我也自幼在北京長(zhǎng)大。武漢這個(gè)家,對(duì)北京鄉(xiāng)土是頗有感情的。因此,總有一份北京報(bào),偶爾看看,略解鄉(xiāng)思。《北京晚報(bào)》鄉(xiāng)土氣息重,又有你的文章,就更喜歡看了。如晚報(bào)上講的,北京官園已建兒童公園,這官園就是我們讀中學(xué)(北師)時(shí)的大操場(chǎng),一片空蕩蕩的舊端王府廢址,有好幾個(gè)足球場(chǎng)大。記得小時(shí)候,那里是我們踢球、放風(fēng)箏、春天躺在草地上仰看云雀鉆天飛叫的好地方。晚報(bào)上說(shuō)的烤肉季,也就在我愛(ài)人她們家不遠(yuǎn)的銀錠橋附近。有一次文代會(huì)我還陪巴金、麗尼幾人去那里吃烤肉……這些像夢(mèng)一樣的情景,卻又那么清晰。你在北京住久了,當(dāng)然也會(huì)漸漸地喜愛(ài)它的。
是的,我很快就喜歡了北京,喜歡這里的渾厚和龐雜,活躍與豐富。之所以如此,我想,與他們夫婦對(duì)北京難以忘懷的那種情感有關(guān)。
除了談北京,畢先生還常教我寫文藝報(bào)道。一次,我寫了篇聶紺弩的專訪,他看后來(lái)信:“聶紺弩的《散宜生詩(shī)》,應(yīng)有一兩首找人作一點(diǎn)評(píng)介和注釋,我覺(jué)得近來(lái)寫舊體詩(shī)的人,比起來(lái),都趕不上他。”這是我最早聽(tīng)到的對(duì)聶紺弩舊體詩(shī)的贊譽(yù)。
畢先生對(duì)我的幫助不止如此。我剛到北京,他就寫信給我,讓我去認(rèn)識(shí)蕭乾:
在北京我的一些老朋友中有30年代就寫報(bào)告文學(xué)的人。知名的有蕭乾。我初學(xué)寫詩(shī)文時(shí)他是《大公報(bào)》文藝副刊的編輯。同我很好。他是斯諾的學(xué)生,也是巴金的朋友。他在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工作。他的舊作最近重印了好幾部,我最近收到他寄來(lái)的一本《栗子》,他英語(yǔ)很好,口語(yǔ)流利并有英文著作。他常出國(guó)訪問(wèn),在北京遇到時(shí)可提一下,或可得到他的一些指導(dǎo)。
……你既寫文學(xué)藝術(shù)方面報(bào)道多,這樣是否可以結(jié)合實(shí)際工作再多讀一點(diǎn)文藝?yán)碚摲矫娴臅瑥募记裳芯康搅髋伤汲钡淖骷以u(píng)傳。有時(shí)間還可寫大一點(diǎn)的文章,如羅曼羅蘭寫的《米開(kāi)朗其羅》《貝多芬》那樣的論著。這是我的一點(diǎn)粗淺的設(shè)想,你當(dāng)然比我想的更切實(shí)更有規(guī)模一些。
過(guò)后,他特地寄來(lái)一封寫給蕭乾的信,讓我持信前去拜望。就這樣,我認(rèn)識(shí)了蕭乾。后來(lái)我為大家作傳,第一部就是《蕭乾傳》。初入社會(huì)的那幾年,我是在畢先生的扶持和關(guān)懷下前行。
我曾聽(tīng)畢先生講自己放牛的故事。“文革”期間,他被迫離開(kāi)教學(xué)崗位,下放到農(nóng)場(chǎng)做“放牛娃”。為此,他曾把名字“奐午”戲稱為“喚牛”。那段日子,他常仰望天空,觀察星辰,不僅學(xué)習(xí)天文學(xué),還用天文學(xué)研究古詩(shī)歌中有關(guān)日月星斗的內(nèi)容。他曾寫信給我:“前見(jiàn)晚報(bào)有一篇講蘇東坡的文章,涉及天文學(xué),甚感作者對(duì)天文所知甚少(歷來(lái)一些講古典文學(xué)的,凡遇描寫星空的地方,因是‘天文盲大都講錯(cuò)了),有感于此,寫一短文,供副刊編輯部參考。”這是磨難帶給他的意外收獲。
在我認(rèn)識(shí)畢先生的時(shí)候,畢奐午這個(gè)名字已被人們遺忘,因?yàn)樗辉儆形膶W(xué)作品問(wèn)世,也不參加諸多文壇活動(dòng)。他默默地躲在珞珈山那間房子里,與書相對(duì),與學(xué)生相對(duì)。然而,他并未對(duì)文學(xué)忘懷。
我曾在復(fù)旦大學(xué)圖書館里借到《掘金記》,便寫信給他,大概還胡亂謅了幾句詩(shī)。他回信寫道:
你對(duì)我那一本早年的小書,稱許過(guò)多,愧不敢當(dāng)。但那些青少年時(shí)代的文字,寫得還認(rèn)真,情意都不虛假。就像看兒時(shí)的照片,癡容憨態(tài),都還一片天真,往往不覺(jué)其難看,反而不免有一點(diǎn)憐惜、愛(ài)悅之情。記得《掘金記》初版出書時(shí),師友們也給予過(guò)譽(yù)的獎(jiǎng)勵(lì)。其中《春城》一首有句云:“鞋匠,以麻縷系其生命,摸索于人類之足底,向炎夏走去。”還有散文《人市》個(gè)別句段,都是人們常常說(shuō)念它們的。這些想起來(lái)已如夢(mèng)如煙。但我覺(jué)得應(yīng)注意的還是努力現(xiàn)在。這些就讓它隨時(shí)光流逝而消失了吧。今天,你居然遇到了它,而且又看了,又寫了熱情的詩(shī),這在我是多么感激而又慚愧的事啊。
在這封信里,他產(chǎn)生了重新寫詩(shī)的念頭和熱情:
你鼓勵(lì)我,我一定再寫詩(shī),我們一起努力寫。我這一老而衰弱的文藝兵卒,要緊緊跟上你們這支生龍活虎的隊(duì)伍。再學(xué)著寫,不管形式怎樣,不管像不像詩(shī)。火原是以各種狀態(tài)飛舞著,只要是真火!
1980年底,畢先生創(chuàng)作了《初出牛棚告白》之一,隨后在1981年1月,寫了之二、之三。雖只有三首,卻是他沉寂多年后的詩(shī)情迸發(fā)。這幾首詩(shī)在《詩(shī)刊》發(fā)表時(shí),許多人驚喜地感嘆,畢奐午還活著,他又寫詩(shī)了!此后,畢先生把一份抄寫的“暫定稿”寄給了我。我將它們和其他來(lái)信一起珍藏著。
我最后一次看望畢先生,是1998年,還是在珞珈山那套破爛不堪的寓所。如今,在畢先生去世17年后,我重新翻閱手稿,仿佛看到他在清晨走出牛棚,牽著牛,向遠(yuǎn)處走去。頭上,漫天星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