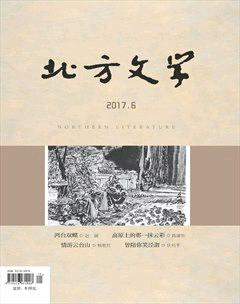從《益世報》文藝副刊看李長之的魯迅批評
鐘星辰
《益世報》文藝副刊創刊共35期,李長之時任編輯,平均每期都有文章發表。文藝副刊的創刊原則與發表立場都可作為李長之個人文學觀念的注釋,李長之在文藝副刊上發表的關于魯迅的批評更是其批評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益世報》文藝副刊可以透視李長之的魯迅批判的形成過程,也可以詮釋李長之批評精神與批評立場的獨特之處。故李長之在《益世報》文藝副刊上刊發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李長之在三十年代的批評家地位,也為李長之批評理論的生發、批評體系的構建奠定了基礎。
一、《益世報》文藝副刊與李長之批評家地位的確立
《益世報》文藝副刊在創刊時的發刊詞中提到“本刊提倡批評精神,堅持學術立場,吹散浪漫精神,贊助翻譯,推行文藝教育”[1],這些都是李長之批評精神和立場的體現。李長之身體力行地翻譯外來著作,同時他一直堅持批評家要保持獨立的批評精神,“批評是反奴性的,凡是屈服于權威,屈服于時代,屈服于欲望,屈服于輿論,屈服于傳說,屈服于多數,屈服于偏見、成見,這些都是奴性,都是反批評。”[2]李長之一直建立一個自由、獨立的批評王國,在這個王國中,李長之為自己找到合法的身份認定和價值認同。
李長之在《益世報》文藝副刊中,刊登了6篇文章專門闡釋其批評思想、5篇書評評論詩歌等現代作家作品、11篇文章用以評價與討論魯迅,此外還有對外國文學的介紹、詩歌創作等[3]。從發表概況來看,李長之在文藝副刊上主要是開展他的魯迅批判。11篇關于魯迅批判的文章中,有9篇文章被結集成《魯迅批判》于1936年出版,另外兩篇《<熱風>以前之魯迅》與《魯迅著譯工作的總檢討》并未收入《魯迅批判》一書中,《魯迅批判》的出版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表現了李長之自身的批評立場的選擇和批評角度的確定,而未收錄人《魯迅批判》的兩篇文章也體現了李長之“魯迅批判”的他質。《益世報》文藝副刊中刊登的李長之的批評文章闡釋了他的批評思想,而他對魯迅的批判研究更是讓他被學界關注,甚至是魯迅自身也與李長之有過通信往來。李長之在這些魯迅評論集中闡釋了魯迅的創作機制、創作心態、作品解析等多方面的內容,在這些內容的論述中,李長之用自己的評價標準搭建了心中的魯迅,并成功將自己的批評理論付諸實踐,“魯迅批評”與李長之自身的批評觀念形成了相互影響、相互生發的張力場。
二、“環境—性格—創作”的“魯迅批評”思路
《魯迅批判》是第一本魯迅生前就出現的專著,也是魯迅研究史上的第一本系統地專論。在《益世報》文藝副刊上,李長之主要從魯迅的生活環境與階段、創作態度與作品的藝術鑒定、思想評價等方面入手,全面考究魯迅其人、其文的獨特價值與魅力,以此李長之得出了一個結論:魯迅的人格是完整的,魯迅的作品中有完整的優秀作品的代表。另外,文藝副刊中未結集入《魯迅批判》一書的兩篇文章也在側面彌補了《魯迅批判》的不足,也起到了為后世對李長之的某些評價進行辯護的作用。
首先,李長之從魯迅生活的環境與性格形成二者之間的關系著手,梳理了魯迅的精神史,以及他在各個階段下的精神狀態,與在這種狀態影響下的創作。李長之用筆于討論世界對作者的影響,如何與作者精神追求共同作用于作品。換而言之,李長之思考了客觀環境對魯迅的影響,和魯迅自身的知識結構、精神力量二者在魯迅創作中的體現,即長之遵循的批評的三個出發點“作品、作家、一般文化狀況”[4]。例如長之在《導言:魯迅之思想性格與環境》中就說“魯迅從小康之家而墮入困頓,生長于代表著中國一般的執拗的農民性的魯鎮,這似乎是偶然的,然而卻影響了、形成了他的思想、性格和文藝作品”[5],李長之認為魯迅的家境變化、生存環境極大地影響甚至決定了他的思想與創作,這種通過影響研究做下判斷的做法李長之將之運用得駕輕就熟。
其次,李長之通過環境的變化,和魯迅在不同環境中的獨特選擇,揭開了魯迅的性格面貌與人格特征——完整的人格與情感的病態。李長之對魯迅在性格上做的判定與評估是:“他在情感上病態是病態了,人格上是全然無缺的”[6]。“完整”是李長之的批評理念中一個重要的概念,所謂“完整”延伸到人格層面,則是“真”。在李長之看來,一個優秀的文學工作者必不能缺少的就是“真”的品質。魯迅是真實的,“他的為人極真,在文字中的表現尤覺誠實無偽”“對于事情極其負責……與人相處,更其不茍……他自己則是勤奮的。”[7]但李長之又認為,魯迅在情感上是病態的。他雖良善卻很多疑;雖不茍與人相處,卻不善與人相處;雖常談世故,卻最是不世故的;所以他孤獨于世而不被人理解。在李長之筆下,魯迅不僅僅是一個戰士,一個積極的反抗者,反倒魯迅身上有許多非正常的病態和偏執。魯迅不是神壇上高高在上的主宰者,而是踽踽獨行的凡人中最堅韌的一個。
最后,李長之通過對魯迅的生存環境及其個性的闡釋,分析了魯迅創作的藝術特色和作品的價值。李長之認為魯迅實現了思想的戰士與藝術的詩人的二者結合。一方面,魯迅因為“人得要生存”故要不斷地攻擊反抗,他攻擊封建思想,痛斥奴性與卑瑣,擯棄舊制度與舊文明,在思想是一個戰士;另一方面,魯迅情感極其的熱烈,他的筆是抒情的,魯迅最成功的作品也是抒情性強烈的作品。“含蓄、凝練、深長的意味,和豐盈充溢的感情”[8]都充斥在他為數不多的抒情作品中,故在文藝上魯迅也就毫無問題的能稱得上是一個詩人。長之認識到了魯迅身上復雜的情緒狀態與情感態度,他認為“強烈的情感,和粗暴的力,才是魯迅所有的”[9]。表現在具體作品上,李長之將魯迅的創作內容大致分成寫農民與寫小市民兩類群體。李長之將“執拗的農民性”提煉出來,反復闡釋,他認為“魯迅更宜于寫農村生活,他性格上的堅韌、固執、多疑,文筆的凝練、老辣都似乎不宜于寫都市。農村,恰恰發揮了他那常覺得受奚落的哀感,寂寞和荒涼。”[10]李長之認為,魯迅在理智上是向上的,所以他對向上者格外的寬宥;同時,情感與理智并非是相悖的,寫農民,情緒飽滿,力透紙背,哪怕是李長之眼中并不出彩的小市民描寫,雖匆忙,也同樣是有情感的。故在理智與情感、詩人與戰士之間,李長之為魯迅找到了中間點和合理的存在價值。
李長之的《魯迅批判》在建國以后的文壇引起了許多非議,就如陳鳴樹的《批判李長之的“魯迅批判”》和譚丕模的《從<魯迅批判>到<文學史家的魯迅>》就是從階級立場嚴厲批判李長之是右派分子,對魯迅做的論斷是有階級陰謀的。直到1980年司馬長風的《李長之【魯迅批判】》出現,李長之對魯迅的批判和評價才開始慢慢地被正面接受。而后來的很多評論家都認為李長之對魯迅“注重做藝術分析,而忽略做思想分析”[11],事實上,李長之未結集入書的《<熱風>以前之魯迅》就對魯迅做了思想分析。而李長之結集《魯迅批判》的時候,更多的是側重在藝術上的評價與抉擇,這與他自身的批評立場有關,《魯迅批判》的結集即體現了李長之自身的批評結構,也展示了自我的批評精神與立場。
三、“魯迅批評”中的自我建構
李長之在《益世報》文藝副刊中較為系統的開展了他的“魯迅批評”,這種系統性為李長之多方面的批評體系的生發奠定了基礎。在“魯迅批評”中,李長之建構了自己的文學觀念和批評態度,從特殊的個體研究中抽離出來,我們能獲取一般的關于李長之的批評價值體系。
第一,李長之最為系統的批評觀念就是“感情的型”的批評方式。在“魯迅批評”中,李長之并未提及“感情的型”這一詞,但在整個魯迅的評價分析中,就從未脫離“感情的型”的核心理念——情感。其實感情的型最終依舊歸結于對“情感”的要求,這種情感是形式化與個性化的統一。而“魯迅批評”中,李長之一而再再而三的強調魯迅情感的變態與強烈,不管是從容的抒情還是匆忙的憤怒,都是情感的一種表現形式。所以,魯迅的創作從總體上來看,是充斥著情感因子的,在這個程度上,“魯迅批評”與李長之的“感情的型”的批評主義是一脈相承的,是論據與論點、具體與抽象的關系。
第二,李長之在文藝副刊上的“魯迅批評”與結集出版的《魯迅批判》是有出入的,最明顯的是《<熱風>以前之魯迅》與《魯迅著譯工作的總檢討》并沒有收錄到《魯迅批判》中。《魯迅批判》的文章選擇其實就體現了李長之自身的批評體系的建構。不管是溫儒敏對李長之進行“傳記批評”的定位[12],還是許道明對其“京派批評”的定性[13],其實都在一定程度上確認了李長之對作家“抒情性”的強調,甚至是對“無功利”“純藝術”的期待。李長之在《魯迅批判》中意識到了魯迅的情感特質,對魯迅進行評價時,也流露出對其抒情作品的獨特欣賞與偏愛。李長之在評價魯迅時,也更側重與對魯迅的藝術作品進行分析討論,從而突出自己對創作、藝術本身的強調。或許是出于這一點考慮,對魯迅的著譯工作以及思想論證也就并未收入到《魯迅批判》一文中去。
第三,李長之對魯迅的批評是站在自己的標準之上的客觀評價。一方面,他堅守了自己的批評標準,不論是“完整”“從容”,還是“抒情性”,這些方面的強調是他批評體系中的一般理論和固守的原則。另一方面,李長之有自己的評價標準,但他的評價仍舊是相對客觀的。在這個標準衡量下的魯迅,并不是十足的偉人,或者是全然的刻薄者,魯迅的為人為文在李長之看來都是有兩面性的,好壞兼具,優劣具顯。不可置否,李長之對魯迅是有著別樣的熱情和鐘愛的。總的來看,魯迅在李長之眼中,是時代精神的倡導者,是永恒價值的傳遞者。李長之期待文壇出現魯迅這樣的戰士和詩人,期待批評界出現對魯迅更為細致、有價值的評價。所以,李長之對魯迅研究的期待,是對文學創作中情感因子的期待,也是對評論界的出現有價值的批評的期待。
總之,《益世報》文藝副刊促生了李長之的“魯迅批評”的系統出現,李長之自己也說“倘若不是天津《益世報》文學副刊,感到稿件之少,這篇東西怕還是得遲些時日動筆,”[14],同時文學副刊的“魯迅批評”與結集的《魯迅批判》二者之間又有復雜的聯系,這種聯系在一定程度上是李長之自我批評立場抉擇的體現。同時“魯迅批評”本身也建構了李長之的批評精神與批評觀念之一隅,故有闡釋與論證的價值與意義。
參考文獻:
[1]益世報[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4影印版.
[2]李長之.李長之文集( 第三卷 )[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155.
[3]益世報[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4影印版.
[4]李長之.李長之文集( 第三卷 )[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199.
[5]李長之.李長之文集( 第二卷 )[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7.
[6]李長之.李長之文集》( 第二卷 )[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98.
[7]李長之.李長之文集( 第二卷 )[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98.
[8]李長之.李長之文集( 第二卷 )[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37.
[9]李長之.李長之文集( 第二卷 )[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90.
[10]李長之.李長之文集》( 第二卷 )[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63.
[11]張蘊艷.李長之學術—心路歷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58.
[12]許道明.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 ( 新編 )[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
[13]李長之.李長之文集》( 第二卷 )[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4.
[14]李長之.李長之文集》( 第二卷 )[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