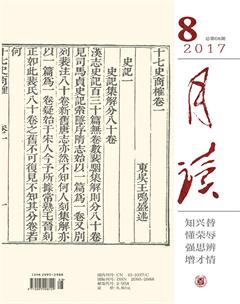嚴格管理,考核為先
侯建良
中國古代考核制度源遠流長。據古籍記載,舜的時候就實行過“三載考績,三考黜陟”(黜,罷免;陟,升遷)的定期考核辦法,以后逐步完善,一直到清末。古人在長期的用人實踐中,根據用人的實際需要創造了若干不同的考核形式:有結合任期的定期全面考核,稱為“考課”“考績”“上計”“考滿”等;有以廉政、整頓官員隊伍為目的的考核,稱為“刺察”“訪察”“京察”“外察”等;有以選拔任用為目的的考核,一般稱為“考察”等。這些考核形式相輔相成,構成了 一個完整的考核體系。
考核是一項不可或缺的人事管理制度。古人認為,考核的作用主要有二:一是“察賢否”(否,音pǐ,是壞或惡的意思),考核是識別人員行為善惡、能力大小的重要手段,考核結果可以作為對人員實施升降去留的直接依據;二是“明功過”,通過考核明確人員有哪些成績和過錯,賞功罰過,對人員直接起到激勵進取、督促工作、監督行為的作用。
正因為考核有如上作用,所以古代政治家對考核歷來重視。唐太宗曾經說:“考核官員業績的優劣,并以此決定對他們的罷免或升遷,這是古往今來國家普遍實行的制度。”a貞觀六年(632),有一次魏徵在與唐太宗討論用人問題時說:“知人善任,自古以來就是一件難事,所以要通過考績來決定官員的升降,了解他們的善惡。”a魏徵在這里講的考績,就是指的定期考核制度,唐朝一年一考,四年(地方高級官員是三年)決定升降。魏徵認為,只有通過考核來決定官員的升降,才能減少用人上的失誤。
清乾隆二年(1737),乾隆皇帝對內閣有一大段諭旨,特別強調了“察吏”的重要性,對各地長官不注意考核下屬大為不滿,著實發了一頓脾氣。其中說道:“從來為政之道,安民必先察吏。所以,作為督撫這一級擔負封疆重任的高級官員,應該懂得除了做好察吏這一工作外,別無其他根本辦法能使百姓安居樂業,自到任之初,就應當認真考察,廣泛征求意見,詳細鑒定識別,核查是否名實相符,聽其言觀其行,務求找到能夠提出治國良策、教化百姓的人才,從而不辜負我廣求人才的心意。”b實際上,將“察吏”當作治理國家的首要任務,并不是乾隆皇帝的獨有認識,而是統治者長期治國的經驗總結和共識。林則徐將這一經驗概括得更簡潔:“立政之道,察吏為先。”③
既然考核作用重大,那么如何才能做好考核工作呢?古人在這方面有很多經驗值得借鑒。
(一)務求嚴格,防止流于形式
再好的制度,如果不嚴格執行也是枉然。各個朝代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考核不認真,甚至流于形式的問題:往往是朝代前期做得比較認真;中期如果有的皇帝振作一下,出現“中興”局面,考核也會趨于嚴格;其他時期不認真的情況比比皆是,特別是每個朝代的末期,吏治敗壞,朝典廢弛,考核僅有其名,而無其實。據《唐會要》載:“自至德(唐肅宗年號)以后,考績部門所搞的考績結果大多失實,能經常上朝的京官及各州刺史,從來不分好壞,都給予‘中上考。”a考核如果不分等次,彼此一樣,那考核也就無法成為升降賞罰的依據了。這種狀況自然會引起一些有責任心的官員的憂慮和反對。唐德宗貞元七年(791),考功郎中上奏說:“自三十年以來,各部門都一律給本機關人員申報‘中上考。按照考課的本義,考課結果是不應雷同的。如果這樣下去,事久因循,朝廷制度恐怕就要廢掉了。”b這無疑是在皇帝面前對考核不認真的積弊敲了一次警鐘。
大致說來,唐朝的考核工作還算比較好的,其他朝代考核不認真的問題更加嚴重。以清朝為例,考核不認真的問題一直不同程度地存在,直至清末;朝廷對考核不認真的嚴厲批評和對考核工作的嚴格要求,倒也從未間斷。
據記載,清代給官員寫的“考語”(考核鑒定),經常出現“拘泥對偶,組織浮詞,抄謄舊案,虛應故事”的問題③。考核鑒定全由對偶的華麗詞句組成,很多考語還是從往年的考核鑒定里抄錄過來的,這樣的鑒定自然是毫無用處,只是“具文”而已。乾隆七年(1742),皇帝諭旨批評說:“近來各省計典(指地方三年一次的‘大計考課),頗有視為具文、茍且塞責者。”a乾隆十年(1745)十月,乾隆皇帝又在給內閣的諭旨中,對一個叫圖爾炳阿的巡撫提出了嚴厲批評,原因是“他對全省屬員的考核鑒定,都是只有優點而沒有缺點”,“千人一面漫無區別”。乾隆皇帝指出:“巡撫肩負考察全省官吏的職責,注意發現和合理使用人才的事情最關緊要,若是考核鑒定人才的事做不好,那擔任這樣的重任怎么能夠稱職呢?”b他講得非常到位,既對不重視考核工作的敷衍態度進行了嚴厲批評,又從高級官員是否稱職的高度對領導的考核工作提出了要求。
(二)客觀公正,防止弄虛作假
考核制度的生命力,在于能對被考核者作出客觀公正的考核評價,即考核結果要客觀公正。考核結果能否客觀地反映事物的本來面目,受很多因素影響,但最能影響“客觀”的因素,就是能否做到“公正”。考核不公正,就不可能得出客觀的考核評價。所以,保證考核效果,公正是關鍵。而各個時期的考核是否公正,與當時的吏治好壞和官場風氣密切相關。
考核不公的問題有各種各樣的表現,最為常見的,一是寬上嚴下,欺軟怕硬,雙重標準;二是以恩怨好惡為轉移,考核結果嚴重失實;三是以考核為交易,賄賂請托,營私舞弊;四是借考核之機打擊報復,黨同伐異,顛倒黑白。如此種種,直接影響了考核結果的客觀真實性。考核失真,自然就難以作為升降賞罰的真正依據,當然也就起不到整頓吏治的實際作用。所以,歷代明君賢相無不強調公正考核的重要性。例如,乾隆皇帝有一段關于考核的諭旨就講得比較到位,他是這樣說的:“國家舉行‘大計(地方官員的定期考核),這是每三年舉行一次考績,并決定升降賞罰的重要制度。各地總督巡撫按照職責應管好這件事,一定要秉公去私,杜絕請托,精心認真地進行鑒別,不得借機拉同伙、搞偏向,要做到提拔一人而眾人都受到激勵,罷免一人而眾人都受到教育。這樣一來,官場便得以整肅,吏治便得以清明,各個管理部門的工作就會順利開展,百姓生活就會因此受益。”a這段諭旨強調的重點,就是要求考核做到“秉公去私”。這跟我們現在強調堅持公正原則是一個意思。
(三)考核務實,與任用、獎懲相結合
考核不是擺樣子,不是為考核而考核。考核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有用。考核的用處,就體現在考核結果要與任用、獎懲相結合。考核結果如與任用、獎懲不掛鉤,考核的作用就會變得蒼白無力,長此以往,考核便無人重視,形同虛設。
北宋知名學者李覯對當時“考績”中存在的升降賞罰不與考核結果掛鉤的弊病,進行了不留情面的批評。他說:“有功者晉升,有過者貶退,無功無過者職務不動,這樣就可以激勵有功者而懲罰有過者。然而現在的考績卻不是這樣,而是無功無過者晉升,這就意味著晉升不必有功;有過者仍然擔任原來的職位,這就意味著有過也不會被貶退。像這樣有功勞無益處,有過錯也無損失,那激勵和懲戒的作用又體現在哪里呢?”a
盡管在實際考核中,一些地方長官和單位領導將考核視為具文,敷衍塞責,但歷代關于定期考核(考課、考績)的規定里,都明確要求考核結果要分出等次,并按等次進行升降賞罰。兩漢時,考核好的稱為“最”,差的稱為“殿”,“最”者或升或賞,“殿”者或降或罰,即所謂“歲盡(年末)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②。北魏孝文帝下詔規定,“三年一考,考了就升降”,并規定“考其優劣為三等”,“上等的升遷,下等的貶降,中等的保留原職務”。③唐代考課結果分為九等,一年一小考,根據考核結果實行加祿或減祿的賞罰,四年一大考,決定官階的升降。宋代一年一考,三考為一任,“定為三等,中等的不賞不罰;上等的或者升轉官職,或者縮短任期,提前進行任滿考核;下等的或者降官,或者延長任期考核的年限”④。明代三年一小考,九年一大考,結果分稱職、平常、不稱職三等,根據考課結果,還要參考原任職務的繁簡程度,決定獎罰;獎賞一般是晉升官階等次,有時還采用升職、蔭子(給孩子安排工作)、封贈(給家人封號)、加祿等激勵辦法;處罰一般是降官階等次、罰俸,太差的要降三四等,甚至不安排官職而“雜職內用”,直至罷免回家。清代的考課,既包括對“才、守、政、年”的全面考核,也包括對“貪、酷、疲軟、不謹、年老、有疾、才力不及、浮躁”等八類問題的考察,稱為“八法”(“八法”考察始自明代,但當時未列入定期考核之中);全面考核合格的升級,被列為“一等”(京官)或“卓異”(地方官)的列入候選升職名冊,“貪、酷”者革職提問,“疲軟、不謹”者革職,“年老、有疾”者退休,“才力不及、浮躁”者酌量降調。
關于考核與賞罰的關系,宋代學者蘇洵有一段論述堪稱精辟,他是這樣說的:“有官員就要有考核,有考核就要有賞罰。有官員而無考核,就等于無官員;有考核而無賞罰,就等于無考核。”a如果沒有考核,那就等于對官員隊伍無管理,只是虛置官位而已;如果考核不與賞罰掛鉤,那考核就沒用了,考核制度便形同虛設。這兩句話言簡意賅,概括了考核的作用以及考核必與賞罰掛鉤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