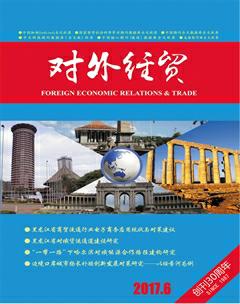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緣起及經濟效應分析
黃丹蕾
[摘要]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是源于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推動,由于中國與東盟各國在空間上相連,自貿區的建立便于國與國之間的要素流動,可實現互利共贏并深化相互合作。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立以來,在貿易、投資、產業結構以及規模經濟等方面產生了良好的經濟效應。
[關鍵詞]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經濟效應;經濟全球化;區域經濟一體化
[中圖分類號]F06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283(2017)06-0037-03
當今,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趨勢愈加明顯,區域合作成為現代區域經濟發展的普遍現象。各區域之間通過優勢互補和資源共享,創造出分散條件下無法取得的經濟效益。1991年7月,中國時任外長錢其琛出席第24屆東盟外長會議開幕式,開始了中國與東盟的對話,經過長期的接觸,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簡稱CAFTA)于2010年1月1日正式全面啟動。自貿區建成后,東盟和中國的貿易占到世界貿易的13%,成為一個涵蓋11個國家、19億人口的巨大經濟體,是世界人口最多的自貿區,也是發展中國家中最大的自貿區。
一、文獻綜述
對于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立的原因和意義,我國許多學者已經做過深入的研究。王玉主(2006)提出,中國經濟依靠引進外國直接投資和出口導向的增長一直面臨著一種兩難的困境,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對于緩解這種困境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1];雷小華(2013)認為,中國的廣西、云南兩省與東盟各國在資源等方面有著較強的互補性,并且雙方的地方政府在發展邊境地區經濟的問題上都表示出了強烈的合作意愿,因此促成了自貿區的建立[2];馬繼憲(2015)則認為自貿區的重點發展區域——中越邊境的區位優勢使交通運輸更加便利,并提出了越南經濟迅速發展和中越兩國友好關系的重要意義[3]。對于經濟效益這一方面,何慧剛(2006)認為,關稅降低導致了區內進口成本高的產品被區內進口成本低的產品所替代,從而增加了貿易量,同時區內成員國之間關稅的減少及更緊密的關系導致區內成員國把原來從區外非成員國的低成本產品進口轉換為從區內成員國高成本產品的進口[4];姜文仙(2010)與何慧剛(2006)有相同的觀點,但同時提出了自貿區促進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實現資源優化配置的投資效益[5];陶岸君(2010)認為,自貿區的建立雖在國家層面上合作大于競爭,但在區域層面上使經濟欠發達的桂、滇、越三地的競爭大于合作[6];程永林(2004)從抵御其它區域一體化組織發展帶來的經濟貿易集團化對中國出口市場的沖擊和加強中國與東亞地區的國際分工和互動增長關系兩個方面論述了區域合作的收益[7]。總之,自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立以來,學者們主要從區域經濟學的視角分析其成立的原因,本文將基于經濟地理學和區域經濟學的雙重視角對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成立的原因及經濟效應進行研究。
二、中國—東盟自貿區的緣起
(一)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推動
1990年以來,經濟全球化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趨勢。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廣泛流動,生產過程和服務所涉及的地域不斷向全世界擴展,從而使世界各國(地區)經濟相互依賴性增強。而消除或減弱貿易壁壘,生產要素趨于自由流動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則反映了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新特點和世界多極化曲折發展的新趨勢。在這一趨勢下,WTO成員紛紛與相關的國家(地區)建立起區域合作,如1993年建立的歐盟和1994年建立的北美自由貿易區。
經濟全球化不僅使各國之間的聯系加強,同時也加劇了區域間的競爭。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迅速增強,并且出口貿易和引進外資也在迅速地增加,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影響力也日益凸顯。但中國國內市場發展還較為落后,且出口主要依靠的是廉價的勞動力,如果不做出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優化,中國經濟未來的發展將面臨嚴峻的挑戰。因此,為了在應對國際競爭時有一個較大的平臺和依托,中國主動提倡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認為與東盟在10+3框架下率先啟動自由貿易區進程,是對東亞合作的重要貢獻,必將對東亞地區的融合產生深遠影響。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順應了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規律,對中國在出口市場上擺脫對歐美國家的過分依賴有著重要的作用。
(二)中國與東盟各國在空間上相連,便于要素流動
從經濟聯系的角度看,區域之間在空間上相連便于要素流動,有利于展開合作。在地理位置上,云南、廣西兩省與東盟中的緬甸、老撾、泰國接壤。尤其是越南,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規劃中六條經濟走廊五條都經過越南,并且越南與中國海陸相連,沿岸分布許多港口作為水陸交通的集結點和樞紐及工農產品和外貿進出口物資的集散地。越南抓住國際產業轉移的機遇,發展出口貿易,吸引了大批國際企業落戶越南,成為世界經濟復蘇最快的區域之一。與越南接壤的廣西是唯一與東盟國家既有陸地接壤又有海上通道的省份,南瀕北部灣,面向東南亞,有良好的區位條件,并且享受多項優惠政策。2008年初,中國批準實施《廣西北部灣經濟區發展規劃》,廣西北部灣經濟區開放開發正式納入國家戰略,為未來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物資交流、信息交流等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因此,中越邊境成為中國—東盟自貿區發展的重點區域。
中國和東盟都屬于發展中國家,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資源。以廣西和越南為例,兩地礦產資源都很豐富,如猛、鋁、錫、鐵等,但東盟國家對地質工作的投入相對不足,礦業政策不夠完善;兩地的勞動力都較為密集,但隨著中國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勞動力成本也在不斷提高;兩地都處熱帶和亞熱帶,農業發達,是熱帶農產品的主要產地。由此可見,兩地的區域合作一方面可以聯合開發資源,另一方面也可以優勢互補,互通有無。
(三)中國與東盟各國實現互利共贏的需要
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九屆中國-東盟商務與投資峰會暨2012中國—東盟自貿區論壇開幕式上的致辭中說:“在經濟全球化、區域一體化深入發展的新形勢下,中國和東盟的前途命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不斷深化中國—東盟戰略伙伴關系,是雙方共同的戰略選擇。”菲律賓前總統拉莫斯在此間全球腦庫論壇壓軸演講中也說到,中國經濟的穩定增長為東南亞各國帶來發展機遇,東盟加上中國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貿易區,將產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應[9]。
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不僅能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也有深遠的政治意義。中國與東盟在經濟上有著很強的互補性,地理上與東盟相依相連,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有利于中國與東盟經濟實力的增強和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有利于彼此贏得信任與支持,減少經濟發展中的摩擦和阻力;有利于彼此經濟制度安排日益適應經濟全球化發展的要求;有利于彼此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并在貿易、投資及市場準入等方面與國際經濟全面接軌;有利于增強彼此在經濟全球化中的應對能力。
(四)中國與東盟各國有相互合作的歷史淵源
中國與東盟國家在地理位置上較為接近,在亞太經合組織、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中都有合作。20世紀90年代初期,中國由于改革開放,經濟發展迅速,并且開始融入地區經濟,剛好冷戰結束,新加坡、馬來西亞等東盟國家的企業家中掀起一股在華投資的熱潮,中國與東盟開始進行經濟貿易。1991年7月,中國時任外長錢其琛出席第24屆東盟外長會議開幕式,與東盟組織進行了首次接觸,自此中國外長每年都出席東盟外長會議。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使亞洲許多國家受到重創,同時也拉近了東亞各國之間的關系。2000年起,中國除了與周邊國家建立友好的政治關系外,開始全面發展區域合作的經濟關系。盡管受世界經濟不景氣和“9.11”事件的影響,中國和東盟的貿易仍呈增長勢頭。東盟已成為中國的第五大貿易伙伴,而中國則成為東盟的第六大貿易伙伴。2003年中國加入《東南亞友好條約》,被認為是雙邊政治互信進一步加強的標志。雙方有著共同的利益和需求,在長期的友好合作中互惠互利,并且雙方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發展邊境經濟,有著建設跨境經濟區的強烈意愿,由此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成為必然。
三、中國—東盟自貿區建立的經濟效應
(一)貿易創造效應和貿易轉移效應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成后,逐年降低成員國的關稅是一個重要的步驟。依據《中國—東盟經濟合作框架協議》規定,中國與東盟雙方從2005年開始正常產品的降稅,2010年中國與東盟老成員國將建成自由貿易區,2015年中國和東盟新成員國建成自由貿易區,屆時中國與東盟絕大多數產品將實行零關稅。關稅的降低產生了貿易創造效應和貿易轉移效應。貿易創造效應是指, “自由貿易區建立后,隨著各成員國關稅水平的削減和取消,區內進口成本高的產品被區內進口成本低的產品所替代,較低的進口價格增加了貿易量,使原先不可能發生的貿易被創造出來,從而提高了進口國的經濟福利”[4]。在自貿區建立之前,中國和東盟為了保護國內市場,相關產業的關稅較高,加之鄰近區域相似的文化背景導致相似的消費者偏好,關稅的降低能夠較大程度地刺激雙方的貿易。其次,中國與東盟的產品有較大的互補性,中國的工業制成品和東盟各國的自然資源相對來說具有較大的優勢,在對方國家也有較大的市場需求,因此能產生貿易創造效應。中國和東盟都屬于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相對落后,出口的商品主要為食品、紡織品等勞動密集型產品,進口的商品主要為精密儀器、設備等資金技術密集型產品,并且主要的貿易伙伴都是日本、韓國、美國、歐洲各國等。因此,中國和東盟雙方之間的貿易無法代替各自與發達國家貿易伙伴之間的貿易,即使自貿區擴大了中國和東盟的貿易來往,也難以從中獲得貿易轉移效應。自由貿易區是獲得利益還是帶來損失,取決于貿易創造和貿易轉移二者的綜合影響。中國和東盟雙邊貿易額在1991年是79.6億美元,到2015年雙邊貿易額達到4721.6億美元,年均增長18.5%,雙邊貿易額占中國對外貿易額的比重由1991年的5.9%上升到2015年的11.9%。[10]從目前看來,自貿區給中國帶來了較大的貿易效益。
(二)產業結構的調整
中國和東盟同屬發展中國家,產業結構有較多相似之處,使雙方之間有較大的競爭。中國面臨產業結構的調整,基本方向是由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向以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為主轉變,由初級加工工業向深加工工業轉變,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對中國而言,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首先可以給中國提供來源穩定且成本更低的石油、橡膠等能源和原材料;其次,自貿區為成員國之間創造更有利的環境,為中國的高新技術產品提供了更廣闊的市場;第三,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建立后,區外的企業為了享受自貿區的關稅優惠,只能選擇在區內進行投資,外資的不斷流入為產業結構的調整提供了資金,在吸引外資的同時也引進了先進的技術和管理方法等。對東盟而言,也有了加大技術投入、發展優勢產業的機遇,并且可以以制造業內部的分工和貿易為導向,推動在東南亞沿海地區經濟發達城市形成產業帶,發揮集聚效應,實現區域貿易合作的動態收益。總之,兩地的企業在自貿區建立后想要在更激烈的競爭中獲得一席之地,必須引進先進的技術和管理方法,培養優秀的人才,不斷創新,實現技術上的升級,降低生產成本,獲取更大的利潤,而這必然會帶動整個產業結構的變化。目前,中國的產業結構調整已經有了一定的成果,總體按照“配第—克拉克定理”所揭示的規律進行,即隨著經濟發展,人均國民收入水平相應提高,勞動力就開始從第一次產業向第二次產業轉移;當人均國民收入水平進一步提高時,勞動力就會向第三次產業轉移,因此第一產業的比重迅速下降,第二產業穩步發展,第三產業呈上升態勢。但要憑中國或東盟中單個國家的實力實現產業結構升級還較為困難,因此必須堅持區域合作,雙方分工協作,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使雙方都實現產業結構升級。
(三)規模經濟
規模經濟是指隨著規模擴大而帶來的效益增加。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成后將形成一個近2萬億美元的國內生產總值、1.2萬億美元貿易量的經濟區,是由發展中國家組成的最大的自由貿易區,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由貿易區,有著極大的市場需求和勞動力,為規模經濟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條件。自貿區的建立、關稅的逐漸減少使中國與東盟各國的生產要素和產品的自由流動性變強,各國發揮自身的優勢,形成了更合理的國際分工,生產經營更專業化,每個國家集中發展自身的優勢產業,生產較少品種的產品,便可擴大該種產品的生產規模,實現規模經濟。另外,自由貿易和生產要素的自由轉移使中國和東盟都面臨著巨大的競爭,在這樣的強壓下,企業必然尋求技術創新,引進先進的技術和人才,提高勞動生產率,實現生產結構的優化和升級,同時擴大中國與東盟互補性商品的市場,帶動各自國內企業資金的投入,實現規模經濟。
綜上所述,在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大趨勢下,中國選擇與東盟建立自由貿易區,是由于地理位置的聯接以及東盟良好的區位優勢;雙方實現政治和經濟上互利共贏的需要以及雙方長期合作建立起來的友好關系和良好默契。自貿區建立之后,給中國與東盟都帶來了一定的貿易效應和投資效應,促進了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并且逐步實現了規模經濟。
[參考文獻]
[1]王玉主.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合作的緣起與利益分析[C].廈門大學南洋研究院50周年慶暨“當代東南亞政治與外交”學術研討會大會手冊,2006-09-01.
[2]雷小華.中國—東盟跨境經濟合作區發展研究[J].亞太經濟,2013(3).
[3]馬繼憲.中國—東盟自貿區框架下的跨境經濟合作區建設[J].國際經濟合作,2015(3).
[4]何慧剛.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經濟效應分析[J].云南社會科學,2006(3).
[5]姜文仙.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經濟效應分析[J].東南亞南亞研究,2010(1).
[6]陶岸君.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對我國區域發展格局的影響與對策[J].經濟地理,2010(5).
[7]程永林.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與我國的地緣經濟利益研究[J].昆明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3).
[8]習近平在第九屆中國-東盟商務與投資峰會暨2012中國—東盟自貿區論壇開幕式上的致辭[EB/OL].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09/21/c_113166298.htm.
[9]菲前總統拉莫斯:東盟加中國將產生1+1>2的效應[EB/OL].中國新聞網 http://www.chinanews.com/2002-11-19/26/244893.html.
[10]中國與東盟雙邊貿易額年均增長18.5%[EB/OL].瞭望新聞周刊網http://www.outlookweekly.cn/yaowen/11499.html.
(責任編輯:郭麗春董博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