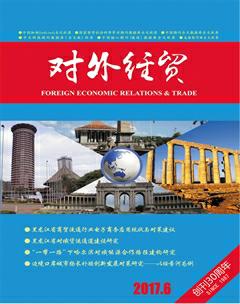發展型社會政策視角分析欠發達地區失地農民欠發展問題
[摘要]失地是城市化進程中的必然現象,失地農民的生存和發展問題日益得到社會的關注,已有研究表明欠發達地區失地農民發展還存在一定的欠發展問題:物質資本喪失嚴重、人力資本更新不足、社會資本積累有限。發展型社會政策視角對欠發達地區失地農民的發展問題提供了解決思路:重視失地農民物質資產積累的同時,有必要通過國家和社會力量介入以引導失地農民群體的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的建設和積累。
[關鍵詞]失地農民;欠發展問題;發展型社會政策
[中圖分類號]F7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283(2017)06-0138-05
[作者簡介]劉曉麗(1971-),女,漢族,江西吉安人,副教授,碩士,研究方向:社會政策、社會工作理論與實務。
[基金項目]江西省教育科學 “十二五”規劃2015年度項目資助(項目編號:15YB074)。
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是我國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的首要任務。失地農民的產生是城市化進程和農業現代化的必然結果,失地農民是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群體。在欠發達地區,基于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的各種現實因素,對失地農民一般采取一次性現金補償(補償標準由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附著物補償費和青苗補償費等構成)。手握一定資金的失地農民本應在失地后逐漸完成城市化和現代化發展,卻出現了一些欠發展問題,而這可能成為其成功城市化的阻礙。
一、我國欠發達地區的失地農民面臨的欠發展問題
我國欠發達地區的城鎮化并非完全始于工業或者其他非農產業的發展,一定程度上存在地方政府主觀提速推進的城鎮化。因此,欠發達地區城鎮化之中的失地農民發展問題更應引發社會關注。從已有研究看,欠發達地區失地農民一定程度上面臨資產受損以及資本準備不足等欠發展問題。
(一)土地喪失,其他物質資本和家庭資產不足
已有的調查研究表明,[1]失地農民在土地征用后,最為重要的自然物質資本土地喪失程度最高,受損嚴重,導致收入數額和水平降低,雖然有一定的貨幣補償或其他方式的補償,但因采用綜合補償方式,補償項目少且補償標準低,大部分失地農民生活水平和質量比不上城市居民,而城市化工業化發展趨勢中失去的土地資本并不能失而復得;欠發達地區擁有房屋、店鋪、廠房、大型機械(汽車、吊車、挖掘機、摩托車等)等可以增值的物質資本的失地農民家庭比例偏低,其帶來的收入比重不高;存款、利息等數額與全國平均水平相比偏低;租金、紅利等金融資本情況分布不均,兩極分化;股息在失地農民中并不被熟悉和接受,比例特別低。
農民失去土地后,擁有的其它可以賴以生存的物質資本并不充足,個人和家庭資產長期積累也無法實現,從而無法促進失地農民個人、家庭、社區的長期發展。另外,欠發達地區失地農民面臨現有資產或財產保護以及保值增值的問題。因為較少接觸現代投資和現代生活方式,欠發達地區失地農民獲得了一定數量的土地補償金后,由于沒有合適的投資或使用渠道,又面臨一些不良誘惑,涉毒、涉賭和奢靡消費事件時有發生,部分失地農民及其家庭面臨一些重大的發展風險。
(二)面臨社會保障的可持續性困境
國家陸續出臺了完善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的社會政策,2014年《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規定,2016年后各省陸續取消區分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統一登記為居民戶口。同時擴大基本公共服務覆蓋面,在養老、就業、醫療、住房等方面給與社會保障;《國務院統一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意見》(國發[2014]8號)指出,城鄉居民養老保險的主要籌資方式是由個人繳款、集體補助、政府補貼構成,待遇有基礎養老金和個人賬戶構成,支付終身;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十三五”規劃要求健全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制度,在農村以在城鄉之間流動就業和居住農民為重點,鼓勵持續參保,完善并落實多繳多補、長繳多得、助殘扶貧等政策,適時提高最低繳費檔次;《國務院關于整合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意見》(國發[2016]3號)要求整合新農合和城鎮居民醫保,建立城鄉統一的居民醫療保險制度。這一系列的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將包括失地農民在內的所有城鄉公民納入了基本社會保障體系內[2]。
但是,欠發達地區失地農民相比有土地收益的農民和一般城市居民而言,其持續參加養老和醫療社會保險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十分突出。另外,部分失地農民安排集體宅基地,集體遷移新居,住房有保障。而有些失地農民獲得補償金后自行安排住宅和生活,解決住房問題的方式有租房、自購房、自建房、廉租或公共租賃房等,住房保障也充滿了不確定性。主要是因為:人均土地補償費用的不足,可支配收入低;部分失地農民后續收入不穩定,持續繳費能力弱;參保的籌資方式比較單一,主要有個人和政府補貼承擔;失去土地后的生活方式和就業壓力使得失地農民日常生活消費開支項增多;補償費用資金的保值增值水平不高。
(三)就業安置相對不力
國家統籌城鄉就業,建立健全城鄉勞動者平等就業制度,拓寬了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渠道,促進了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就業和外出務工人員返鄉創業;推行終身職業技能培訓制度,構建覆蓋城鄉全體勞動者、貫穿勞動者學習工作終身、適應勞動者和市場需求的職業培訓制度,完善市場配置資源、勞動者自主選擇、政府購買服務和依法監管的職業培訓工作機制,全方位提升人力資本質量和勞動者就業創業能力。但由于國家提供的就業保障缺乏切實法律保障和資金不足,欠發達地區本地區城市接收勞動力就業能力弱,政府能提供的再就業崗位比較有限,無法滿足失地農民再就業的需要。現有就業培訓體系以政府辦學為主,覆蓋了省市縣三級,但較少推廣到鄉鎮及農村基層[3];培訓內容豐富性不足,無法滿足失地農民向職業化農民轉化的需要以及和非農就業需要;培訓師資配備單一及培訓方式較為陳舊;培訓實踐設施老化,以課堂和視頻為主,鮮有實踐機會。培訓客觀上對失地農民沒有吸引力,加上失地農民文化水平較低,參加培訓的主觀積極性較低,因而在勞動力市場上就業競爭乏力,極易陷入半失業或無業境地。
(四)風險防范與利益表達行動能力較弱
欠發達地區失地農民權益難以保障的根源在城鄉二元結構,現有國家土地征用制度、法律制度以及社會保障制度還沒有充分保障失地農民的利益。失地農民面臨的可持續生存風險在現有戶籍制度、福利制度、就業制度強化下無法得到有效防范,容易面臨資產風險、收入風險、福利風險等,未來陷入貧困的可能性較大。另外,在征地過程及社會保障的利益博弈中,與其他利益主體相比,失地農民的利益表達、集體行動能力和資源不足,一般處于相對弱勢的地位,其利益保護和風險防范能力十分弱小。
(五)適應性、社會融合、心態危機等問題持續存在
失地農民的社會生產和生活方式發生了斷裂式變化,從農業生產到亦農亦工亦商再到完全非農職業,最終完全不同于農村的生產方式,或依靠自身技能外出務工、開店,或本地從事小生意、保潔、維修,或無所事事; 從自由安排生產生活的安逸農村生活過渡到備受約束的較快節奏的城市生活,從諸多的自給自足的生產消費到所有吃穿住用行處處花錢的市場經濟生活,從獨門獨院到許多公共空間的安置小區房,從方便走家串戶的農村住房到由物業管理的封閉獨立的高樓套房等,不僅生活成本提高,許多失地農民行為習慣和心理上更面臨諸多不適應。[4]
在征地利益受損體驗后,失地農民又感受到的非農生存以及融入城市的困境與不安。在整個社會結構場域中,失地農民感受到了明顯的“比較落差”以及在結構中的無力感,這些感受體現在對于自身處境的悲觀以及改善可能性的否定,以及對于導致這種社會分化的原因的否定與不滿。已有研究也表明,失地農民群體存在普遍的焦慮、不信任、群體性怨恨、負面情緒等心態危機。[5]
二、從發展型社會政策視角看失地農民欠發展問題的根源
從發展型社會政策理論視角看,在較低水平的國家社會保障條件和較低的失地農民自身能力素養的實際情況下,欠發達地區失地農民融入城市是有限的,其帶來的社會風險將深遠影響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這些問題存在的根源在于失地農民群體擁有的社會資本和人力資本有限。
(一)發展型社會政策要義
20世紀90年代以來,“發展型社會政策”作為一種新的社會政策范式受到理論界和實務界的重視,人們開始形成了共識,即福利的提供既不能完全依賴政府,也不能單純依靠市場,而是需要構建一種積極性社會政策,使社會各個成分都能夠在福利體系中充分發揮作用。發展型社會政策受到人力資本理論和社會資本理論的影響:
1強調人力資本在社會福利中的比重。發展型社會政策理論代表吉登斯認為,建設社會投資國家不僅可以解決福利國家本身的問題,還可以增強各國在經濟全球化壓力下的競爭力[6]。建立社會投資國家的基本原則是盡量在人力資本上進行投資,而不是給予直接的經濟援助。提供費用較高的普遍福利已經成為不可能的選擇,社會福利支出只有用于人力資本的投資和增加個人參與經濟的機會才具有可行性。欠發達地區失地農民的社會福利保障投資應該重視人力資本的投資。
2強調促進個人資產長期積累的社會政策。社會政策的重點不應再放在傳統的收入再分配上,而是應該促進個人資產的長期積累,以推動個人、家庭和社區的發展。“社會投資”理念被另一位發展型社會政策學者美國華盛頓大學的邁克爾&謝諾登教授進一步發展為“資產為本的社會政策”。在《窮人與資產》一書中,他首次提出了“資產為本”的社會政策觀,主張社會政策的重點應該強調授權于個人,促進個人資產的長期積累,以推動個人、家庭和社區的發展,并以這種發展構成社會整體的長期發展。邁克爾&謝諾登認為擁有資產除了能維持消費以外,還可能產生其他積極的影響,如更確切的未來觀、更穩定的家庭、更多的人力資本投資、更妥善的財產管理、更積極的社區參與、增加個人效能感、增加社會影響等。[7]欠發達地區失地農民可持續發展需要個人資產支持個人、家庭發展的人力資本和社區發展等社會資本的投資。
3強調社會資本作用的社會政策。發展型社會政策思路從以消費和維持為導向的服務轉向提高能力、投資于民、擴大經濟參與和促進經濟發展的干預[8]。發展型社會政策包含一些重要理念:社會變遷和社會進步;社會干預和集體行為;普遍主義、平等和社會包容;協調社會政策和經濟政策等等。美國社會政策學者米奇利認為這些理念在實踐中體現為系列“社會投資”行為,如投資于人力資本、就業和創業計劃、社會資本、資產發展、社會計劃;消除經濟參與屏障等[8]。處于弱勢的失地農民的發展問題不應該僅僅停留于滿足維持消費,更可以傾向于為其進行“社會投資”。
4強調提升社會質量水準的社會政策。“社會質量化理論”是發展型社會政策的主要理論成果之一,“社會質量”被界定為“民眾在提升其福祉和個人潛能的條件下,能夠參與社區的社會經濟生活的程度。”為了達到可接受的社會質量水準,必須滿足四個條件:一是人們必須有機會獲得社會經濟保障,不管是來自就業還是來自社會保障,以便使自己免于貧困和其他形式的物質剝奪;二是在勞動力市場之類的主要社會經濟制度中,人們必須體驗社會融入,或使其所遭受的社會排斥最小化;三是人們應能夠生活在以社會整合為特征的社區和社會中;四是人們必須在一定程度上自主并被賦予一定的權能,以便在社會經濟的急劇變遷面前有能力全面參與。這四個基本條件決定了社會關系朝社會質量方向發展的機會。滿足這四個條件,人們才能獲得社會質量能力。[9]失地農民群體的“社會質量”還遠沒有處于可接受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其享有應該的福祉和成果。
(二)欠發達地區失地農民欠發展是人力資本更新不足和社會資本積累有限的結果
欠發達地區失地農民面臨的資產受損以及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準備不足等是影響失地農民及其家庭、社區長期發展的核心要素。提高土地征收補償費用,使失地農民得到公正充分的市場化補償,是解決失地農民欠發展問題的重要舉措,也取得了一定的實踐效果。但提高補償費并不能必然支撐失地農民持續生計和適應發展的雙重需求,且土地征收補償的公平市場化也要有必要的法律制度性保障。
1失地農民個體和群體擁有的社會資本缺乏與社會制度性保障不足和社會排斥問題的弱性循環
布爾迪厄認為,社會資本是由“社會義務或聯系組成”,“是那些實際的或潛在的資源的集合體,這些資源是對一個相互熟識和認可的、具有制度化關系的持久網絡的擁有,也即與一個群體的成員身份聯系在一起。” “特定行為者占有的社會資本的大小,取決于他可以有效加以運用的網絡規模的大小,或者與他有聯系的每個人依靠自身的身份所占有的(經濟的、文化的和符號的)資本的大小。”[10]嵌入在社會關系網絡中的社會資本能夠通過其信息功能、影響功能、社會信用功能和強化功能而在行動者的工具性行動和表達性行動中獲取預期收益。[11]
從失地農民個體和群體本身看,社會資本是具有失地農民身份的“那些實際的或潛在的資源的集合體”,這些資源是與失地農民群體的成員身份聯系在一起。失地農民能有效運用和占有社會資本很小,因而再獲得制度性保障的社會資本、關系性社會資本也就小,形成一個弱性循環,在各種緊急情況下,能夠獲得或者將會獲得社區或網絡提供的幫助是有限的,從正式制度上獲得的支持也是有限的。
失地農民制度關系和制度結構的社會資本貯備不足。首先,對于土地征收補償市場化的法律制度保障嚴重不足。我國沒有專門的土地征收法律,有關征地的法律規定僅限于《土地管理法》中的部分規定,且規定不夠詳細具體,尤其是征地補償為綜合性補償,補償項目沒有進行細化,在征地事件中引發一些不滿和抗爭。其次,失地后的福利制度性保障不夠。失地農民有一定的失地補償和基本生活保障,當前及以后相當長時間生活暫時不存在經濟困難。國務院2006年4月10日就出臺過《關于建立被征地農民培訓就業和社會保障制度的意見》,但因為地方經濟水平和財力不足,欠發達地區失地農民社會保障水平較低,教育培訓就業也沒有得到制度上的保障。這些不足又和失地農民的社會關系網絡和組織集體行動等方面的社會資本是密切相關的。
失地農民的社會信任、道德規范和社會網絡等關系性社會資本少。欠發達地區經濟建設和社會建設相對滯后,城市化社區建設不完善;失地農民面臨生活方式現代化和城市化,很多生活習慣在城市不被認可,集中安置失地農民的城市小區被市民認為是不宜居的,對這一群體產生不信任和落后沒文化沒教養等標簽化認識。由于失地農民沒有充足人際交往及社會融合空間,對失地農民在勞動力市場中的職業發展產生了消極影響。就是說,失地農民關系性社會資本占有很少,因而在新的生存環境中失地農民個體及其家庭、集團型社會組織之間所擁有的社會信任、道德規范和社會網絡等關系性社會資本無法有效增加。
失地農民參與不充分,采取有效集體行動不足。欠發達地區失地農民因共同面臨失地問題,在處理土地補償、具體安置等實際問題時失地農民有一定的參與機會,但因為文化素養等限制,參與能力并不強,再加上居住和就業多樣化,異質性日顯明顯,組織化程度低,相對弱小的失地農民群體在面臨公共問題和追求共同利益時參與并不充分,采取有效集體行動不足,因而無法有效爭取獲得個體和群體性社會福利保障。
總體上看,失地農民的欠發展問題不僅是經濟因素造成的,更是觀念、規范、制度、信任以及相關的其他社會資本的赤字造成的,同時,欠發展問題又強化了失地農民的社會資本不足。
2失地農民人力資本不足與就業、醫療健康和收入保障的不確定性的相互強化
舒爾茨認為人力資本主要指凝集在人身上的知識、技能、經歷、經驗和熟練程度等,表現為人的智力與體力的總和。其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大于物的資本所發揮的作用。[12]人力資本不僅包含才干、知識和技能,而且還包含時間、健康和壽命。根據人力資本內涵,人們一般會從健康狀況、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經驗來測量人力資本情況。
失地之前,農民農村生活和農業生產經驗豐富,體力勞動能力強,吃苦耐勞,但其擁有的非農產業的人力資本是有限的。失地過程中,欠發達地區失地農民相當部分是被動參與城鎮化,是在非農產業發展不足以支撐失地農民收入來源及數量不減少的情況下的被迫失地。從主觀意愿上看,失地農民的失地行動不是其自主理性選擇的結果,沒有為此做好充分的人力資本準備和積累。失地后,農民處于對以后生活的無準備的慌亂和迷失中,并不充足的土地補償費一般用于必要的生活消費型開支和家庭資產的積累,沒有理性計劃和切實安排用于教育培訓和健康保障上的人力資本支出。
欠發達地區失地農民普遍受教育的年限偏少,學歷水平不高,有非農職業一技之長的比例、參加技能學習與培訓比例很低,獲得非農職業從業資格的比例更低,從事農業之外的其他職業的工作經驗有限。相當多的失地農民因為環境惡化、不良生活方式和飲食習慣等原因,身體健康狀況還存在諸多問題。失地農民人力資本在非農職業就業競爭中處于劣勢,由此引發其收入保障和持續參加社會保險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又強化了失地農民在人力資本上的投入和付出的不足。
綜上,欠發達地區失地農民欠發展問題就是其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不足從而社會質量低下的體現,是其在提升其福祉和個人潛能的條件欠缺、參與社區的社會經濟生活的程度不足的表征。
三、解決欠發達地區失地農民問題的路徑思考
國家和社會以及失地農民自身應認識到不斷爭取保障和更新其社會資本、人力資本與積累物質資本、金融資本同樣重要。
(一)提升失地農民社會質量
使失地農民有機會獲得社會經濟保障,不管是來自就業還是來自社會保障,以使其免于貧困或一定形式的物質剝奪;在勞動力市場等主要社會經濟參與中,考慮失地農民體驗社會融入,或使其所遭受的社會排斥最小化;能夠生活在以社會整合為特征的社區和社會中;給與失地農民群體一定程度上的自主并賦予其一定的權能,以便其在社會經濟的急劇變遷面前有能力全面參與。
(二)健全征地法律,保障失地農民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建設的物質基礎
土地是失地農民曾經最重要的發展資本,土地征用時應科學公平考慮土地的增值功能,進行合理估價,提高征地補償水平。通過制定專門的征地法律,保障失地農民在貨幣財富有所補償,使其生存與發展有物質基礎作保障,同時在征地補償中增加人力資本培訓和發展費用項目,提供其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投資建設的物質基礎。
(三)社會力量引導失地農民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建設
失地農民個體最基本的需求是可持續生計的需求,就是保障各種收入來源的需求,其中起關鍵作用的是發展失地農民的社會資本和人力資本。欠發達地區失地農民的發展,最終要通過失地農民自組織建構,緩解自我排斥,促進社會融合;要通過社區能力建設和失地農民自身能力建設,獲得自我發展機會與能力。在優勢視角下,以能力建設和資產建立為核心,發掘失地農民社區和農民的資產和能力,使得社區和民眾成為當地農村發展的主體。這種內生力對于當前的失地農民來說還不夠,可能需要一定的外在力量的介入和幫助。通過有效的教育培訓等行動干預失地農民個體、群體和社區進行積極干預。開展失地農民社區教育,提高其城市適應性,培養其現代性,以滿足其現代化需求,提高失地農民群體的“社會質量”。
總之,從發展型社會政策理論視角看,在較低水平的國家社會保障條件和較低的失地農民自身能力素養的實際情況下,缺少社會資本和人力資本的失地農民融入城市是有限的,其帶來的社會風險將深遠影響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在發展型社會政策視野下,以社會投資為導向,國家應該在政府主導下發動各方力量對欠發達地區失地農民的發展進行積極干預,盡量在人力資本上進行投資,提高參與市場競爭的能力,而不是給予直接的經濟補償和援助;盡量投資和積累失地農民的社會資本,提高其適應性,培養其現代性,以滿足其現代化需求。其中,對失地農民個人、家庭和社區進行教育與培訓成為這種干預的主要渠道。
[參考文獻]
[1]黃建偉.失地農民可持續生計研究[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13:76-87,107—108,109—110.
[2]趙定東,袁麗麗.村改居居民的社會保障可持續性困境分析[J].浙江社會科學,2016(12).
[3]孫建家.做好失地農民就業培訓工作的對策探討[J].現代經濟信息,2016(21).
[4]周畢芬.社會排斥視角下的失地農民權益問題分析[J].農業經濟問題,2015(4).
[5]胡鵬飛.社會底層:結構機會與心態危機[J].福建論壇,2016(11).
[6][英]安東尼·吉登斯. 第三條道路:社會民主主義的復興[M]. 鄭戈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132.
[7][美]邁克爾&謝諾登.資產與窮人:一項新的美國福利政策[M]. 高鑒國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207—217.
[8][美]米奇利.發展型社會政策:理論和實踐[A].張秀蘭,徐月賓,米奇利.中國發展型社會政策論綱[C].北京: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2007:163—175.
[9][英]艾倫·沃克.21世紀的社會政策:最低標準,還是生活質量?[J].社會政策評論,2007(1):3—27.
[10][法]布爾迪厄.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202.
[11]林南.社會資本——社會結構與行動的理論[M].張磊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18—20.
[12]西奧多· 舒爾茨. 人力資本投資——教育和研究的作用[M].北京: 商務印書館. 1990:22—43.
[13]李惠斌.社會資本與社會發展[J].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0(2).
[14][美]托馬斯·福特·布朗.社會資本理論綜述[J]. 木子西編譯.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0(2).
Abstract: Land loss is an inevitable phenomenon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Some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 land-lost farmers still have some underdevelopment problems in underdeveloped areas: the loss of material capital, the lack of human capital renewal, social capital accumulation is limited.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policy perspective provides beneficial inspir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blem of land-lost farmers: the importance of land-lost farmers physical asset accumulation.At the same time, it is necessary to guide the land-lost farmers to construct and accumulate human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by the state and society.
Key words: land-lost farmers; underdevelopment problems;the developmental social policy
(責任編輯:郭麗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