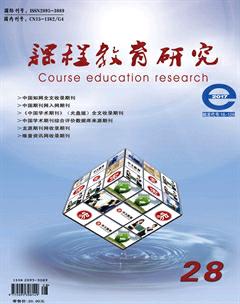楚文物形象上的文化烙印及楚舞的風格尋覓
【摘要】楚文物上的形象造設往往是一種帶有隱喻性的符號,這些符號表達著楚文化的內涵與宗教信仰。楚舞的風格特點與楚文物上這些獨特的形象造設有著緊密的聯系,在許多方面還呈現出一種異質同構的關系。楚文物上的這些圖案形象給當代楚舞研究提供一定的參考,能通過透析其中所隱喻的文化內涵,進行更為深入的研究,開拓當代楚舞復現與創編中其舞蹈身體語言所要表達的內容,明晰其表達的文化主旨,找出楚舞的風格特點。從楚文物的形象造設所隱射的文化信仰中體會出楚人的審美心理結構去進行楚舞的研究、復現甚至是當作品的創作不失為一條值得探索的道路。
【關鍵詞】楚文物 形象造設 楚舞 審美心理結構
【基金項目】該文為國家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楚舞形態及文化研究”(課題編號:15YJC760032)階段性研究成果。
【中圖分類號】G6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089(2017)28-0010-02
楚學家們認為,楚,既是民族的概念,又是國家的概念,也是地域的概念。作為兩周時期的南方大國,楚國擁有著燦爛的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其龍飛鳳舞的氣質與氣場、悠久的歷史內涵、燦爛的文化在史籍、詩詞、歌賦甚至多種文物的造型與圖案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構成東方文化的典型代表。楚文化在與在與中原文化的分庭抗禮中自成一格,體現出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蘊。楚文化在與中原文化交相輝映之時,體現出其獨特的魅力。楚文化親鬼好巫,力求浪漫與感性,其中,楚舞流傳久遠,如《楚辭·招魂》就描寫當時宮廷貴族間的樂舞生活,楚霸王項羽的《虞兮歌》都是楚聲, 再如漢高祖劉邦的《大風歌》中就會有“舞楚舞”,劉邦寵姬戚夫人,本魯定陶人,而史稱其“善楚舞”……楚文物形象上的文化烙印與楚舞的風格有著必然的聯系,對楚舞的研究、當代復現以及舞蹈創作都具有重要的價值與意義。
一、現象與內涵:獨特形象造設隱喻性符號的呈現及其內涵
楚國是一個神秘的國度,有著深厚的文化積淀與豐富的文化傳說。我們從已出土的許多文物中能發現諸多奧妙,窺見許多久遠的神話故事在此棲息,如在一些喪葬用品、絲織物上的繪畫,以及器皿的裝飾圖畫、木雕以及青銅雕塑上都能看到許多“有意味的形象”。這些獨特的形象造設訴說著神秘而久遠的神話傳說,其濃郁的巫風之氣、厚重的歷史話語似乎都在這些形象造設之中隱約呈現與依稀透射。
楚地集長江流域先秦時期神話傳說之大成,其中諸多的典籍中保存了諸多的神話故事。如《楚辭》中就保存了豐富的神話故事材料。同時,楚文物上有著大量神話題材的圖像造設,這與楚人對神話的追隨與人們心中的“神仙思想”有著緊密的聯系。可以說,楚文物上許多獨特的形象造設構成一種“有意味的形象”,承載著寓意深遠的神話故事。如從楚墓中發掘出來的諸多文物喪葬品,如絲織物上的繪畫、器皿上的裝飾圖畫、木雕以及青銅雕塑上所表現的神話故事如“十日扶桑”、“夸父追日”、“羽人神話”等等都是楚文物承載著神話故事的例證。這些獨特的形象造設往往是一種帶有隱喻性的符號,這些符號表達著楚文化的內涵與宗教信仰。
無論是楚文化典籍還是楚墓出土文物,它們所承載的神話故事往往能為當今楚舞研究、當代復現,甚至舞蹈作品的創作提供豐富的創作題材,也為楚舞的創作營造了一種風格。縱觀我們目前的楚舞作品創作,較多是對對現存的舊時楚地的傳統民間歌舞形式進行考察與借鑒而作的歌舞作品,如《編鐘樂舞》(1983)和《鐘鳴楚天》(2003)等等;或是抓住楚國女樂舞的姿態造型特點進行的女子舞蹈作品的編創,如《楚腰》(1997)等等;或是表現具體歷史人物故事的大型舞劇類作品。可以說,目前有關楚舞的創作對神話題材的攝入還并不多,題材內容還比較單一,棲息于楚文物上的久遠的神話故事無疑可以給當代楚舞的研究、當代復現與作品編創提供一定的研究方向與創作題材,對當代楚舞創作題材的拓展起到積極的作用。
二、尋覓與聯想:“異質同構”下楚文物形象造設與楚舞風格的聯系
“異質同構”可謂是“格式塔”心理學的核心理論。格式塔心理學派認為在外部事物的存在形式、人的視知覺組織活動和人情感以及視覺藝術形式之間,有一種對應關系,一旦這幾種不同領域的“力”的作用模式達到結構上的一致時,就有可能激起審美經驗,這就是“異質同構”。“異質同構”對于我們感受藝術起到魔力般的作用。正是在這種“異質同構”的作用下,人們才在外部事物和美術品的形式中直接感受到類似于“活力”、“生命”、“運動”“平衡”等性質,產生出獨特的審美經驗。楚舞是楚文化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楚舞的風格特點與楚文物上這些獨特的形象造設有著緊密的聯系,在許多方面還呈現一種異質同構的關系,使不同的東西能在人們心里產生相同的審美效應。楚文物上的這些圖案形象給當代楚舞研究起到一定借鑒作用,能通過透析其中所隱喻的文化內涵,將其進一步融入到舞蹈的表現中,開拓當代楚舞復現與創編中其舞蹈身體語言所要表達的內容,明晰其表達的文化主旨,找出楚舞的風格特點。
(一)飄逸與流暢韻致互映,精巧與新奇風格共現。
楚國的文化藝術呈現出浪漫與理性交織的特點,在華夏與蠻夷風格混融的過程中體現出其獨有的風格韻致。如楚文物上的圖案、造型等形象造設往往具有飄逸、流暢、靈動、精巧、新奇的特點。楚人的思想往往開闊自由,他們的藝術想象力常常能大膽突破理想與規范的制約而自由馳騁、放蕩不羈。我們從楚文物那些流光溢彩的漆工藝、美麗繽紛的服飾工藝、鬼斧神工的雕刻、姿態萬千的龍鳳紋、舒卷自如、綽約多姿的云紋、變化多樣的幾何紋、活靈活現的人物紋以及惟妙惟肖的動物紋中都可以看出楚人在藝術品上對飄逸流暢與精巧新奇審美風格的追求。如1982年湖北江陵馬山1號墓出土的“舞人動物紋錦”的圖案中,舞人舞姿翩翩、瀟灑飄逸,峨冠鳳鳥長尾曳地。此“舞人動物紋錦”上的一些紋路與色調都極為精巧與別致,如其上的龍紋、麒麟圖案以及溫色調等等都使整個畫面顯得明朗歡快。又如 1982年湖北精靈馬山1號墓出土的“龍鳳虎紋繡羅單衣”的圖案由龍、鳳、虎纏繞穿插排列,呈現出一種縈繞飄逸、神妙奇特之美,極其富有浪漫氣息。
楚之禮樂可以說是乘自中原,但其中也有不乏楚人的創造,其中不可避免地會融入了楚人的生活風尚和審美趣味,這樣才會形成獨具風韻的楚樂舞藝術。楚國的文化藝術既有中原文化藝術所具有的凝重、典雅、簡樸的特點,同時又融入了楚地的靈性,有著活潑、靈動,甚至是繁縟的元素特點。根據審美的共通性以及“異質同構”原理,我們是否也能推測出楚舞的某些風格可能也會呈現出這樣一種飄逸流暢與精巧新奇的審美特點?事實上,中國古代文獻的記載或傳說中就有過相關楚舞風格的描述,其中較多就具有美輪美奐、精巧絕倫、瀟灑飄逸的特點。因此,聯系起其他楚藝術的審美表達與風格韻味,對我們聯想與推測出楚舞大致的風格韻味也有一定的幫助。
(二)升騰與魔幻交織,怪誕與奇譎風格互映。
楚文物形象造設上升騰與魔幻交織、怪誕與奇譎風格互映的審美風格對楚舞的探尋有著重要的啟示作用。以20世紀40年代湖南長沙出土的《人物龍鳳帛畫》中的形象造設為例,帛畫中貴族女子的“細腰”與“廣袖”充分展現了楚文化中女性外形的審美追求與生活習慣。又如帛畫的上方有鳳鳥展翅飛翔與夔龍騰空遨游的形態,這展現出一種“飛升”的動勢,這種獨特形象造設是一種隱喻性的符號,與楚文化中“龍鳳導引靈魂‘升天”有關。當代對楚舞的探尋則可以從其中所隱射的文化信仰中體會出楚人的審美心理結構,從而在當代楚舞復現或作品創作的風格韻律上把握一種“巫風”之氣。編舞者能在一種“異質同構”之下,通過帛畫的上方有鳳鳥展翅飛翔與夔龍騰空遨游的形態尋找出楚舞的一種意境與風格。
又如1973年于湖南省長沙市子彈庫一號墓出土《人物御龍帛畫》中男子的裝束與氣質為當代楚舞中男子形象的創作提供了參照:戴高帽、身穿博袍、腰配長劍,人物衣著的飄帶隨風飄起……該帛畫中“龍昂首卷尾,躬身成舟,舟尾立鶴(鳳),周旁有一鯉魚隨行。”[1]大多數學者認為是一幅“引魂升天”圖。楚人好巫,楚人迷信人的靈魂可以四處游蕩,甚至可以歸為天神,這種“魂幡”便是源自于楚地為死者招魂的習俗。當代楚舞的創編一方面可以吸收這幅帛畫中對男子身體形態的審美追求,形成男子舞蹈的基本體態動作;一方面可以從其中所隱射的文化信仰中體會出楚人的審美心理結構,從而在當代楚舞的風格韻律上把握一種“巫風”之氣。
諸如此類的例子還很多,對于楚舞的研究可進行一定的延伸與擴展,總之,從楚文物所隱射的文化信仰中體會出楚人的審美心理結構去進行楚舞的研究、當代復現甚至是作品的創作不失為一條值得探索的道路。
參考文獻:
[1]湖南省博物館 主編.鳳舞九天—楚文物特展[M].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09:232
作者簡介:
龔倩,女,壯族,中南大學音樂舞蹈系副教授,南京藝術學院在職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舞劇創作與批評、舞蹈身體語言、中國古典舞(楚舞)、舞蹈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