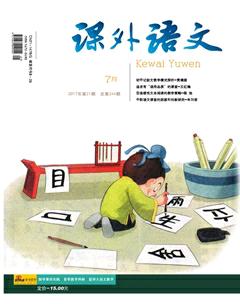再談對(duì)外漢語漢字教學(xué)與母語漢字教學(xué)的異同
徐亮+羅藝雪
【摘要】本文基于教學(xué)體系、教學(xué)目標(biāo)對(duì)對(duì)外漢字教學(xué)和母語漢字教學(xué)進(jìn)行了比較和分析,在過去研究的基礎(chǔ)上,以期能針對(duì)對(duì)外漢語漢字教學(xué)提出一些可行的建議和設(shè)想。
【關(guān)鍵詞】漢字教學(xué);教學(xué)體系;教學(xué)目標(biāo)
【中圖分類號(hào)】H19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一、引言
毋庸贅言,對(duì)外漢語教學(xué)和母語教學(xué)存在本質(zhì)的不同。因此,近年來研究者多從二者的區(qū)別出發(fā),強(qiáng)調(diào)對(duì)外漢字教學(xué)區(qū)別于母語漢字教學(xué)的特殊性,劃清二者間界限。就二者各自不同的客觀規(guī)律而言,這種區(qū)別對(duì)待的態(tài)度是科學(xué)的。然而,對(duì)它們的內(nèi)在聯(lián)系和一致性的忽略也難免會(huì)對(duì)具體教學(xué)過程造成不良影響。本文結(jié)合之前的研究,擬從二者的教學(xué)體系和教學(xué)目標(biāo)兩方面對(duì)二者進(jìn)行具體的比較和分析,論述其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的特點(diǎn),并以此為切入點(diǎn),討論加強(qiáng)對(duì)外漢字教學(xué)的方法。
二、由教學(xué)體系說起
就母語語文教學(xué)體系而言,不存在“口語教學(xué)”“語法(結(jié)構(gòu))教學(xué)”這樣的課型,識(shí)字、閱讀、寫作(一般稱為“作文”)統(tǒng)一于書面語教學(xué),統(tǒng)稱為“語文”課。也就是說,母語語文教學(xué)體系一直以一體化為特點(diǎn),沒有教學(xué)內(nèi)容或是課型之間的矛盾。具體到教學(xué)過程當(dāng)中,即是以識(shí)字帶動(dòng)閱讀,奠定寫作基礎(chǔ);以閱讀促進(jìn)識(shí)字,培養(yǎng)文學(xué)感,積累寫作素材;又以寫作檢驗(yàn)寫字用字,進(jìn)一步推動(dòng)閱讀活動(dòng)的開展。整個(gè)進(jìn)程中教學(xué)內(nèi)容各方面協(xié)調(diào)發(fā)展。而隨著對(duì)外漢語教學(xué)學(xué)科體系的逐步建立與完善,在全面培養(yǎng)學(xué)生交際能力的理念指導(dǎo)下,一方面,各課型之間的配合更加緊密,形成一個(gè)有機(jī)聯(lián)系、相輔相成的整體;另一方面,各課型之間的分工又日趨明確,形成各自相對(duì)獨(dú)立的課程規(guī)范,其中漢字教學(xué)在這一教學(xué)體系中呈現(xiàn)滯后狀態(tài)。也就是說,不同于母語教學(xué),對(duì)外漢語教學(xué)體系的各個(gè)因素之間并非自然地互相促進(jìn)、平衡發(fā)展,而是需要人為的調(diào)節(jié)。要改變漢字教學(xué)現(xiàn)狀,便需要理順結(jié)構(gòu)教學(xué)、功能教學(xué)與漢字教學(xué)的關(guān)系并采取有效措施。教學(xué)界嘗試過幾種教學(xué)方法,如“先語后文”“語文并進(jìn)”“拼音文字交叉出現(xiàn)”“獨(dú)立設(shè)課、集中強(qiáng)化”等,然而都不能很好地滿足教學(xué)的需要。對(duì)此,許多研究者都提出了頗有啟發(fā)性的設(shè)想,有的還在實(shí)踐上進(jìn)行了探索,下舉較有代表性的幾種觀之:
(一)口語與讀寫分開的漢語雙軌教學(xué)
這一教學(xué)模式在法國(guó)學(xué)者華為民(Monique Hoa)(1999)的文章中有比較詳細(xì)的論述,總的框架是“依據(jù)同一課文內(nèi)容,將口語與漢字分開教授。教說話用口語本,采用漢語拼音。口語本講授詞匯、語法、句型結(jié)構(gòu)等。教讀寫用漢字本。口語課先行,漢字課在后,即先學(xué)說話,后學(xué)讀寫”(華為民,1999)。即在漢語教學(xué)上采用雙軌制,在漢字教學(xué)上采取篩選法,使?jié)h字教學(xué)依據(jù)漢字本身的結(jié)構(gòu)規(guī)律自成系統(tǒng),同時(shí)又不與口語教學(xué)脫節(jié)。這與上面提到的“獨(dú)立設(shè)課、集中強(qiáng)化”在結(jié)構(gòu)上似乎異曲同工。但“獨(dú)立設(shè)課、集中強(qiáng)化”是附屬于語法教學(xué)之下的,如現(xiàn)階段許多學(xué)校實(shí)行的是語法教學(xué)(精讀課)和口語教學(xué)雙軌制;而這一設(shè)想把語法教學(xué)融入口語教學(xué)之中,同時(shí)增加漢字教學(xué)一“軌”,無疑大大提升了漢字教學(xué)的地位。
(二)建立書面語言教學(xué)系統(tǒng)
呂必松老師(1999)提出建立相對(duì)獨(dú)立的、與口頭語言教學(xué)系統(tǒng)相平行的書面語言教學(xué)系統(tǒng),這是從根本上改變現(xiàn)行教學(xué)模式的設(shè)想,形成語體教學(xué)的意識(shí)。漢語書面語言教學(xué)系統(tǒng)把“字”作為最小的語法單位,突出“字”的教學(xué),并把“字”的教學(xué)與書面語言的教學(xué)有機(jī)結(jié)合起來,專門進(jìn)行漢字、閱讀和寫作教學(xué),將口頭語言能力和書面語言能力分別進(jìn)行培養(yǎng)。這又是以“字本位”為理論指導(dǎo),切實(shí)變革現(xiàn)行教學(xué)體系的設(shè)想,最具建設(shè)性的是針對(duì)現(xiàn)行教學(xué)體系缺乏語體意識(shí)、學(xué)生不能區(qū)分口語體語言和書面語語言的弊端,將口語與書面語的區(qū)分作為教學(xué)模式劃分的主要依據(jù)。
(三)從現(xiàn)行體系下漢字教學(xué)的加強(qiáng)到教學(xué)體系的根本性變革
關(guān)于這一設(shè)想北京大學(xué)李大遂老師(1999)有詳細(xì)論述。即一方面在現(xiàn)行基礎(chǔ)漢語教學(xué)體系框架下盡力加強(qiáng)漢字教學(xué),如“在課堂教學(xué)這一環(huán)節(jié)上充實(shí)漢字教學(xué)內(nèi)容,改進(jìn)漢字教學(xué)方法,以漢字教學(xué)帶動(dòng)詞匯、語法及語音的教學(xué)。也可以為不同層次的學(xué)生開設(shè)相對(duì)獨(dú)立的漢字課”(李大遂,1999),這是“治標(biāo)”之法;另一方面,開始在理論和實(shí)踐兩個(gè)層面上探索建立切實(shí)重視漢字教學(xué)的基礎(chǔ)漢語教學(xué)體系,對(duì)教學(xué)體系進(jìn)行根本性變革,這是“治本”之法。由于這一層面的變革涉及現(xiàn)行體系的方方面面,是一個(gè)復(fù)雜、曲折和長(zhǎng)遠(yuǎn)的進(jìn)程,對(duì)這方面李大遂老師并沒有具體步驟、方法的論述,但舉了法國(guó)白樂桑和北京語言文化大學(xué)合編的《漢語語言文字啟蒙》為例。這種提法從實(shí)際出發(fā),在現(xiàn)實(shí)層面上對(duì)現(xiàn)階段教學(xué)中急需變革的頑癥起到了補(bǔ)偏救弊的作用;同時(shí),在發(fā)展層面上又有整體性和長(zhǎng)遠(yuǎn)性思考,對(duì)根本目標(biāo)的實(shí)現(xiàn)采取了分步走的策略。
(四)“字本位”的教學(xué)實(shí)踐
這是對(duì)基礎(chǔ)漢語教學(xué)體系進(jìn)行根本性變革的探索之一。上文提到的《漢語語言文字啟蒙》(下簡(jiǎn)稱《啟蒙》)是其重要代表。呂必松(1999)認(rèn)為:“長(zhǎng)期以來我們的對(duì)外漢語教學(xué)所采用的教學(xué)路子,基本上是印歐系語言教學(xué)的路子。”“把‘詞和‘句子作為教學(xué)內(nèi)容的基本單位;把漢字排除在語言要素之外,使其成為詞匯的附屬品”。這就是“詞本位”的指導(dǎo)思想。“字本位”籠統(tǒng)來說即認(rèn)為漢語句法結(jié)構(gòu)的基本單位是“字”,這一點(diǎn)趙元任和徐通鏘都曾撰文加以論證。應(yīng)用到教學(xué)上,“字本位”和“詞本位”體現(xiàn)著兩種不同的教學(xué)思路。《啟蒙》作者在教材簡(jiǎn)介中指出:“本教材在總體設(shè)計(jì)上力圖體現(xiàn)漢語字與詞關(guān)系這一特點(diǎn),循漢語之本來面目進(jìn)行教學(xué),故本教材可稱為‘字本位教學(xué)法。”如其所述,它突破了傳統(tǒng)的語法框架,根據(jù)漢語的特點(diǎn),以字為基本結(jié)構(gòu)單位,從字到詞,采用“字本位”教學(xué)法,有效地組織了字、詞、句以及文化的教學(xué),而事實(shí)也證明了該實(shí)踐的成功,這對(duì)國(guó)內(nèi)對(duì)外漢語教學(xué)不能不說有很大的啟示。
這些設(shè)想和教學(xué)實(shí)踐都從現(xiàn)實(shí)需求出發(fā),具有一定的建設(shè)性和可行性,從中可以窺見基礎(chǔ)漢語教學(xué)體系根本性變革的曙光。漢語教學(xué)隨漢語語言研究、語言教學(xué)研究、語言學(xué)習(xí)研究及實(shí)踐的發(fā)展而發(fā)展,上面的設(shè)想都體現(xiàn)了這一規(guī)律,但它們都需要在實(shí)踐的檢驗(yàn)中不斷發(fā)展、不斷完善。endprint
三、由教學(xué)目標(biāo)說起
(一)目標(biāo)一致性
作為記錄漢語言的符號(hào)體系,漢字是我國(guó)唯一的正式文字工具,是漢文化的載體。無論是中國(guó)學(xué)生,還是外國(guó)留學(xué)生,要獲得全面的漢語語言交際能力,并由此學(xué)習(xí)和研究中國(guó)文化,就必須學(xué)習(xí)漢字。因此,母語漢字教學(xué)和對(duì)外漢字教學(xué)的總體目標(biāo)都是獲得漢字交際能力(這里主要指識(shí)字、寫字、用字能力)及漢字學(xué)習(xí)能力,二者有其一致性和可參照性。
(二)目標(biāo)差異性
然而,總體目標(biāo)的一致性不能掩蓋由漢字交際能力所包含內(nèi)容的層次性引起教學(xué)過程中具體目標(biāo)的分歧。朱德熙先生(1988)曾簡(jiǎn)明地解釋漢字學(xué)習(xí)中“認(rèn)漢字、寫漢字、用漢字”的層次問題。他指出:“三者之中,認(rèn)最容易,寫就比較難。因?yàn)闈h字的特點(diǎn)很明顯,只要抓住某一方面的特點(diǎn)就能認(rèn)識(shí)它……不難認(rèn),可是寫起來就難多了。因?yàn)閷懙臅r(shí)候要求掌握全部細(xì)節(jié),差一點(diǎn)兒也不行,而且還有筆順問題,寫漢字要比認(rèn)漢字難……用漢字要比認(rèn)和寫都難得多。所謂會(huì)用,就是要學(xué)會(huì)區(qū)別同音字,知道哪種場(chǎng)合用哪個(gè)。”這里指出了識(shí)字教學(xué)的最高質(zhì)量要求。但對(duì)內(nèi)識(shí)字教學(xué)中,應(yīng)該識(shí)字、寫字、用字并重;對(duì)外識(shí)字教學(xué)中,在三者結(jié)合的同時(shí)應(yīng)該突出識(shí)字。下面僅就識(shí)字與寫字的關(guān)系作簡(jiǎn)單論述。
就漢字本身而言,易認(rèn)、難讀、難寫是其自身的特性,我們應(yīng)注意閱讀的心理特點(diǎn),把認(rèn)、讀、寫的要求適時(shí)分開,強(qiáng)化識(shí)字教學(xué)。識(shí)字量的增加可以大幅度地增加閱讀量,反過來又會(huì)鞏固對(duì)漢字的掌握。另一方面,就中國(guó)的現(xiàn)狀而論,漢字差不多可以說是漢人唯一的書面交際工具,書寫行為是漢人進(jìn)行書面交際時(shí)的主要行為,識(shí)字只能實(shí)現(xiàn)輸入,寫字、用字才能實(shí)現(xiàn)輸出。所以,母語識(shí)字教學(xué)中的識(shí)字、寫字、用字必須并重,使學(xué)習(xí)者掌握正確使用書面語的能力,以滿足社會(huì)書面交際需要。對(duì)留學(xué)生而言卻有所不同,他們的書面語言交際主要借助母語或至少是雙語,且隨著信息技術(shù)的發(fā)展和漢字輸入技術(shù)的成熟,越來越多的人依賴電腦“書寫”,只要能掌握讀音、字義和模糊的字形,便能實(shí)現(xiàn)有效交際。從閱讀和使用電腦的角度來說,認(rèn)讀可能比書寫更為重要。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在學(xué)習(xí)漢字的一開始就可以降低寫字的要求。
(三)對(duì)外漢字教學(xué)目標(biāo)
所謂漢字難,主要是“入門難”,難在學(xué)生對(duì)漢字沒有清晰正確的認(rèn)識(shí)。母語小學(xué)識(shí)字教學(xué)就非常重視學(xué)生在一開始對(duì)漢字從字形、字音、字義的全面把握和認(rèn)識(shí),為以后的學(xué)習(xí)打下扎實(shí)基礎(chǔ)。同樣,如果留學(xué)生能在初級(jí)階段牢固掌握字形結(jié)構(gòu)規(guī)律,不但可以降低漢字學(xué)習(xí)的難度,還可以為閱讀和寫作教學(xué)打下堅(jiān)實(shí)基礎(chǔ)。這時(shí)對(duì)字形的模仿和書寫練習(xí)便能發(fā)揮很大的作用,使留學(xué)生在一開始對(duì)漢字筆畫、部件、部件結(jié)構(gòu)、整體輪廓等從感性和理性兩方面進(jìn)行認(rèn)識(shí),實(shí)現(xiàn)清晰記憶和把握。這一階段對(duì)字形不到位的容忍不但違反認(rèn)知策略(教學(xué)實(shí)踐顯示留學(xué)生這一階段常運(yùn)用字形策略),破壞漢字教學(xué)和學(xué)習(xí)的系統(tǒng)性,而且最終會(huì)妨礙有效的交際,不利于漢字能力的后續(xù)發(fā)展,與漢字教學(xué)培養(yǎng)學(xué)生自學(xué)能力的教學(xué)目標(biāo)相違背。母語學(xué)習(xí)者對(duì)漢字的綜合把握與小學(xué)識(shí)字教學(xué)階段一定量的抄寫練習(xí)是分不開的,這是個(gè)很好的經(jīng)驗(yàn)。識(shí)字量大于寫字、用字量,是科學(xué)有效且符合語言能力的做法,但是,由于入門階段所教授的多為基本字或基本構(gòu)字部件,此時(shí)的識(shí)字與寫字基本上應(yīng)是平衡發(fā)展的過程。試想如果我們的學(xué)生能用電腦敲出正確的漢字,卻不能在日常生活中寫出一張能夠使?jié)h語母語使用者理解的便條,我們的教學(xué)活動(dòng)能說是成功的嗎?
四、結(jié)語
對(duì)外漢字教學(xué)是整個(gè)對(duì)外漢語教學(xué)的重要一環(huán),也是一個(gè)突出的難點(diǎn)。從母語漢字教學(xué)和對(duì)外漢字教學(xué)的異同點(diǎn)切入進(jìn)行分析,也許能對(duì)加強(qiáng)現(xiàn)階段漢字教學(xué)有所啟示。當(dāng)然以上論述只是一些大致的方向,在現(xiàn)實(shí)的漢字教學(xué)過程中,還需要結(jié)合教學(xué)對(duì)象、教學(xué)內(nèi)容、教學(xué)階段性目標(biāo)等具體情況進(jìn)行細(xì)致分析,方能有效地改進(jìn)漢字教學(xué)。
參考文獻(xiàn)
[1]安雄.談對(duì)外“理性識(shí)字法”的構(gòu)造[J].世界漢語教學(xué),2003(2).
[2]卞覺非.漢字教學(xué):教什么?怎么教?[J].語言文字應(yīng)用,1999(1).
[3]費(fèi)錦昌.對(duì)外漢字教學(xué)的特點(diǎn)、難點(diǎn)及對(duì)策[J].漢字與漢字教學(xué)研究,1999.
[4]華為民.談漢語雙軌教學(xué)中漢字的引入[J].漢字與漢字教學(xué)研究,1999.
[5]李大遂.從漢語的兩個(gè)特點(diǎn)談必須切實(shí)重視漢字教學(xué)[J].漢字與漢字教學(xué)研究論文集,1999.
[6]李大遂.突出系統(tǒng)性 擴(kuò)大識(shí)字量—關(guān)于中高級(jí)漢字課的思考與實(shí)踐[J].語言文字應(yīng)用,2004(3).
[7]呂必松.漢字教學(xué)與漢語教學(xué)[J].漢字與漢字教學(xué)研究,1999.
[8]楊夷平,易洪川.淺析識(shí)字教學(xué)的對(duì)內(nèi)、對(duì)外差別[J].世界漢語教學(xué),1998(2).
[9]周健尉萬傳.研究學(xué)習(xí)策略改進(jìn)漢字教學(xué)[J].暨南大學(xué)華文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04(1).
[10]朱德熙.在“漢字問題學(xué)術(shù)討論會(huì)”開幕式上的發(fā)言[A].]漢字問題學(xué)術(shù)討論會(huì)論文集//[C].北京:語文出版社,1988.
作者簡(jiǎn)介:徐亮,1982年生,四川內(nèi)江人,碩士,內(nèi)江師范學(xué)院外國(guó)語學(xué)院講師,研究方向?yàn)橥庹Z教學(xué)與中華文化國(guó)際傳播;羅藝雪,系本文通訊作者,女,1983年生,四川邛崍人,博士,四川大學(xué)海外教育學(xué)院講師,研究方向?yàn)楝F(xiàn)代漢語語法與對(duì)外漢語教學(xué)。
(編輯:龍賢東)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