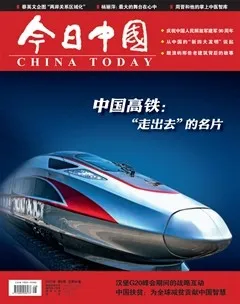劉心武:我是馬拉松式的寫(xiě)作者
文|施 迅 綦麗潔
劉心武:我是馬拉松式的寫(xiě)作者
文|施 迅 綦麗潔
幾十年來(lái)劉心武始終活躍在文壇,筆耕不輟。他曾不止一次地說(shuō),自己是一個(gè)馬拉松長(zhǎng)跑式的寫(xiě)作者。

劉心武
2017年5月28日,《劉心武自選集》新書(shū)發(fā)布會(huì)在北京金融街字里行間書(shū)店舉行。75歲的劉心武在交流會(huì)上講述了從事文學(xué)寫(xiě)作60年來(lái)的心得。現(xiàn)場(chǎng)來(lái)的粉絲既有當(dāng)年《班主任》的讀者,也有許多在校學(xué)生。
幾十年來(lái)劉心武始終活躍在文壇,筆耕不輟。他曾不止一次地說(shuō),自己是一個(gè)馬拉松長(zhǎng)跑式的寫(xiě)作者。
2016年,某出版社推出26卷本《劉心武文粹》時(shí),劉心武說(shuō),“有時(shí)候需要把自己作為一個(gè)個(gè)案,提供給文學(xué)史的研究者研究——在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的發(fā)展過(guò)程中,他是怎么過(guò)來(lái)的,這個(gè)人當(dāng)初多么幼稚可笑,寫(xiě)的東西多么糟糕,但是他又引起了轟動(dòng),作品又很有爭(zhēng)議。有些作品現(xiàn)在看來(lái)還有一定的比較久遠(yuǎn)的審美價(jià)值,雖然很雜駁,但是要做一個(gè)羅列,這就是文存的意義。”
寫(xiě)《班主任》心里也打鼓
劉心武1942年出生于成都,8歲跟隨父母移居北京,曾當(dāng)過(guò)中學(xué)教師、出版社編輯、《人民文學(xué)》雜志主編。他在1977年發(fā)表的短篇小說(shuō)《班主任》,被認(rèn)為是“傷痕文學(xué)”的發(fā)軔作。
在成名之前,劉心武已經(jīng)堅(jiān)持寫(xiě)作多年。他的第一篇稿子是評(píng)論蘇聯(lián)的拉夫列尼約夫的小說(shuō)《第四十一》。稿子被某雜志刊登之后,編輯以為他是一個(gè)學(xué)究,就用墨筆在很高級(jí)的宣紙上給他寫(xiě)親筆信,希望他多多賜稿。后來(lái)他們一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劉心武高中沒(méi)畢業(yè),還是未成年人,讓人失笑,就把后來(lái)的稿子退了。
寫(xiě)《班主任》時(shí),劉心武自己也心里打鼓:這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嘛!這樣的稿子能公開(kāi)拿出去嗎?在發(fā)表欲的支配下,他終于還是鼓起勇氣,投給了《人民文學(xué)》雜志。
這篇小說(shuō)今天看來(lái)并不成熟,但當(dāng)時(shí)帶來(lái)的反響卻超出他的想象。既有工人打聽(tīng)他家地址找上門(mén)來(lái)表達(dá)喜愛(ài),也有人給“有關(guān)部門(mén)”寫(xiě)匿名信指斥《班主任》等“傷痕文學(xué)”作品是搞“修正主義”,還有人勸其“不要走得太遠(yuǎn)”。
海外對(duì)《班主任》不吝贊美,甚至稱他為“傷痕文學(xué)之父”。
“那時(shí)候,這樣的‘海外反響’越多,便越令一些人對(duì)當(dāng)事人側(cè)目。因此我在頗長(zhǎng)一段時(shí)間里,心里都不是非常踏實(shí)。”劉心武說(shuō)。
1981年,他應(yīng)日本《文藝春秋》社邀請(qǐng)?jiān)L日期間,主辦方帶他們參觀一座日本古代監(jiān)獄模型時(shí),翻譯小姐對(duì)他說(shuō):“你是不是差一點(diǎn)被關(guān)起來(lái)?”“文革”期間,她在中國(guó)待過(guò),后來(lái)在異國(guó)讀到《班主任》時(shí),還為劉心武捏了一把汗。
“這種心理狀態(tài),29年過(guò)去,不要說(shuō)現(xiàn)在的年輕人難以理解,就是我這個(gè)當(dāng)事人,回想起來(lái),也恍若一夢(mèng)!”劉心武曾感慨。
在那個(gè)特殊的時(shí)代,劉心武的作品具有特殊的價(jià)值。陳丹青曾自曝,當(dāng)年在雜志上看到劉心武的《立體交叉橋》時(shí),喜歡得不得了,立即撕下來(lái),帶著它飛往美國(guó)。
沒(méi)有《金瓶梅》就沒(méi)有《紅樓夢(mèng)》
劉心武的再次爆紅是因?yàn)椤都t樓夢(mèng)》。2005年,劉心武在中央電視臺(tái)《百家講壇》欄目上講秦可卿專題,2011年又出版《劉心武續(xù)紅樓夢(mèng)》,都在中國(guó)掀起一股“紅樓夢(mèng)”熱潮。
這個(gè)系列講座觀眾數(shù)量龐大,不但有中老年人,還有相當(dāng)一部分年輕人,包括在校學(xué)生。劉心武的觀點(diǎn)頗具爭(zhēng)議,有人叫絕,有人抨擊,相互辯論。讓劉心武感到最可喜的,是這個(gè)系列節(jié)目引發(fā)出了閱讀《紅樓夢(mèng)》的興趣,沒(méi)讀過(guò)的要找來(lái)讀,沒(méi)通讀過(guò)的打算通讀,通讀過(guò)的還想再讀。“網(wǎng)上關(guān)于對(duì)《紅樓夢(mèng)》的討論,角度更多,觀點(diǎn)更新,分析更細(xì),揭示更深,我從這些不同的反應(yīng)里,真是獲益匪淺。”劉心武說(shuō)。
在劉心武看來(lái),紅學(xué)研究應(yīng)該是一個(gè)公眾共享的學(xué)術(shù)空間,他借用了蔡元培的八個(gè)字,“多歧為貴,不取茍同”——誰(shuí)也不應(yīng)該聲稱關(guān)于《紅樓夢(mèng)》的闡釋獨(dú)他正確,更不能壓制封殺不同的觀點(diǎn),要允許哪怕是自己覺(jué)得最刺耳的不同見(jiàn)解發(fā)表出來(lái),要有平等討論的態(tài)度、容納分歧爭(zhēng)議的學(xué)術(shù)襟懷。
“我的研究,屬于探佚學(xué)范疇,方法基本是原型研究。從對(duì)秦可卿原型的研究入手,揭示《紅樓夢(mèng)》文本背后的清代康、雍、乾三朝的政治權(quán)力之爭(zhēng),并不是我的終極目的。”劉心武說(shuō),對(duì)秦可卿的研究只是一個(gè)突破口,好比打開(kāi)一扇能看清內(nèi)部景象的窗戶,借此進(jìn)入《紅樓夢(mèng)》,領(lǐng)悟里面的無(wú)窮奧妙。”
劉心武說(shuō),說(shuō)到頭,他的秦學(xué)究竟是否能夠成立,并不是一個(gè)多么重要的問(wèn)題。“這個(gè)系列講座,引發(fā)出了人們對(duì)《紅樓夢(mèng)》的更濃厚的興趣,讀《紅樓夢(mèng)》的人更多了,參與討論的人更多了,紅學(xué)在民間的空間,因此大大拓展,這才是最重要的。”
研究紅樓夢(mèng)的爭(zhēng)議尚未完全散去,2012年,劉心武又開(kāi)始評(píng)點(diǎn)《金瓶梅》,很多人痛心疾首地對(duì)他說(shuō):你這是要晚節(jié)不保啊。劉心武不理解,在他看來(lái),作為一個(gè)普通中國(guó)人,一生一次《紅樓夢(mèng)》都不讀,很遺憾;一生對(duì)于《金瓶梅》總是誤解,也很遺憾。
劉心武第一次“結(jié)緣”《金瓶梅》,已經(jīng)是在改革開(kāi)放以后,讀的也不是全本,但《金瓶梅》中寫(xiě)實(shí)主義的文本達(dá)到的高度、人物的刻畫(huà)功力還是讓他震驚乃至相見(jiàn)恨晚。
書(shū)中的人物性格完全不是符號(hào)化的,“潘金蓮很兇惡,武大郎不死,她跳到武大郎身上,拿被子把他捂死,非常殘暴。但是她也有直率的一面,她跟西門(mén)慶吵架的時(shí)候非常不畏強(qiáng)暴;還有乞丐乞討的時(shí)候她也是很熱心地施舍,她也有善良的一面。《金瓶梅》把人性當(dāng)中的真假善惡、是非良善寫(xiě)得非常鮮活真實(shí)。”
劉心武還看到了更多。他說(shuō),《金瓶梅》里描述了一個(gè)很黑暗、很墮落的社會(huì),整個(gè)社會(huì)生活負(fù)面的東西很多。但是由于商品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和社會(huì)的相對(duì)穩(wěn)定,創(chuàng)造出一種從上到下富人和窮人的共享繁華。
十多年里劉心武參閱了大量資料,最后從《金瓶梅》的成書(shū)之謎、西門(mén)慶死亡之謎、大結(jié)局之謎、影響《紅樓夢(mèng)》之謎等31個(gè)謎題入手來(lái)談。面對(duì)種種爭(zhēng)議,他不是毫無(wú)壓力,但他還是堅(jiān)持自己的看法:“《金瓶梅》是《紅樓夢(mèng)》的祖宗。沒(méi)有《金瓶梅》,也就不會(huì)有《紅樓夢(mèng)》”。
那些“人生有信”
不少人說(shuō)劉心武脾氣有點(diǎn)“怪”。《紅樓夢(mèng)》中,劉心武最喜歡的是妙玉。“我有時(shí)候和妙玉一樣,過(guò)著離群索居的生活,性格也很孤僻。”他一般不接受采訪,也不參加文學(xué)會(huì)議,跟文化圈的活動(dòng)基本不沾邊。
身為“正局級(jí)干部”的劉心武對(duì)記者說(shuō)過(guò):“雖然我有用車待遇,但一次也沒(méi)享受過(guò)。我自己打車,不報(bào)銷。因?yàn)槲矣邪娑悾兜闷疬@個(gè)錢(qián)。”“我早就不是專業(yè)作家了,沒(méi)有寫(xiě)作任務(wù),也不用報(bào)計(jì)劃,更不用自己驅(qū)趕自己,就是賦閑、退休,自己過(guò)活。”
東方出版社出版的《人生有信》里,劉心武記錄了與孫犁、冰心、夏志清、余英時(shí)、蔣孔陽(yáng)、馮牧等數(shù)十位文化名人的信函,以細(xì)膩的筆觸記錄了那一代文化人同氣相求的真誠(chéng)善念。
劉心武和著名美學(xué)家蔣孔陽(yáng)的情誼,始于中篇小說(shuō)《立體交叉橋》。當(dāng)年這部小說(shuō)引發(fā)爭(zhēng)議,蔣孔陽(yáng)發(fā)表了長(zhǎng)篇評(píng)論予以充分肯定,并從此開(kāi)始二人之間長(zhǎng)達(dá)20多年的書(shū)信往來(lái)。雖然兩人始終緣慳一面,但蔣先生當(dāng)年的鼎力扶持讓劉心武終身難忘。
“這些書(shū)信牽動(dòng)出我絲絲縷縷五味雜陳的心緒。當(dāng)時(shí)代浪濤的相激相蕩將我們拋到同一種困境中時(shí),我們能夠相濡以沫,互相激勵(lì),互相聲援。30年前那些雨絲風(fēng)片,如今回想起來(lái),有若許亮光,若許暖意,也有若許混沌,若許惆悵。”劉心武說(shuō)。
劉心武曾在一家小書(shū)店里偶然發(fā)現(xiàn)《黃金時(shí)代》,他一口氣讀完,“多年來(lái)沒(méi)有這樣的閱讀快感了”。回家后他立馬打了一圈電話詢問(wèn)王小波的聯(lián)系方式,迫不及待打通電話后報(bào)上姓名,那頭的王小波懶懶地“唔”了一聲。劉心武一時(shí)不知該如何介紹自己,只好直截了當(dāng)?shù)卣f(shuō):“看了《黃金時(shí)代》,想認(rèn)識(shí)你,想跟你聊聊。”第二天下午,兩人約好見(jiàn)面,一直聊到夜里十一點(diǎn)飯館打烊。
“這一天我沒(méi)有白過(guò),我多了一個(gè)談伴,無(wú)所謂受益不受益,甚至可以說(shuō)并無(wú)特別收獲,但一個(gè)生命在與另一個(gè)生命的隨意的、絕無(wú)功利的交談中,覺(jué)得舒暢,感到愉快,這命運(yùn)的賜予,不就應(yīng)該合掌感激嗎?”多年后,劉心武依然記得那種暢聊之后的滿足感。
有一次,兩人聊到靠寫(xiě)作生存的問(wèn)題,王小波說(shuō),他有開(kāi)載重車的駕照,必要時(shí)可以上路掙錢(qián)。
劉心武的朋友、文化學(xué)者張頤武說(shuō),當(dāng)王小波還默默無(wú)聞時(shí),劉心武逢人就介紹,說(shuō)有一個(gè)特別了不起的作者。但王小波離世且名聲大噪后,劉心武卻退后,很少提及兩人的密切交往。
中學(xué)時(shí)期劉心武就愛(ài)畫(huà)水彩寫(xiě)生,常畫(huà)城里的古典建筑。在《王小波,晚上能來(lái)喝酒嗎》里,他畫(huà)了一幅五塔寺的水彩寫(xiě)生。“生前,王小波只相當(dāng)于五塔寺,冷寂無(wú)聲。死后,他卻仿佛成了碧云寺,熱鬧非凡。”

劉心武于2011年在《劉心武續(xù)紅樓夢(mèng)》簽售現(xiàn)場(chǎng)
文學(xué)就是寫(xiě)人的困境
1984年,劉心武的首部長(zhǎng)篇小說(shuō)《鐘鼓樓》刊載于《當(dāng)代》雜志,后獲得了第二屆茅盾文學(xué)獎(jiǎng)。小說(shuō)講述了20世紀(jì)80年代北京鐘鼓樓下的一個(gè)小雜院,在12個(gè)小時(shí)里發(fā)生的故事,濃縮了人生百態(tài)。
劉心武天生是喜愛(ài)寫(xiě)底層人物的。他有很多平民百姓朋友,像農(nóng)民朋友三兒,“的哥”朋友青嶺。
退休后,劉心武在京郊溫榆河畔買(mǎi)下農(nóng)舍,取名“溫榆齋”。他常從大飄窗望出去,看到形形色色的人,“就是一幅當(dāng)代的《清明上河圖》”。用了一年多時(shí)間,劉心武寫(xiě)就了這部16萬(wàn)字的《飄窗》,依然是人生百態(tài),只是比《鐘鼓樓》多了一些沉重和焦慮。
“作家興趣不同,有人專寫(xiě)官場(chǎng),有人寫(xiě)自己沒(méi)有生活過(guò)的年代,我的興趣從《鐘鼓樓》開(kāi)始,一貫有草根人物出現(xiàn),我覺(jué)得他們的真實(shí)狀態(tài)適合用文學(xué)來(lái)表現(xiàn),我也有能力去表現(xiàn)。”劉心武說(shuō)。
“作家興趣不同,有人專寫(xiě)官場(chǎng),有人寫(xiě)自己沒(méi)有生活過(guò)的年代,我的興趣從《鐘鼓樓》開(kāi)始,一貫有草根人物出現(xiàn),我覺(jué)得他們的真實(shí)狀態(tài)適合用文學(xué)來(lái)表現(xiàn),我也有能力去表現(xiàn)。”劉心武說(shuō)。在他看來(lái),市井人物是城市文化的煙火。作家也許未必能給他們提供解決困境的方法,但不能因此而不去關(guān)注現(xiàn)實(shí)。
“我們面對(duì)人間不平,乃至慘劇,往往把原因歸結(jié)到社會(huì)、制度的弊病,但是就文學(xué)而言,提醒讀者要直面人性,特別是人性惡,恐怕是更重要的使命。如何壓抑、控制、消弭人性惡?最好的文學(xué),應(yīng)該把讀者朝這樣的深度去引。”劉心武說(shuō)。
文學(xué)的本質(zhì)是什么?在一次交流會(huì)上,75歲的劉心武對(duì)提出這個(gè)問(wèn)題的讀者說(shuō),“文學(xué)就是寫(xiě)人性,要展示人的生存困境。這是我從最早60年前開(kāi)始投稿,一步一步所領(lǐng)悟到的一個(gè)文學(xué)的真諦、文學(xué)的本質(zh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