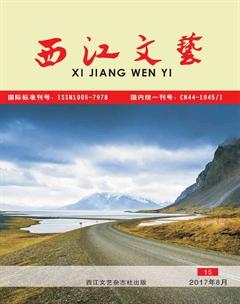“妓女”與“母親”兩重身份在新興電影運動下的架構解讀
孫亞男
【摘要】:《神女》通過一個具有妓女與母親“兩重生活”的形象深刻揭露了三十年代中國社會的殘酷和無情,批判了將人性異化的社會環境,即社會的制度層面。20世紀30年代的舊中國,無序攢動的人群、神情冷漠的面孔、逼促的警察、油頭滑面的流氓、佇立街頭的妓女、忙于奔波的人力車夫、閃著寒光的柏油路面、破爛的商店櫥窗……電影《神女》使觀眾能了解到了當時整個社會的風氣、社會人心的冷漠,以激發民眾的革命意識,無疑是默片藝術的巔峰之作,亦是新興進步電影中的經典之作。
【關鍵詞】:神女;母親;妓女;女性主義
在內憂外患、民不聊生的社會大背景下,處在家國危亡時刻的中國觀眾棄了那些神怪武俠奇觀電影和鴛鴦蝴蝶派的電影,這便迫切需要電影文藝工作者們創作出具有精神導引和社會意識的電影。借力高漲的民族主義思潮和文藝思潮,新興電影運動逐漸興起,出現了《三個摩登女性》、《狂流》、《漁光曲》、《姊妹花》、《桃李劫》、《神女》、《馬路天使》等一系列的優秀作品。在這場新興電影運動中,吳永剛作出了突出的貢獻,“他開拓了電影探索的新途徑,著力于將民族文化與電影相結合,他的電影帶有著明顯地中、西相互相融的特點,但是電影中卻有著深厚的傳統文化意境在其中,吳永剛的電影開始從敘事和造型等方面來嘗試電影的民族化意蘊。”
中華文明幾千年來,“妓女”一般代表著欲望、卑賤和邪惡;母親則代表圣潔、無私奉獻。為了消解傳統妓女身份帶來的欲望、卑賤和邪惡感暗示,導演吳永剛盡量壓縮了阮嫂作為妓女這一身份的占比率,而是盡可能的表現母親這一面,便是對阮嫂出賣身體的場景進行隱晦處理。最經典的便是阮嫂在夜上海街頭的三次接客:在第一次接客的場景中,一個男人側身入鏡,阮嫂跟其出鏡,鏡頭淡出,轉換為阮嫂疲憊上樓的畫面;第二次接客,畫面中只出現男人的一雙腳;第三次則采用俯拍鏡頭,畫面中只出現兩個人的頭頂。這種處理方式,使影片中流露出的男權無意識的被最大化的稀釋,進而使得阮嫂母親的偉大形象被高揚。“可以說這是一個被理想化的母親——以理想化的方式清除一個具有致命誘惑力的女子的威脅。”[1] 她也就只能通過無私的奉獻來完成罪感的洗滌,實現人格的升華。
從影片整體形式來看,影片《神女》多多少少帶有一些“鴛鴦蝴蝶派”的意味: “妓女形象作為都市奇觀可供獵奇 ,而母親形象作為家庭倫理的符號則表露出對傳統文化價值 (如忍辱負重 、自我克制、深明大義等)的借用。”[2]一方面“妓女”形象作為景觀供觀眾獵奇,而另一方面“母親”這一形象又成為家庭倫理的符號,浸潤著中國傳統文化里母親堅忍、克制、包容的形象的文化內涵。“妓女形象作為都市奇觀可供獵奇 ,而母親形象作為家庭倫理的符號則表露出對傳統文化價值 (如忍辱負重 、自我克制、深明大義等)的借用。”阮嫂獨自一人帶著孩子,靠出賣肉體維持生活,盡管如此,阮嫂仍然顯得樸實端莊。這是中國傳統話語塑造的、一般意義上的中國母親形象——忍辱負重而又不失尊嚴。導演一方面用“妓女”身份滿足觀眾“窺視癖”[3]的傾好;又依靠“母親”形象保留了電影的人道主義關切,進而使其成為一種意識形態,滿足市民階層的生理和心理的雙重需要。更精妙之處在于,“妓女”在影片中被重新定義賦予上了“普通市民”的層次。正如電影片頭所述:“神女……掙扎在生活的漩渦里……在這夜之街頭,她是一個低賤的神女……當她懷抱起她的孩子,她是一位圣潔的母親……在這兩重生活里,她顯出了偉大的人格……”[4]導演吳永剛似乎并不滿足于“底層妓女母親”艱難求生的母題,而是更加強化了底層“妓女”這一身份的可視性,并且試圖超越傳統敘事模式下知識分子式的“人道主義”變性,把“妓女”現象看作是社會制度腐衰的病態的表現,“在每一個都會的陰暗面——甚至窮鄉僻地的小市鎮里,都不會沒有公開的、或者私的娼妓,尤其是在這動蕩時期。那些在生活鞭策底下的女性們,她們除了出賣肉體來生活外,沒有比這再簡捷的方法,我們可以看到成群從破產的農村里來的女性,倒閉的工廠里的女工們,都淪落而為娼妓。在上海,尤其可以見到這種現象:她們被人蹂躪,被人唾棄,被那些流氓鴇婦當榨取金錢的工具,過著非人的生活。這是整個社會的問題,這是社會經濟制度的病態。” [5]正是這種獨特的大歷史觀視野使得《神女》突破了“鴛鴦蝴蝶派”式的意味,且沒有完全受制于傳統的敘事模式。吳永剛在民族危機加劇的時代背景下,在這種框架里進行了“有道德妓女”的塑造,從而展示出對新的電影運動形態進行“藝術形式化”的訴求。
《神女》融入了吳永剛深厚的情感和理性的考思,是一部暴露社會黑暗的影片。國民黨腐敗,社會經濟的蕭條,使處在社會底層的許多婦女淪落為暗娼。《神女》以“都市之夜”為線索架構了導演在揭示底層小人物的性格和命運的無意識情緒——無意識地通過阮嫂的境遇和母愛的各種表現,對普遍性的麻木人性進行深刻的批判。在影片中的大上海都市,社會制度越不合理,影片對人性批判的意味鋒芒就越銳利。可以說,阮嫂的一切可訾議處,都來自于麻木的自私人性和被異化的社會。最顯著的是,影片的一系列“都市之夜”鏡頭,以罕見的文化蘊涵、情感張力、內在結構和思想深度,從本源上熔鑄了導演的內在情感和思考,引發出觀眾對底層小人物在大都市中的渺小以及人在社會洪流中不可預知的命運的感喟。
在《神女》中,阮嫂兼具誘惑性感與溫柔賢惠的“兩重形象”,然而阮嫂的人物命運則表現為被動的毀滅與主動的救贖的二元模式。女性的主體性始終是缺失的,阮嫂依然是失語者,和數千年歷史洪流中的底層女性一樣,被表現得沒有歷史也沒有未來,甚至悲慘的命運也是必然的,作為那個時代的底層女性,獨身一人帶著幼小的兒子以暗娼身份生存,這種的人生選擇實在是作為女性的無奈。然而,阮嫂的身份卻是可以被毀滅或者被救贖的,但無論是被毀滅還是被救贖,她都只能作為被動的女性形象而存在于社會。阮嫂的主體性在影片中被降低到了最低限度,在影片中她沒有歷史,未來也是在監獄里延續,她的一切價值全在于撫養兒子成人,其實無形之中她還是從男權社會秩序外延回到了秩序內,她將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兒子身上。然而這種價值卻在她反抗社會洪流的掙扎里被毀滅,學校僅作為國家意識形態機器的角色而存在,從良的決心在工業背景里化成泡沫,她最后的反抗,使她作為母親的資格徹底被毀滅,寄托在下一代身上的希望被現實碾壓的粉碎。她的所有希望不斷被男性為主導的男權社會所打壓,不論是妓女身份還是母親身份,男性身份地位主導的從來都是將內部扭曲變態的欲望加之在想象的外在具體形象之上的,霓虹燈下是陌生男人的嘴臉,家中是章老大變相的壓迫。因此,在她的生命狀態里,也就只有自我拯救式的反抗才會使她有實現自己作為母親價值的可能,盡管最后這種反抗使她墜入另一種靈與肉的苦痛,她還是義無返顧的做了,她用自己的行為和期待,徹底抹擦了自己在男權社會中曾經留下的痕跡。幸運的是,撫養下一代的任務沒有被社會巨浪沖垮,
代之的是一個“替代性”的父親,阮嫂作為女性的使命已經完成,由此也完成了對阮嫂的救贖。
黑夜與白晝,將阮嫂的生活劃分成兩個世界、兩種分裂的人格。黑夜中,阮嫂以高叉旗袍和攝人心魄的神態游弋在霓虹燈下的上海街頭,抽煙、接客、麻木、疲倦;而白天在溫馨的家里,她則溫順、賢惠、裝扮樸素,是一位稱職的母親。“兩重生活”身份的巨大落差難免使觀眾覺得突兀,而恰恰是這種落差批判了男權社會里男權意識對女性人格的變態塑造。在阮嫂的生活中,男性的性格或灰暗、或卑微,能夠拯救和庇護她的理想男性僅僅只存在于想象或者期望之中,從本質上看,她根本無法在男性和社會方面得到自我的完整,期望和現實之間由此形成巨大的落差。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有過表現,“妓女”與“女性”都是男性幻想的產物。然而對于她們的幻想,通常會跳出男性潛意識的領域,進而成為演變成為一種意識形態,并在實踐領域進化為以“男性中心論”病理學為主導的社會意識形態。在章老大面前,阮嫂是無力反抗的,家中還有幼小的兒子等著她回去照顧,這個選擇實在是充滿了荒涼與無奈。換一種說法,阮嫂是沒有自主選擇的權利的,外面是逼促她的警察,面前是流氓,也只能選擇流氓。那個時代的女性的命運按照男性認為的軌道發展,相夫教子、賢妻良母。妓女作為比女性更低級的生物群體,只能是男性追逐的獵物和手里把玩的玩物。在新興電影運動的狂流中,“流氓”與“妓女”的同構性在《神女》中并沒有被作為表現對象,盡管流氓與妓女是具有相似社會地位的群體,但流氓并沒有對他們施以援助甚至是同情,反而利用身體構造上的優勢威嚇壓榨,試圖傾力榨出她們身上的最后一滴血。一個被社會洪流沖擊的無比脆弱的女子都滿懷希望傾盡全力向未來蹣跚著,而身強力壯的流氓漢卻在這個社會上洋洋自得的靠吸食妓女用身體和眼淚換來的金錢的血茍延殘喘。而代表著國家運轉機器的政府警察,他們從來沒有產出過為掙扎在社會邊緣的孱弱女子尋找生活出路的意識,掙扎在城市生存邊緣為生計而被迫過著皮肉生涯的妓女們,當是社會的最底層,她們被迫承受著世間最深、最大的苦難。而他們只會拿著滑稽的長矛驅趕,將她們向更深淵的地方驅趕。從這層意義上看,警察和流氓又怎么會有區別。“無論男性還是女性,人類的身體已經被符碼化置于社會網絡之中,在文化中,并且被文化賦予意義,男性被認為是雄健和有陽具的,女性則是被動和被閹割的。”[6]
神女悲慘的一生是那個悲劇性時代的真實反應,她凄涼的結局是對那個舊社會最深沉的控訴。《神女》成為默片電影的巔峰之作的意義在于,立足于那個年代失聲女性的視角,顛覆、反叛了男性正義的權威,塑造了浮出父權制歷史地表的女性形象,就是在這種普遍的定位過程中,《神女》逐漸超越了它所創作的時代,直到今天,依然散發著經久不衰的藝術魅力。
注釋:
[1]李學武.凝視母親的三種方式:《新女性》、《神女》、《紅顏》對母親形象的視覺呈現Ⅱ].電影藝術,2006年,(1):頁94.
[2]吳永剛:《我的探索和追求》,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86年:頁154。
[3]李科瑩:《幻光魅影背后的妓女身份在中國式情欲里的展現——以<神女><一步之遙>為例》,載《戲劇之家》第06期,頁124。
[4]《神女》片首字幕。參見《神女》劇本,載吳永剛: 《我的探索和追求》人文中國學報(第十七期)15,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86 年,頁804。
[5]吳永剛: 《〈神女〉完成之后》(原載《聯華畫報》,1935年第3卷第1期),載吳永剛: 《我的探索和追求》頁 134。
[6]張若冰女權主義文論 山東: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頁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