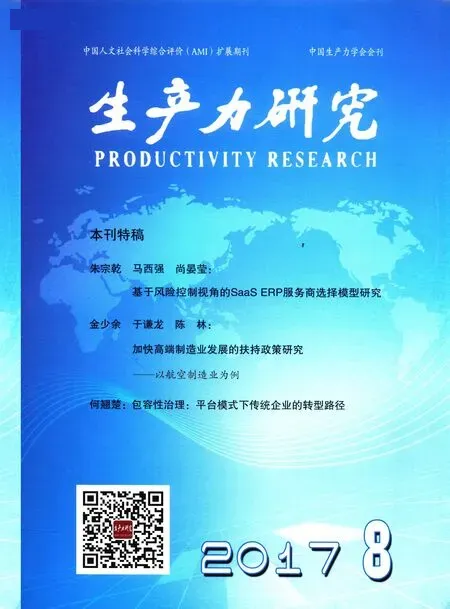農村公共物品協同供給運行機理:基于利益相關者的分析
崔曉芳,王文昌
(山西農業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山西 晉中 030801)
農村公共物品協同供給運行機理:基于利益相關者的分析
崔曉芳,王文昌
(山西農業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山西 晉中 030801)
農村公共物品協同供給是供給主體多元化的必然趨勢。但實踐中多元協同并不能自發生成,利益相關者理論為農村公共物品協同供給運行機理提供了相契合的研究范式。在利益相關者視角下,農村公共物品協同供給實質上是各主體間利益博弈過程,協同供給的實現依賴多元主體間利益均衡狀態的達成。基于利益相關者理論框架,首先對農村公共物品協同供給中各利益相關者進行界定,繼而對我國農村公共物品供給領域中以政府為基點,各利益主體間形成的扇形關系網進行了全景分析。通過理論和現實雙重維度審視,提出實踐中促使農村公共物品各利益主體間良性互動、達成利益均衡狀態、實現協同供給需政府從制度層面、運行層面、技術層面發揮關鍵作用。
農村公共物品;協同供給;利益相關者;利益關系;利益均衡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從頂層設計的高度提出健全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而農村公共物品有效供給是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實現社會公平正義之基石,同時也是貧困農村地區實施精準扶貧的著重點。稅費改革后,創新契合農村經濟社會結構的公共物品供給制度成為當下農村問題研究者關注的熱點。通過對農村公共物品供給相關文獻的梳理,可看到目前打破政府壟斷,引入多元主體成為廣受贊同之思路。但在農村公共物品供給實踐場域中,多元主體整體優勢的發揮,必須建立在各主體間協作互構基礎上,若各自為戰,將導致協調成本增加、供給碎片化問題。因此探究農村公共物品多元協同機制運行機理成為提倡供給主體多元化的學者們必然要面臨的研究課題[1]。
“協同”概念最早出自自然科學領域,在管理學中,協同指多元主體基于共同目標,平等協商、彼此合作、消除資源壁壘,實現價值增殖的過程[2]。在公共物品供給領域,多元協同供給指多元主體間通過構成多層復合、功能互補,相互支撐嵌入的網狀結構形成各主體間制度化、長效化、穩定化協作體系[3],以達到為公眾提供無縫隙公共物品、實現公共利益的過程。無疑多元協同是滿足農村公共物品需求多樣化的有效機制,但協同并不能自然而然發生,需深入細致地探究農村公共物品多元協同供給的內在運作機理,而相關理論闡釋的缺乏使多元協同機制的構建成為又一難題[1]。正如美國學者阿格拉諾夫在其著作《協作性公共管理:地方政府新戰略》中所述:盡管多元協同日益明顯,但迄今為止仍缺乏一個相當于官僚管理體系的理論基礎[4]。加之目前國內關于協同供給的相關研究大多集中在城市公共物品供給領域,而農村公共物品多元協同供給機制的構建相比城市更加復雜。因此,引入恰當理論分析范式,從多元主體協作背后的行為邏輯出發,對農村公共物品多元協同供給深入分析,對避免研究范式單一造成重復性闡釋具有重要的理論及實踐意義。
一、農村公共物品協同供給契合性研究范式:利益相關者理論
1963年美國斯坦福大學研究所針對企業管理中傳統的“股東至上主義”首次提出了“利益相關者”概念,認為企業生存發展不僅與股東休戚相關,還應獲得與企業緊密相連的利益人群或團體的支持[5],并經歷了“利益相關者影響”、“利益相關者參與”、“利益相關者共同治理”的發展脈絡①對利益相關者理論發展階段,國內不同學者觀點不一,此文中借鑒王身余在《從“影響”、“參與”到“共同治理”——利益相關者理論發展的歷史跨越及其啟示》一文中劃分法。。20世紀末隨著全球領域公共治理的興起,利益相關者理論從經濟學領域逐步擴展到管理學、政治學、社會學多學科領域,成為對管理過程進行深層剖析的新銳理論研究范式。
管理學中利益相關者理論內容可概括為以下幾點:第一,現實的組織活動都是在一定生態背景下進行,其生存發展離不開與組織密切聯系的利益相關者。借鑒美國經濟學家弗里曼(freeman)的觀點:組織中被組織目標實現過程影響并可影響組織目標實現的所有個人或群體都被稱為特定組織的利益相關者[6]。第二,組織中各利益相關者力量不同但地位平等,應共同參與組織決策。共同參與的要義是通過合作,謀求組織中單個主體無法達到的整體利益。第三,各利益相關者具有不同利益訴求,在走向共同合作過程中,通過彼此間利益牽制、支持等相互作用不斷進行利益博弈,形成不同利益關系,應通過協商交流等促使各利益主體從不均衡狀態轉化為均衡狀態。第四,各利益相關者力量和利益訴求會隨著組織內外環境變化不斷調整,利益均衡是具有特定時空性的相對狀態。
利益相關者理論強調管理活動中多元協作和動態參與,這與協同治理理念內核高度一致。更重要的是利益相關者理論從認知各主體利益關聯角度為探究農村公共物品協同供給運行機制提供了契合性研究范式。在利益相關者理論框架下,農村公共物品協同供給實質上是各供給主體基于不同利益訴求,相互依存、制約、博弈的過程,多元協同供給的實現要依賴多元主體間良性互動達成利益均衡狀態。利益相關者理論為農村公共物品多元協同供給運行機制提供了有效分析視角,同時也拓展了利益相關者理論的實踐應用范疇[7]。
二、農村公共物品協同供給中的利益相關者界定
借鑒相關學者觀點,將農村公共物品供給抽象為一個場域系統,其中利益相關者可界定為:為滿足農村發展需要,依據正式或非正式制度,以不同手段共同參與農村公共物品供給過程,并受農村公共物品供給發展目標影響的個人、群體和組織[8]。這些利益相關者也就是農村公共物品協同供給中的多元參與者,具體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出于研究對象及研究必要,主要指縣鄉基層政府)、企業組織、非營利組織、村委會、農村居民。這些參與者基于各自不同的角色、特質,在農村公共物品供給中表現出不同的利益訴求。借鑒學者何繼新、李原樂對社區公共物品利益相關者的多維分類,結合農村地區實踐,將農村公共物品多元協同相關利益主體做如下剖析[9](見表1)。

表1 農村公共物品協同供給中利益相關者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是農村公共物品協同供給中的權威型利益相關者,以國家強制力為后盾,不以營利為目的,通過直接或間接方式為農村提供公共物品。中央政府雖是社會公共利益的集中代表,但中央政府社會公利目標在特定時期表現為不同的利益選擇傾向,從農村與城市公共物品供給的二元結構可窺一斑。在農村公共物品協同供給中,中央政府不僅是公共物品提供者,同時也是促成農村公共物品協同供給達成的相關制度設計者、各利益相關者之間關系協調者、對其它利益相關者行為的監督者和管理者。
同為權威型利益相關者的基層政府具有雙重利益目標,一方面作為中央政府在農村地區的延伸代理,要最大限度維護并執行中央政府利益目標和利益行動;另一方面基層政府亦具有獨立性利益需求。如農村稅費改前基層政府在稅費收取中基于自身利益驅動加重了農民負擔,成為中央屢減不輕的痼疾,最終成為拉開農村稅費改革序幕的直接原因。
企業組織是營利型利益相關者,不具備強制權力。作為彌補政府失靈的私營組織,能在政府監管授權下提供一些外部性不強、排他性消費成本不高、產權歸屬明確的準公共物品,以緩解政府財政壓力。如農村社區健身、養老、良種培育等。但在農村公共物品協同供給中,營利者是企業組織最重要的角色,對其提供的公共物品,農村居民需繳納一定費用。
非營利組織、村委會和農村居民是農村公共物品協同供給中自愿型利益相關者,他們權力性及營利性弱,具有明顯的利他偏好。除公利目標外,在我國農村公共物品供給實踐中,自愿型利益相關者各有其它利益訴求。我國公民社會發育弱小,非營利組織剛剛起步,參與農村公共物品供給,有助于獲得政府部門對其合法性的肯定和一定的政策、資金、技術支持,以及提升公信力和供給能力;村委會成員由村民選舉產生,在“代理人”和“當家人”雙重沖突中[10],要謀求村民及上級鄉鎮政府合法性認同,以維護自身利益;農村居民作為理性經濟人有以最少代價獲取最大限度公共物品滿足的自利性訴求。
三、農村公共物品協同供給中利益相關者互動關系分析
農村公共物品協同供給中,各主體間利益相互不可代替,彼此進行交互作用,形成復雜的利益關系網。探究農村公共物品協同供給運行機理,必須以實踐為導向,揭示我國農村公共物品供給中多元利益主體互動之現實圖景。在我國特定經濟社會發展條件下,政府在農村公共物品多元利益主體互動中占有主導地位。因此以政府為基點,各利益相關者互動關系形成一個扇形關系網[11],如圖1所示。因此,對農村公共物品協同供給中利益互動關系的研究可從三方面展開:政府內部垂直互動關系、政府與政府外主體跨界互動關系、政府外主體間平行互動關系。

圖1 農村公共物品協同供給中各利益相關者扇形關系網
(一)政府內部垂直互動關系
政府內部垂直互動關系指的是中央政府和基層政府在農村公共物品供給中的博弈關系。中央政府在財力有限情況下,基于全社會福利最大化目標,沒能完全承擔起供給全國農村公共物品職責,而是通過強制性行政權力推給“話語權”相對弱勢一方的地方政府。例如在農村義務教育方面,我國占有財政收入20%的縣政府負擔了絕大部分義務教育經費[12]。在縣級財政自主統籌情況下,一些縣政府不得不想方設法籌集資金,甚至出現類似于福建省云霄縣將義務教育部分市場化的做法。福建省云霄縣曾將集中全縣優勢資源的云霄一中初中部轉讓給私人經營,按照成績學費分為不同等級,比之前增加了數十倍不止[12]。
基層政府從自利性出發,容易扭曲或消極執行中央政府決策,如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作為世紀初中央政府推動城鄉社會保障一體化的重大惠農政策,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農村居民醫療壓力,但農民并不是最大受益者,而是縣鄉醫療部門。因為衛生行政部門作為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管理者,既是農村公共衛生提供者,又是代表農村居民的購買者,難以通過加強自身管理減低醫療費用,反而帶來了醫療設備更新,醫療人員待遇升高的局面;除此之外,部分基層政府官員出于政績考慮,對中央下達的公共物品專項資金,使用不當,出現扶強不扶弱,不愿雪中送炭,更喜錦上添花的供給現象。
(二)政府與政府外主體跨界互動關系
政府與政府外主體跨界互動關系是農村公共物品協同供給研究中的重要內容。其中政府與企業組織和非營利組織間關系在實踐中出現兩種傾向:一是政府作為既有權力者,不肯輕易放權,在實踐中往往排斥或凌駕于其它主體之上。如在農村衛生保健、民辦養老方面,一些基層政府對非營利組織和企業組織不信任,形成競爭關系,以強制性手段迫使其退出農村公共物品供給領域;另一種就是將市場化或社會改革看做是解決農村公共供給問題的萬能良藥。如湖北省曾經進行的“以錢養事”的鄉鎮事業單位改革,對原本提供農村公共物品供給的事業單位進行撤銷或精簡,同時由鄉鎮和縣級業務主管部門進行規劃核算,將原有負擔鄉鎮事業單位資金用于向企業購買公共物品。但由于公共物品供給效果難以衡量及相關監管缺乏,企業行為短期化明顯,而且難以避免企業組織與掌握購買資金行政人員“利益同盟”的達成[13]。因此,政府與政府外主體互動關系的核心是政府對作為供給者、監督者和管理者角色的全面認知。
(三)政府外主體間平行互動關系
政府外主體間平行互動關系亦受到政府行為影響。因多元主體供給缺乏明確的邊界界定,易形成非營利組織、企業組織和村委會在某些供給領域中相互牽扯糾纏。譬如一些福利性公共物品供給在市場準入不清晰的情況下,演變成個別企業新的利潤增長點。
村委會作為農村基層自治組織與當地居民間關系的最大問題在于“當家人”角色威望的弱化與認同感的降低。例如農村糾紛調節是維護農村穩定的重要公共物品,隨著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村社會自然秩序的消解及稅費改革后農村集體經濟勢弱,村干部與村民間互動減少,一些原先依賴體制內權威調解的“穩定型”農村,內部調解能力大大下降。蘇北沭陽的錢集鎮,調解是村干部多年來的主要工作,但現在只有類似于南村村干部通過家族勢力的體制外權威,能夠取得村民認同,其它村莊村干部不具備體制外權威資源的,很難開展調解工作[12]。因此,村委會體制內權威的重塑是農村公共物品協同供給的重要研究內容。
村民間關系的難點在于如何克服協同供給中的“搭便車”問題。如在南方農村水稻產區,大中型水利設施難以對不交費農民進行排他,當有農民不交費卻同樣享受了灌溉時,少數“搭便車”者便會成為大多數。因為農民“寧可都失利,也不能讓別人獲利”的特殊公平觀,使得總是在集體行動中支付成本的村民被邊緣化,而“搭便車”卻成為擁有話語權的中心人物。解決“搭便車”問題的關鍵在于農村信任、規范和社會網絡等社會資本的重構,以及農村中體制內和體制外權威的重塑。
四、農村公共物品協同供給達成路徑:利益均衡
根據利益相關者理論,農村公共物品協同供給的實現取決于各利益主體間能否達成互利共贏的均衡狀態。而均衡狀態的實現關鍵在于政府主導力的發揮。雖然稅費改革后各級政府自覺進行制度創新,不斷賦予農村社會、農民及非營利組織更多權利空間,促使各政府外主體從“影響”到逐步“參與”,但當下各利益主體“共同治理”局面并未形成[14]。因此政府應從制度層面、運行層面、技術層面著手,推動多方利益主體消除摩擦、由非合作博弈走向合作博弈,形成相對穩定的利益均衡狀態,實現各主體優勢互補、內外聯接、縱橫交錯的農村公共物品協同供給效應。
(一)制度層面:創新利益相關者參與制度保障
農村公共物品各利益主體要形成持續有效的互動秩序,首先應將各主體參與農村公共物品供給行為納入制度化剛性軌道。從農村公共物品供給實際及各主體利益需求出發,規范各主體行為責任追究及權利義務保護相關規定、明確農村公共物品供給市場準入條件、嚴格考核指標體系與程序、放寬非營利組織注冊要求,并給予其合法地位支持等;改革基層政府行政人員績效考核和激勵制度,對基層政府公共物品供給動機進行正向驅動;此外還應創新信任評審制度。多元利益主體參與農村公共物品供給從理性角度看,是因他們能從中獲得利益訴求的滿足,但在各利益主體深度交互過程中,對合作利益與風險的感知不僅是通過理性計算,同時要受到情感反映和文化取向的綜合作用。其中,信任是合作能夠達成的基礎[15],尤其是解決農村公共供給中村民“搭便車”行為的重要因素。因此傳統農村社會熟人信任應當與制度信任相結合,通過一整套持續性的評審體系,將政府、非營利組織、企業組織、村委會與農村居民供給行為進行信任審核,并建立信任檔案和懲罰激勵制度,以利于各主體規避風險,達成利益共贏的有效協作[16]。
(二)運行層面:理順利益相關者責權利關系
農村公共物品供給中,政府自身變革是驅動多元利益主體從“影響”、“參與”到“共同治理”的關鍵。為推動協同供給的達成,政府需從縱向和橫向兩個維度有意識地進行調整,以理順各利益主體在農村公共物品供給中責權利關系[17]。縱向維度通過分權化改革調整行政組織權力結構,中央政府權力適度下放,同時改革中央和地方財政收入比例關系,加大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力度,促進基層政府在農村公共物品供給中事權和財權的復位,尤其要扶持加強農村集體經濟實力,提供村委會體制內權威重塑的經濟基礎;橫向維度將政府在農村公共物品供給中的職責平行轉移并加以規定,以發揮政府外組織供給作用。目前可依據農村公共物品科學分類,設定不同主體承擔公共物品供給的職能和范圍。如中央政府提供全國范圍內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農村純公共物品,基層政府和非營利部門可提供農村區域范圍內公共物品,企業組織提供農村中那些進入成本不高、外部性不強的收費公共物品,村委會提供村落小范圍公共物品[18]。同時構建多元主體間彈性責任共擔機制,將利益風險在多元主體間“稀釋”,減輕各主體成本負擔。除橫向職責轉移外,還需改變政府單一權力中心,建立權力共享機制,通過資源在多元主體間有效配置,形成利益協調、相互依賴的多元利益主體聯動結構。
(三)技術層面:構建利益相關者信息共享平臺
農村公共物品協同供給實踐中,各利益主體間信息不對稱、溝通不暢是造成差異化利益訴求得不到尊重、利益主體實施機會主義行為的重要因素。因此,農村公共物品協同供給在技術層面上,需要構建一個公開透明的現代化信息平臺,暢通信息反饋渠道、加強信息公開化建設[16]。便于對農村公共物品供給中分散的信息進行采集、分析并及時反饋,為農村公共物品協同供給系統提供決策依據,同時將政府、非營利組織、企業組織、村委會和農民參與公共物品供給行為置于監督之下,可有效約束各利益主體損害共同利益以謀取私利之舉。信息技術的應用,消除了農村物品供給中多元利益主體行為邊界、改變了單向互動,形成整體動態聯動的網絡化聯結,實現了農村公共物品多元利益主體供給的協同效應。
五、結語
當農村公共物品供給領域活躍著超過一個以上的供給主體時,必然產生協同需求。但實踐中協同并不必然發生,如何探究農村公共物品多元協同運行機理需要恰當的理論研究范式。利益相關者理論從多元主體行為邏輯背后的利益關系出發,提供了清晰有效的理論分析路徑。
上述基于利益相關者理論分析框架對農村公共物品供給中多元利益主體、利益互動關系及利益均衡的闡述,意在通過理論抽象對協同供給進行普遍性分析,力求為相關研究推進提供思路。實踐中,我國廣大農村地區正面臨城鎮化進程帶來的急速轉型,不同農村地區情況各異,利益均衡的實現會受到諸多因素影響,并呈現不同的利益均衡形態。在理論探究基礎上,應進一步結合特定農村地區實際情況對農村公共物品供給運行進行個性分析。
[1]汪錦軍,2012.構建公共服務的協同機制:一個界定性框架[J].中國行政管理(1):18-19.
[2]張賢明,田玉麒,2016.論協同治理的內涵、價值及發展趨向[J].湖北社會科學(1):31.
[3]常敏.城鄉公共產品多元供給研究——基于長三角地區的探索與實踐[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141.
[4]羅伯特·阿格拉諾夫,邁克爾·麥圭爾.協作性公共管理:地方政府新戰略[M].李玲玲,鄞益奮,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22.
[5]Freem an,Edw ard R,Evan,William M.Corporate governance:A stakeh older interpretation[J].Journal of Behavioral Economics,1990,19(4):337-359.
[6]R.Edward Freeman.Stockholders and Stakeholders:A NewPerspective on Corporate Governance[J].California ManagementReview(pre-1986),1983:88-107. [7]賈升華,陳宏輝,2002.利益相關者的界定方法述評[J].外國經濟與管理(5):13.
[8]柳春慈,2011.區域公共物品供給中的利益協調機制探討[J].學術交流(7):73.
[9]何繼新,李原樂,2015.社區公共物品供給主體多維分類、角色功能與復合協同治理[J].廣西社會科學(11):161-164.
[10]徐勇,1997.村干部的雙重角色:代理人與當家人[J].二十一世紀(香港)(8).
[11]崔曉芳,2016.農村公共物品多元主體供給中的政府職能研究——基于新公共服務理論的視角[J].山西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1):786.
[12]徐勇.中國農村與農民問題前沿研究[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9:304-319.
[13]宋亞平.關于“以錢養事”的幾點認識[M].三農中國.第8輯.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39-62.
[14]王身余,2008.從“影響”、“參與”到“共同治理”——利益相關者理論發展的歷史跨越及其啟示[J].湘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1):28-30.
[15]Michael Moody.Everyone Will Get Better Together:How Those Responsible for California's Bay-Delta Water System Understand Collaboration[J].International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2009(13):13-32.
[16]何繼新,楊鵬,高亞君,2015.城市社區公共物品多主體協同供給影響因素分析——基于626例樣本的實證研究[J].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1):47-48.
[17]唐任伍,趙國欽,2012.公共服務跨界合作——碎片化服務的整合[J].中國行政管理(8):18.
[18]崔曉芳,2010.論新農村建設中農村公共物品供給主體多元化——基于多中心理論的視角[J].山西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6):661.
(責任編輯:D 校對:T)
D035;F320.3
A
1004-2768(2017)08-0042-04
2017-06-23
山西省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項目“山西省農村公共物品供給主體多元化研究”(2014227);山西農業大學哲學社會科學項目“新型農民培育機制創新研究”(20132-24)
崔曉芳(1983-),女,山西晉城人,山西農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講師,研究方向:農村資源配置、管理創新;王文昌(1962-),男,山西萬榮人,山西農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研究方向:農村土地資源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