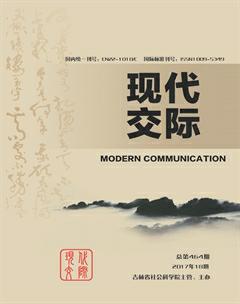我國刑事訴訟中“毒樹之果”的適用問題研究
劉煜瀟
摘要:證據的合法性是刑事訴訟案件中備受關注的焦點。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規定了以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證據要予以排除,但對于“毒樹之果”規則的立法以及司法實踐適用規定不明確其存在較大的分歧。本文分為四個部分對“毒樹之果”規則在我國的司法實踐適用進行分析,其中,第一部分闡述了何為“毒樹之果”,包括毒樹之果規則的起源、內涵及例外情況;第二部分是有關域外各國是如何適用“毒樹之果”規則的以及針對目前我國法律、司法解釋還沒有明文規定“毒樹之果”規則分析了現狀,即學者們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觀點即“砍樹食果”和“砍樹棄果”;第三部分分析了在我國“毒樹之果”規則缺失的危害及我國借鑒該規則的意義;第四部分針對上述的內容對“毒樹之果”在我國司法實踐運用提出可行性建議,希望能為我國司法實踐提供有益的參考。
關鍵詞:毒樹之果 非法證據 證據排除 司法實踐
近些年,隨著公眾法制意識的增強,越來越多人關注司法實踐案件,有相當部分的冤假錯案慢慢進入公眾的視野,而只有少部分冤假錯案得以平反,多數是因為“真兇再現”或“亡者歸來”,這些冤假錯案讓許多無辜的受害者遭受了本不該有的刑事懲罰。從1994年的佘祥林案,1996年的呼格吉勒圖案到1998年的趙作海案,違背了刑法的根本目的,對社會長期和諧健康發展起到了消極的作用。佘祥林案、呼格吉勒圖案、趙作海案都存在違法取證現象,通過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獲得證據為線索,再以此收集其他證據,這就是要研究的“毒樹之果”理論的代表案件。然而我國刑事訴訟法以及司法解釋乃至行政規章都沒有對“毒樹之果”理論的詳細規定,這樣加劇非法取證的行為,在對犯罪人證據不足的情況下指控,只會讓冤假錯案數量增多。“毒樹”派生的證據對冤假錯案無疑產生了決定性的作用,因此對“毒樹之果”是否予以采納和排除要有正確的態度。
一、何為“毒樹之果”
(一)“毒樹之果”來源及內涵
“毒樹之果”這一概念源于美國,簡而言之,是指以非法取得證據為線索間接獲得的證據。[1]“毒樹之果”規則首次出現于1920年的“西爾弗所恩·倫巴公司訴美國聯邦政府案”[2]。從西爾弗所恩·倫巴公司訴美國聯邦政府案中可以看出如果認定執法人員從一開始就存在違法行為,那么審判中,被告人就有可能通過毒樹之果規則將其排除掉。根據毒樹之果規則,執法人員通過非法手段獲得的材料哪怕真的能證明某些真實情況的存在,但在審批過程中也不得作為證據出示,要予以排除。
換句話說,執法人員的執法行為就猶如一條河流的源頭,河流下游的水就好像執法人員執法時獲得的證據,如果河流從源頭就已經被污染了,那么下游的水也因此變得不清澈干凈了,整條河流都被污染了。這就好比整個司法系統,如果從一開始便是違法的,則會傷害到整個司法體系。因此,來源于美國的“毒樹之果”的內涵便清晰可見,不僅要排除通過違法手段獲得的證據,而且對據此手段獲得的其他證據材料也要排除。其內容主要包括:非法行為所間接獲得的證據;與違法收集密不可分的證據;以違法收集為線索發現的證據;以違法取得的證據引誘他人所獲得的證據;違法取得口供后再次訊問得到的口供;非法行為后多重間接得來的證據。[3]
簡單來講,此規則就是偵查人員通過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獲得某項證據,進而又利用此非法證據取得的派生證據。其中偵查人員通過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獲得某項證據是所謂“毒樹”,由其中獲取資料進而獲得的其他證據是毒樹的“果實”。[4]
(二)“毒樹之果”規則的例外情況
毒樹之果規則在阻止執法人員違法取證和維護程序正義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有效打擊犯罪,但司法實體公正可能會難以實現。這樣的規則使得執法人員的錯誤讓社會公眾承擔后果,結果導致罪犯獲得好處,這樣做是不公正的,因此美國法院通過權衡,通過一系列的案例,逐步確立一些例外,使得毒樹之果理論的弊端得到緩和。“毒樹之果”規則例外主要包括三個方面:污染中斷,獨立來源以及必然發現。[5]
首先,污染中斷的例外。污染中斷的例外是指執法人員在執法過程中通過非法手段獲得某些證據,如若執法人員通過非法手段獲取證據的相對人在此之后自愿作出某些行為,此行為可以將執法人員的非法行為與由此非法手段獲取的證據的因果關系切斷,則之前通過非法手段獲得的證據不需排除,仍然可以采納適用。消除污點例外規則的理解關鍵是:相對人在執法人員非法手段獲取證據后作出的自愿行為是否能排除當初執法人員的違法行為。
其次,獨立來源的例外。獨立來源的例外是指執法人員在搜集相關證據之前也用過非法手段對待此證據,但是若能證明執法人員搜集的相關證據和之前用過的非法手段之間不存在任何關聯,換句話說,執法人員搜集的證據是完全獨立于之前的非法手段的,這些相關證據仍然可以在審判中采用,無需排除。
最后,必然發現的例外。必然發現的例外是指如果有充分且清晰的證據證明在執法人員沒有使用任何違法手段的情況下,根據客觀的情況執法人員仍能夠發現該證據,那么該證據就是必然被發現的證據,在法庭上法官予以采納。但要說明一點,必然被發現的證據必須是令人信服且充分清晰,達到這種程度才能在法庭上予以采納適用。
二、“毒樹之果”規則在域外的適用及在我國的發展現狀
(一)域外關于“毒樹之果”規則的適用
在美國,“毒樹之果”來源于美國納多恩訴合眾國案,發生在1939年,所以毒樹之果理論在美國的刑事訴訟中最早應用,相比于其他國家也是最成熟的。美國實行三權分立的治國理念,基于這樣的理念,美國在司法實踐中一定會通過嚴格的司法程序加以限制偵查機關的偵查活動。因此,比起實體正義美國更加追求程序正義,美國刑事訴訟中確立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和“毒樹之果”理論在司法實踐中的不斷發展就是最好的體現。美國最高院在納多恩訴合眾國案的判決書中寫到,法律規范真正的精髓在于不僅要禁止以某種方法取得的證據,不得提出適用,更要禁止一切適用。由此毒樹之果理論運用由此誕生,德國稱之為波及效。[6]endprint
在英國,根據英國的普通法,適用排除“毒樹”而食用“果實”的規則,即對于從被排除的被告人供述中發現的任何證據和事實,只要具備相關性和其他條件,就具備證據的可采性。舉這樣一個例子,偵查人員通過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得到了被告人的口供,內容中提到被告人作案場所中的某位置放有作案時攜帶的工具,偵查人員并據此供述找到了作案工具會采納。因此英國在“毒樹之果”規則適用方面與美國不同。
在日本,“毒樹之果”理論在司法實踐中的適用基本與英國的做法一致,即對通過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獲得的原始證據要予以排除,在此基礎上獲取的其他證據可以使用。德國與日本在刑事訴訟法中有關“毒樹之果”司法適用的態度趨于一致,但在歐洲大陸的其他國家情況可能完全不一樣,有些國家不僅以不合法手段獲取的證據要排除,而且利用此證據再獲取的其他證據也不可以使用。
(二)“毒樹之果”規則在我國的發展現狀
隨著冤假錯案的增多,偵查人員通過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搜取證據的行為被頻繁曝光逐漸進入大眾的視野,隨之而來“毒樹之果”規則在我國也就被經常提起。我國對“毒樹之果”規則沒有完整的立法,就此現狀下刑事司法理論界大致分為兩大陣營:一種主張“砍樹棄果”,其價值取向是保護被告人的利益優于懲罰犯罪,另一種主張“砍樹食果”,其價值取向是懲罰犯罪優于被告人利益的保護。[7]
一些支持“砍樹棄果”的學者們價值出發點在于比起懲罰犯罪,被告人的利益更為重要。這些學者們認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砍樹棄果”可以規范偵查人員的行為,杜絕濫用職權侵害公民的合法權益。其次,一個法治國家應該擁有現代化的法治理念,而不是以毒攻毒,在懲罰犯罪和保障人權兩者相沖突時,自然是保障人權更具有優先性,畢竟,一個國家如果連公民的人權尊嚴都無法保證,偵查人員可以隨意踐踏國家的法律,那么國家的秩序也會相當混亂。再次,“果實”取得的手段是非法的,但是“果實”是客觀存在的,并不一定要通過非法取得證據即“毒樹”取得,可以換為另一種說法“毒樹之果”是否有“毒”歸根結底取決于偵查人員在獲取證據時的方式,而并不是證據本身。“砍樹棄果”是真正實現程序上的公正,能促使整個司法制度更具有正義性,這是程序正義最具有意義的一點,而實體正義僅僅是對某個案件的正義。
其他學者還有另外一種觀點叫做“食果毀樹”,這就比較類似于英國對于“毒樹之果”在司法實踐中的適用規則。“食果毀樹”更加追求實體正義高于程序正義,認為懲罰罪犯、打擊犯罪是首要的任務,這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犯罪行為。但目前我國對“毒樹之果”規則并沒有完整的立法。
三、“毒樹之果”規則缺失的危害及借鑒的意義
(一)“毒樹之果”規則缺失的危害
自新刑訴訴訟法頒布后,由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衍生的“毒樹之果”規則的確立就尤為重要,非法證據排除規矩盡管會放縱犯罪,但其最大優點就是保證言辭證據的自愿性,從而達到定罪處罰的準確性,同時能切實保障訴訟參與人的確立,因此,這一規則的確立,是一國文明水平的標志,體現了從懲罰犯罪第一到注重保護人權的訴訟觀念的進步。[8]因此,此規則的缺失是有一定危害的,主要體現在內容上的不完整以及實踐中出現被架空的情況。在此基礎上,“毒樹之果”規則的缺失更為嚴重結果可能會變相激勵非法取證,最終違背了刑事訴訟法的根本目的,而且會導致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作用減弱以及效果也消失不見。
變相激勵非法取證情況包括偵查人員通過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獲取的證據,或者利用重復供述即偵查人員通過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獲得被告的首次有罪供述,之后偵查人員利用被告人的首次有罪供述帶來的持續影響,再通過合法手段或者程序再次取得有罪供述,即便首次有罪供述會因為利用了非法手段獲取而予以排除,但利用首次有罪供述后的重復供述獲得的有罪供述準予采納。關于利用重復供述規則,一些學者認為在“毒樹之果”規則沒有明確規定時,“使得以重復供述定罪未受禁止,偵控機關完全可以據此規避排除規則的適用”[9],這種情況持續長時間“可能會形成一種政策效應,即偵查機關可能采取先對犯罪嫌疑人實施刑訊逼供,然后再經合法詢問取得嫌疑人有罪供述的策略,以此規避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約束。如此一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將被架空”[10]。
(二)“毒樹之果”規則借鑒的意義
在案件審理中,證據能否被法庭采納對案件審理結果有著不同的影響,因此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對刑事訴訟活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對法庭審理結果占據決定性地位,此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也包括其衍生規則“毒樹之果”。但就目前,在我國刑事訴訟實踐中,現行的證據規則尚不完善,雖然可以排除明顯的非法證據,但無法確定特殊情形下所得證據的可采性。[11]舉例說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1條規定了“用非法方法取得的言詞證據禁止作為定案的根據”,然而對于通過非法手段取得證據進而獲得其他證據的可采性沒有明確規定。司法活動的公正性需要不斷地對證據規則進行修補與完善。
刑訊逼供、非法搜查屢禁不止,根本原因只是對非法獲得的言詞證據予以排除,這樣至多只會讓那些通過刑訊逼供的人再通過“合法”程序詢問一遍罷了,而不可能從根本上鏟除它的根源。[12]而“毒樹之果”規則的適用,能從根源上遏制刑訊逼供的證據規則。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衍生規則“毒樹之果”進行相關立法與規則完善,可以提高司法審判案件的公正性,進而得到的審判結果才更有公信力,不僅可以實現程序正義,更可以實現實體正義。程序關心的是作出決定是所采用的過程和步驟,實體是關心決定的內容。[13]程序與實體相統一,這符合了我國刑事訴訟法的立法要求。
從我國刑事訴訟法立法角度,1996年3 月修正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12條規定體現了“無罪推定”原則,要求偵查人員不能簡單地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視為罪犯,在偵查階段要嚴格按照法定程序進行。[14]“無罪推定”原則對偵查人員的取證活動有一定的指導作用,但無法杜絕刑訊逼供、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取證行為。[15]而“毒樹之果”規則的相關立法可以杜絕不合法取證。另一方面,從偵查人員刑事偵查獲取證據來看,利用刑訊逼供手段獲取的證據可以更加節省成本得到更多結果。但若根據“毒樹之果”規則,偵查人員非法取得證據不得采用,進而取得的其他證據也要予以排除。所以,我國刑事訴訟法對“毒樹之果”規則進行相關立法,可以降低非法取證的可能性,避免冤假錯案的產生,真正實現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endprint
四、“毒樹之果”規則在我國司法實踐領域適用建議
(一)建立相關的立法機制
與判例法系國家不同,我國是成文法系國家,因此在借鑒“毒樹之果”規則時,應該在我國現有證據規則基礎上構建適合我國刑事司法實踐的規則。一方面,“毒樹之果”規則成熟于判例法系國家的實踐之中。[16] 判例法國家的法官在審理案件時,依靠豐富的經驗和具有指導性的判例,能夠比較靈活地作出公正審判。[17]因此不同法系的國家,法官審理案件的依據也是不同的,我國是成文法系國家,主要依據的是成文的法律條文。鑒于如此差異,在對證據規則立法時只能是借鑒判例法系國家的經驗并結合我國實情。另一方面,“毒樹之果”規則本身也存在缺陷,即過度追求程序正義而影響了實體正義。[18]
建立相關的立法可以從幾個方面入手,比如對非法證據種類細化,我國目前有八種證據類型,明確區分之間的不同,按證據類型歸入,有助于提高司法效率。其次,對偵查人員以非法手段獲得證據的認定細化。偵查人員獲取證據時應按照法律及其法規規定的程序進行,禁止使用非法手段,從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五十四條也可以看出,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不得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對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不得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手段收集。因此對于非法手段獲得證據的行為要從根源防止。還有,司法實踐中最重要的仍是保障人權,因此在偵查人員獲得證據后,對于證據的合法性的舉證責任應該進行細化,保證證據真實合法。
(二)提升偵查能力和偵查階段的透明度
提升偵查能力,加強偵查階段的透明度,加大對私權利的保障力度,避免公權力的過度膨脹,對公權力的限制減弱就會對私權利產生不利影響。我國是一個成文法國家,存在一個現象即對公權力限制很少,這就導致對私權利會卻缺少保障。根據大陸法系國家以往的司法實踐經驗,非法證據只要能夠反映案件事實,具有基本的證明力,就具有可采性。[19]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條規定:“刑事訴訟法的任務是懲罰犯罪分子,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將刑事訴訟活動側重于對罪犯的懲罰會導致對公民私權利的侵犯,甚至會使無罪之人蒙冤[20],嚴重違背了我國刑事訴訟法的目的。盡管我國在限制公權力的膨脹,而且在刑事訴訟法中對違法取證行為的禁令也明確進行了規定,但在司法實踐中卻沒有配套的禁令措施來確保其實施。因此,我國在建立“毒樹之果”規則時要統籌兼顧,對偵查人員通過非法手段獲取證據的方式進行規范,進而減少違法取證行為,確保實現對公權力的限制;偵查人員取證水平要進一步提高,提高涉案證據對待證事實的證明力,還原事實真相,最終達到保護案件當事人合法權益。
(三)完善程序性裁判,保證國家公正審判
我國是大陸法系國家,法官保障了法官在對非法證據的排除提供依據,維護刑事審判程序的公正性以及合理性在保證公正審判中有著重要的地位,因此為了保證每一樁案件都能公正審判,首先要完善程序性裁判。在美國最初設立“毒樹之果”規則是在審理階段,為確保非法證據規則嚴格適用,我國對法庭審判程序和規則也進行了細化。為解決訴訟中取證行為合法性以及非法證據可采性問題,應完善程序性裁判。案件在進入第一審程序之前,若被告方當事人或其律師對涉案證據取證的合法性產生懷疑時,被告人當事人或其律師可以向法庭提出申請,對產生的懷疑法官先進行程序性裁判。案件在審判中,如果控方和辯方對偵查機關的行為以及獲取涉案證據行為的合法性存有爭議,可以申請程序性裁定,但法官必須先暫停實體性審判程序,針對爭議舉行司法聽證會。在案件審理過程中的任何階段,法官有權利要求控方提出能證明其可采性的證據,也有權要求偵查機關證明其取證活動的合法性。如果控方和辯方不認可裁判結果,抗辯雙方可以申請上一級人民法院再次審查裁判。
簡而言之,目前我國刑事訴訟法沒有明文規定“毒樹之果”規則,但此規則的缺失卻會對司法實踐帶來負面影響,因此應當在汲取美國毒樹之果規則的實踐經驗基礎上,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來科學立法,而不是一味地照搬照抄。通過科學立法提高偵查人員的能力和偵查階段的透明度以及完善程序性裁判,使得我國刑事訴訟案件在處理時更加公正,減少冤假錯案的發生,避免無辜的被害人承受不應有的懲罰。
參考文獻:
[1]陳光中,徐靜村,刑事訴訟法學[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0:190.
[2]喬恩·R·華爾茲.刑事證據大全[M].何家弘譯.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4:42.
[3]楊宇冠.毒樹之果理論在美國的運用[J].人民檢察院,2002(7).
[4] 樊崇義.刑事訴訟法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279.
[5]李秋芳.毒樹之果理論之探討[J].法治與經濟(中旬刊),2009(2):95-96.
[6]宋英輝,甄貞,劉廣三.刑事訴訟法學研究述評[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604
[7]閆海.非法證據的衍生證據規則探討——美國毒樹之果理論述評[J].社科縱橫,2016,21(2):76-77.
[8]陳衛東,李奮飛.刑事訴訟法理解與適用[M].北京:人民出版社,2102:123.
[9]龍宗智.兩個證據規定的規范與執行若干問題研究[J].中國法學,2010(6):22.
[10]萬毅.論“反復供述”的效力[J].四川大學學報,2011(5):139.
[11]汪海燕.論美國毒樹之果原則——兼論對我國刑事證據立法的啟示[J].比較法研究,2002(1):65-74.
[12]陳潔.“毒樹之果”原則在我國刑事訴訟中的可行性研究[J].刑事訴訟,2011(3).
[13] 邁克爾·D·貝克爾,程序正義——向個人分配[M].鄧海平譯.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7.
[14]崔敏.刑事訴訟與證據運用[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6:74.
[15]房保國.刑事證據規則實證研究[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212.
[16]田口守一.刑事訴訟法[M].劉迪,張凌,穆津等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26.
[17]何家弘.證據法學研究[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241.
[18]保羅·蘭德.有組織犯罪大揭秘[M].歐陽柏青譯.北京:中國旅游出版社,2005.
[19]卡斯東·斯特法尼,喬治·勒瓦索,貝爾納·布洛克.法國刑事訴訟法精義(上)[M].羅結珍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56.
[20]羅納德·J·艾倫,理查德·B·庫思期,埃莉諾·斯威夫特.證據法——文本、問題和案例[M].張保生,王進喜,趙瀅譯.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61.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