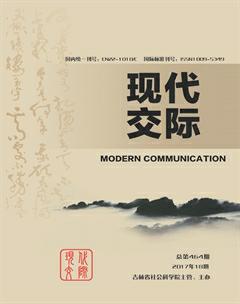社會熱點事件微信刷屏現象的分析與反思
摘要:“羅爾事件”在微信朋友圈刷屏的現象,是網民出于維系社交關系、完善網絡環境、構建認知的目的所驅使。網民的行為、認知心理會隨著進程的變化,不斷呈現出新的特征,并轉而影響、推動事件的發展。促使網民向理性的朋友圈轉發行為回歸,需要強化大眾媒體內容生產與傳播的責任,提升網民的媒介素養。
關鍵詞:羅爾事件 微信 刷屏
新媒體時代,人們對社交媒體的使用與依賴不斷加深,同時社交媒體也改變了人們的溝通與思維方式。作為當下使用最為廣泛的社交媒體,微信在網民發表言論、表達思想、動員慈善活動等領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而與之相伴生的熱點事件在微信朋友圈刷屏的現象頻繁出現。2016年末,文章《羅一笑,你給我站住》刷爆朋友圈,獲得微信打賞金額超過200萬元。一個月間,羅爾、小銅人、網民、各家媒體輪番登場,原本看似單純的個人募捐事件經歷了模糊、反轉、清晰的復雜過程,網民的行為、認知心理也隨著進程的變化,不斷呈現出新的特征,并轉而影響、推動事件的發展。
一、相關背景
羅爾曾任深圳某報社編輯,其女兒羅一笑于2016年9月被確診為白血病。羅爾在其微信公眾號“羅爾”發文表達對女兒的憐惜和作為父親的心痛,獲得廣泛關注。其后羅爾與微信公眾號“P2P觀察”合作發布《羅一笑,你給我站住》等一系列刷文,短時間內獲得微信巨額打賞。不久有消息稱羅爾本人名下有房產、汽車和廣告公司,羅一笑的住院費用遠沒有文章中所述那樣高昂,“羅爾事件”被批為“帶血的營銷”,社會輿論傾向于對羅爾及公眾號“P2P觀察”進行聲討。之后又有媒體證實羅爾的真實經濟狀況并不樂觀,部分民眾轉而對羅爾表示同情。最終“P2P觀察”“羅爾”兩個公眾號決定將所獲資助退還給網友。
二、“羅爾事件”刷屏現象分析
法國心理學家、社會學家古斯塔夫·勒龐在《烏合之眾》中寫道:“有時,在某種狂暴的感情——譬如因為國家大事的影響下,成千上萬孤立的個人也會獲得一個心理群體的特征。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偶然事件就足以使他們聞風而動聚集在一起,從而立刻獲得群體行為特有的屬性。”[1]熱點事件在微信中的刷屏,其本質上是一種人際傳播。“每轉發文章一次,就可以幫羅一笑籌款一元”,網友們在受眾與傳者的身份間不斷變換,使得文章《羅一笑,你給我站住》在朋友圈中進行著病毒式的傳播,是社交關系維系、網絡秩序完善、認知構建共同驅使了“羅爾事件”的瘋狂刷屏。
一是建設穩定社交關系的需要。維系穩定的社交關系,保持朋友間的情感與信任,一方面需要保持與好友的有效交流,一方面需要樹立自身的群體形象。對熱點事件的轉發是重要途徑,無論是依托于親朋好友的強關系社交圈子,還是基于某種利益需求臨時搭建的弱關系社交圈子,想保持活躍而不是變成沉默的“僵尸關系”,都需要交流有共鳴的話題。[2]慈善事件的社會動員會強化塑造人際交往中的積極形象,出于個體公共精神、網絡形象的凝練與展現,網民以積極的態勢涌入“羅爾事件”的慈善社會動員之中,不僅主動地轉發,還發動自己的親朋好友轉發。
二是形成完善網絡秩序的需要。和諧網絡秩序的構建,需要群體道德在網絡中達成共識、彰顯,這一過程離不開每一個網民“自我”的道德責任感的生成和積淀。在事件進程的不同時期,這種推動事件傳播的道德責任的表現是不同的。在“羅爾事件”的初期,這種道德責任體現為對個體的生命價值和生存的尊嚴的關注。標簽“白血病”“五歲”“女孩”、“父親賣文”很容易引發網民的同情心,網民會情不自禁地擔心女孩的病情,并為羅爾的不幸感到惋惜,此時已經不自覺地產生“移情”。網民為羅一笑的病情焦灼,擔心治療費用的不足,會利用微信打賞;當有與自己向左的意見產生時,會為此與他人爭論。此時網民已不再以旁觀的立場看待“羅爾事件”,而是主動置身其中,帶有強烈的主觀色彩,積極地轉發、打賞。而在事件的后期,這種道德責任體現為對誠實守信的關注,當羅爾被揭露出擁有相當規模的財產時,受眾發現自己被欺騙與利用,情緒由同情轉為憤慨,開始對羅爾進行譴責,轉發相關內容,最終促成了輿論反轉。
三是認知構建的需要。碎片化的閱讀習慣決定了網民更多地會去關注簡化的事實,以降低認知成本,但這并不意味著人們不關注事實與真相。在“羅爾”事件的逐步發展中,越來越多的信息沖擊著人們的固有認知,促使網民廣泛參與到事件的討論與轉發之中。在“羅爾事件”初期,患兒加貧困的模式使人們根據既有的認知將羅爾認定為需要幫助的對象,采取一貫的應對策略,表現出強烈的關懷,這使得文章廣為轉發。而在后續的發展中,媒體報道與已有信息的沖突不斷出現,超過了受眾對本事件既有認知的邊界,民眾對自己的行為作出反思,為事件超出自己的“刻板印象”而產生恐懼,進而產生對類似事件新的認知與應對策略。
三、“羅爾事件”刷屏現象反思
(一)強化大眾媒體內容生產與傳播的責任
“羅爾事件”的裂變不是一蹴而就的,在這個過程中,受眾的非理性行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對事件邏輯上的清楚認識。無論是羅一笑的醫療費用問題還是羅爾的資產問題,都涉及受眾不了解的知識增量。然而回顧“羅爾事件”的整個進程,特別是《羅爾說“羅爾事件”》發文之后,各家媒體發布的較有影響力的幾篇報道卻呈現出分裂的狀態。有媒體復盤“羅爾事件”,將羅爾的解釋轉化為第三方描述,缺乏可信度,也沒有為網民提供新的認知增量,因而被指責不夠客觀;有媒體將視角放在大病醫保報銷的問題,然而此事件中深圳的兒童醫保是全國最完善的醫保,羅一笑的大部分治療費用也被報銷,在這一事件背景下探討大病醫保困境并不恰當,只會制造新的對立與困局。[3]
正如《南方都市報》深度報道部主任龍志所言:“沒有可靠、連貫而系統的事實,每一個人看到的都是一個面,隨之產出的評論、批評和做各類邏輯推演都可能是不準確的,不僅沒有解決問題,還可能制造新的對立和撕裂。”[4]媒體應該對相關信息源進行相互印證,發揮權威性、專業性信息源的優勢,對這些內容進行梳理,彌補受眾的知識盲點,幫助受眾在紛繁交錯的信息中找到符合大眾認知、梳理理性邏輯脈絡的事件真相。endprint
(二)提升網民的媒介素養
作為整個事件的傳播主體,羅爾曾任雜志《新故事》主編,熟悉網民心理,了解如何在新媒體中進行傳播。其微信公眾號原本就匯聚了大量的粉絲,本質上這是由意見領袖發起的傳播活動。同時其發表的文章經過了精心的打磨,按照受眾“喜歡”的模式進行塑造。這樣符合受眾胃口的內容,看起來順眼,再加上“羅爾”公眾號具有的粉絲基礎,大規模傳播水到渠成。
而在事件的微信傳播中,受眾的媒介素養表現得極不成熟。一方面人際傳播降低了人們對信息真實性的敏感,很多人往往沒有對“羅爾事件”進行全面了解就投身其中,“推波助瀾”,成為下一輪信息傳播的發布者。另一方面,人們更想去表達而不是了解,會主動地選擇忽視完整報道、深度分析,關注一些經過篩選的所謂關鍵信息,乃至只言片語、翻黃倒皁,只要這些信息印證我們觀點。表面看起來這樣的內容傳播容易引起共鳴,但本質上是一種“傳謠”的行為。[5]
媒體人與受眾媒介素養的巨大差異,使得在“羅爾事件”的傳播中,網民始終處于被動狀態,網民的愛心與熱情被不斷地被消費、磨滅。直接后果是網民對羅爾本人的質疑與否定,而更為嚴重的后果是網民對非制度化募捐的質疑與憂慮,會懷疑募捐過程中存在信息不透明,慈善資源可能被濫用、慈善資源分配不公等問題,進而影響到整個慈善公益事業的健康發展。因此有必要高度重視網民媒介素養的提高。作為網民首先應樹立對網絡媒體與信息質疑的意識, 在信息洪流中保持清晰的頭腦,能夠進行科學的評估與理性的批判。其次網民應提高網絡信息的探索、過濾、分析的能力,能夠自主選擇網絡信息進行閱讀。再者,在參與網絡公共事件過程中,應保持理性,降低情緒感染,加強對自身合法權益與邊緣弱勢群體利益的關注。最后,網民應重新審視自身的信息獲取渠道,注重對主流媒體與傳統媒體的關注,消除關注單一媒體帶來的認知局限。[6]
四、結論
“羅爾事件”引起的軒然大波并沒有讓人們對新媒體慈善失去信心,反而豐富了其看待問題的角度,對類似事件抱有更客觀、理智的態度。在爭議性事件報道中,大眾傳媒應深入挖掘事件真相,堅持正確輿論導向,把握話語權。全社會應加強傳媒教育,不斷滲透并強化民眾的責任意識,提升民眾媒介素養,合力塑造健康的網絡環境。
參考文獻:
[1](法)古斯塔夫·勒龐.烏合之眾[M].馮克利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2]彭蘭.碎片化社會背景下的碎片化傳播及其價值實現[J].今傳媒,2011(10).
[3]白佳慧.看媒體人在羅爾事件上如何分裂[DB/OL].[2016-12-10].http://media.sohu.com/20161210/n475512147.shtml.
[4]任孟山.從“羅爾事件”看意見過剩與新聞稀缺[J].傳媒,2017(1).
[5]易艷剛.“后真相時代”新聞價值的標準之變——以“羅爾事件”為例[J].青年記者,2017(2).
[6]夏維波,王鵬.如何培養“有尖、有棱、有底”的金剛石型人才——新聞出版應用型人才“331素質”培養策略探索[J].中國出版,2017(6).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