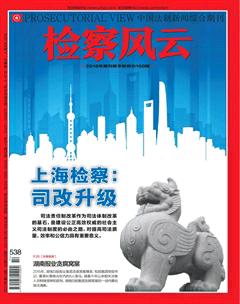王澍:黃金十年的冷思考
一段時期以來,我國在古建筑保護方面存在誤區,一些地方為了GDP對古建筑大肆拆除和破壞。近年來,隨著黨和國家越發強調對傳統文化的保護和傳承,越來越多的人也認識到,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要實現“中國夢”,必須立足于優秀的傳統文化之上,而有效地保護古建筑則是保護和傳承優秀傳統文化的題中之意。
建筑在當代中國的變化
《檢察風云》:2005年你的寧波五散房項目和寧波博物館榮獲國際 HOLCIM 可持續建筑大獎賽亞太區榮譽獎,2010年你又設計了上海世博會寧波滕頭案例館,怎么做這些項目的?寧波這座城市為什么會在你的作品中占據如此重要的位置?
王澍:寧波是我特別喜歡的城市,這個城市非常開放。有人說寧波是商人城市,沒什么文化。但是商人有商人的特點,他們干凈利落,不拖泥帶水,事情每次都做得特別清楚。而且,也許是寧波缺乏文化,所以它才特別重視文化的討論。
寧波美術館的原址是寧波老碼頭的碼頭候船大樓。這樣的碼頭,在中國近幾十年來很多,它們也是傳統的一部分。那次去看現場,有些藝術家看了之后就覺得,這個空間非常好,非常適合做美術館。但是,如果新建大概需要2個億,如果是改建,又省錢又保全了地區的一段文化歷史。寧波方面很快就接受了我們的提議,我們的方案也中標了,這是一個以保護為前提的方案。里面的空間完全被保護,包括里面的信號塔都被保護下來。我們又拓展出來,將里面的空間和外面的現代城市空間銜接,我們稱之為“高臺院落”,是一個非常特別的設計。
規劃局一開始一直拖著不批,因為不理解。寧波博物館也是,那地方有“小曼哈頓”之稱。結果我就做了那樣的建筑,有人就說,在這樣現代化的新城的中心,你用這么舊的材料做這樣的博物館,是什么意思?我當時真是很擔心,當腳手架拆完之后,可能出現一個比他們想象還要奇怪的建筑物,寧波市民是否會接受它?會不會提出強烈抗議?盡管有各種各樣的意見,但是我還是得到了很多的支持,畢竟,這件事情還是做完了。
后來他們請我去寧波的天一大講壇開講座,講寧波博物館的設計,來了上千人,我發現,如果我去和這些聽眾毫無保留的交流,他們都會特別高興。事實上,大家對寧波博物館也很認可,這從每天參觀的人數就可以看得出來,第一天的人流就突破了一萬大關,一個月達到了一百多萬,以至于寧波博物館連續三個月沒有安排館休日。
《檢察風云》:中國的建筑文脈有斷層,這是不是讓我們在面對西方話語的時候特別沒有自信,特別容易跟風?你覺得一個中國建筑師,堅持自己的文化傳統和建筑語言,是否就能和西方建筑師分庭抗禮?
王澍:在一個西方建筑話語占主導地位的今天,我們會有很多的迷惑和迷失。已經有一些先驅做出了他們的努力,比如童寯先生,比如楊廷寶先生設計的和平飯店,但是并沒有得到很好的繼承和總結。和平飯店那是新中國成立之后里程碑似的作品,但基本上沒有一個尊重好作品的意識。就像我的某些作品,想要去拍兩張照片都拍不了,空調機在外面亂掛,里面肆無忌憚亂改造,有的甚至已經被拆掉。有些朋友打電話來說:“你不感到憤怒嗎?這些作品在中國是什么位置他們難道不知道嗎?”我說我一點都不奇怪,我剛做完的時候,有人就想炸掉它。我就說把它們當當代藝術,這就是中國現實中發生的事,我也想拿個大相機去現場拍一下,王澍的作品現在就是這樣子了!我并不是一個追求永恒建筑的人,我感興趣的是建筑在當代中國的變化。
一個中國建筑師如果一直堅持做具有中國本土特色的建筑,那么他們和來華的西方建筑師就有各自的優勢,如果他們也做完全西化的建筑的話,那競爭就會比較激烈。很多中國建筑師都害怕趕不上西方的潮流,可是你要知道,你再怎么追趕,你都是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而已。你要知道真正的流行都是從自己的文化淵源中流淌出來的新思想、新設計,拋開了這個文化淵源來談流行其實沒有意義。所以我認為,在自己的文化背景中來思考當下建筑的趨勢,反而容易被人們接受。這些年我都在國外做這樣的工作,很苦,但是發現西方特別有了解中國的欲望,這種相互理解需要更多相互交流才能獲得。
早些年,國內大的建筑設計院幾乎都是給西方建筑事務所畫施工圖的,幾乎沒有自己設計的機會,這兩年已經有變化了。
“我和李漁在一起!”
《檢察風云》:“錢江時代”是你做的唯一一個商業項目,怎么會做起商業性的項目來了?在造型上又非常特別,是怎么考慮的?
王澍:對,錢江時代6棟高層住宅,這是我唯一一次為房地產商做設計。20世紀90年代末的時候,有一些青年建筑師發起了“實驗建筑運動”,做一些非常有探索性的設計。但是有一次開會的時候我說,如果我們這批建筑師總是在做藝術家工作室、茶室這類非常小規模的設計探索,我們就不能稱之為實驗建筑運動。在我看來,實驗建筑運動,首先要直面中國正在發生的變化與現實,對中國變化與現實中暴露的問題給予正面的回答。房地產在一個城市中,基本上都要占到90%的量,這是整個城市建筑中的主體,如果我們這批建筑師缺席的話,我們很難說我們的實驗是有徹底性的。我說我要嘗試著做一個商業性的項目,但是非常困難。因為房地產基本上都以追逐利潤為目標,一個追逐利潤的行業你要求它在建筑上有所探索,探討藝術的問題、生活的問題,肯定有市場的風險,其實是非常困難。
“錢江時代”的房地產開發商,我們從一開始見面喝茶聊天,到最后他拍板做我的設計,整整用了兩年時間。我記得那一天,他跟我說:“我下定決心了。我也理想主義一次,我們來做一下。”
我是從中國傳統的生活經驗出發來做這個設計的。我記得很清楚,第一張圖畫出來,他拿到手直發愣,問我:“你的總平面圖在哪里?”我畫了兩層樓的小盒子,里面住了4戶到6戶人家,我說我的基本觀念是這棟樓,不管造多高,要讓大家回到住在兩層樓房子里的感覺,這個兩層樓有一個很深的陽臺,我們也可以稱之為院子,這個陽臺上一定要有1米以上的覆土,可以種6米以下的樹,不同的家庭可以種不同的樹。我可以站在底樓說,那個種著桂花的是我家,那個種著玉蘭的是我家。后來我就把這樣的小盒子摞起來,成了6棟100米高的高層房子,這里面不僅包含了造型方面的探索,其實也是中國人生活經驗的延續和文化身份的重新定位。
很多人認為我是不是反對造高層建筑,其實在中國,這么多的人口,高層是不可避免的,但問題是如何讓高層不是簡單的標準化公寓,而是能成為某種生活經驗的延續?整個西方現代建筑的興起就是從住宅建筑開始的,“一戰”之后,城市被破壞,工業興起,出現大量的工人,建筑師開始在這個領域里嶄露頭角。用快速、廉價的方式來解決居住的難題。一開始就有很多的爭論,完全標準化的住宅是典型的資本主義的住宅,那是把工人安排在流水線上,用最簡便的方式來安排你的生活,用馬克思的說法,是把異化的人作為前提來生活的。
《檢察風云》:近十年來,房地產迎來了黃金十年,中國城市化的進程也如火如荼。對于中國現在的城市發展方向,你持什么樣的立場?
王澍:現在中國那些高樓大廈,我看了都挺反感。城市的街道是供人漫游,不是用來跑車的。所以我說上海還可以算城市,北京只剩下交通大馬路了。沒有街道的城市還能稱之為城市嗎?所以說上海非常幸運。我們不知道什么是城市,什么是現代城市,就在那盲目地開發城市。用寬大的馬路圍合超級市場和住宅區,這是城市嗎?這是典型的美國郊區啊!
我在80年代以言論激烈著稱,90年代沉默,2000年以后埋頭做實踐。這是因為,我覺得建筑問題,光靠討論是不夠的,需要有人做出實實在在的作品。杭州的“錢江時代”樓盤設計,它提供了一種尺度,一種建筑和周邊景觀環境關系的樣板。它回答了一個問題:現在中國要不要建高層建筑,基本上在怎樣的一個體量?我們測算過,七八層樓就夠了,根本不需要造得特別高,就能滿足城市人口的居住需要。高層,滿足的其實是欲望!那是某種權力、財富和表達的欲望!它和生活本身的美好無關!
《檢察風云》:中國的城市正在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到處都是拆遷和工地,對此你怎么看?
王澍:現在城市居民在城市里反復搬家,都成“移民”了,都找不到自己的老家在哪了。歷史形成的社區整個瓦解了,新建的住宅區都沒有社區的觀念,這些是公共建筑嗎?它們連最基本的社區結構都不存在。“保護性拆遷”是個很荒誕的問題。集體化大生產、大商業是現代社會的一個大背景,這是直接導致問題的條件。我有時候甚至極端地說,我根本不是現代的人,我生在17世紀,我和李漁在一起!
編輯:薛華 icexue0321@163.com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