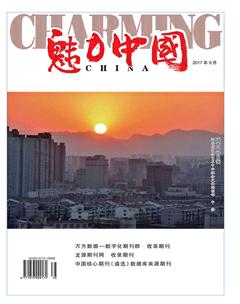腐敗產生與治理的兩個視角
摘 要:在對腐敗問題的研究中有兩個獨特的視角,即理性個體效用視角和社會經濟轉型視角,對認清腐敗的本質以及我國現階段腐敗問題的整體狀況有優越的作用。從這兩個角度提出的腐敗防治對策,對今后的反腐理論和實踐也應當有借鑒作用。
關鍵詞:腐敗;個體效用;社會轉型
腐敗,簡單來說就是指以公權謀私利,是“公共權力的非公共運用”,即運用公共權力實現私人利益的行為,其基本特征是公共權力及公共權力的非公共運用。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的腐敗狀況趨于惡化,學術界對腐敗問題的研究逐漸進入了一個高潮階段,并一直保持著足夠的熱度,相關文獻汗牛充棟。而在眾多腐敗問題的理論與對策分析中,有兩個較為獨特的視角對于我們認識腐敗的本質、認識我國腐敗的形勢有所裨益,或許值得我們繼續深入進行探索。
一、腐敗產生與治理的個體效用視角
在對腐敗問題的認識上,傳統的理論曾長期把其看成是由一時的沖動而引發的非理智行為。李懷(1996)指出,這種觀點在現實中是遭到否定的[1]。若這種非理智主義的解釋能夠成立的話,則權力腐敗應當僅表現為一種偶發性現象,而現實情況卻并非如此。在權力運行的現實中,權力執掌者的行為選擇首先取決于其欲望和動機。按照經濟學的一般方法,可以合理假定權力執掌者都是具有利己私心的“理性經濟人”,如果假設現行制度的缺陷使得:①腐敗行為的約束條件為零;②腐敗的行為后果的社會懲罰率為零,那么權力行為的動機就完全取決于權力執掌者對效用的價值判斷和追求。即是說,在自我約束無力、外部約束缺乏的情況下,腐敗行為的發生有必然性。同一時期,相似的觀點被大量的學者提及。程厚思和曹文(1997)指出公職人員的理性自利心理是腐敗的動力來源;而權力配置資源是腐敗行為得以產生的制度基礎,構成了腐敗產生的必要條件[2]。這兩個因素使腐敗的產生存在了可能性,腐敗發生與否依賴于其它一系列主客觀的制約因素,包括掌權者的需求偏好、道德水平、權力制約、法律懲罰等。然而在現實中,自我道德約束的不可靠、外部約束的缺乏和綿軟,使腐敗成本過低、腐敗收益過高,公共權力掌握者作為“理性經濟人”必然會選擇腐敗。樊綱(2000)認為現實中克己奉公、大公無私的官員在數量上是處于少數的,多數人是“有私心”的,這就是“以公權謀私利”的腐敗行為泛濫的內在原因。鄭利平(2001)也提出,對于個人腐敗的分析應更多地從理性經濟和預期效用的角度出發。
從這個角度出發,腐敗行為的產生是由于在自利的心理下,掌握公共權力的人自覺或不自覺地進行成本收益的計算與比較后而做出的理性決策。當腐敗行為的個人收益遠大于其所付出的成本時,“理性經濟人”必然會選擇腐敗。所以治理腐敗的關鍵就在于使腐敗行為成為高成本低收益的行為,許多的反腐對策、手段的原理都可以歸為這一點。這些都需要一個前提,就是完備法制、嚴密法網,增加腐敗被查處的幾率。幾乎所有的反腐對策都會提到要提高腐敗被查處的概率,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建立強有力的監督體系,提高監督機構的獨立性和權威性等。從個體效用視角出發的反腐對策,是要通過多種手段,使腐敗活動成為一種成本收益比極高的一種“不經濟的”行為,則在理性自利的人性前提下,公共權力的掌握者即有腐敗機會的人,必然會理性地選擇不腐敗。
二、腐敗產生與治理的社會經濟轉型視角
亨廷頓在其代表作《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提出一個著名的觀點:社會經濟的現代化進程會導致發展中國家腐敗形勢惡化。這一理論在世界范圍內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受此理論的啟發,很多學者在分析我國90年代以來腐敗形勢的惡化時,也認為社會經濟的轉型是一個重要原因。盛宇明(2000)指出在黨和國家極為重視反腐的情況下,腐敗現象卻愈演愈烈,成為廣泛影響經濟人行為的現象,主要是因為經濟轉型使我國經濟制度存在更多的腐敗供給和對腐敗的更強的需求[3]。過勇和胡鞍鋼(2003)對中國轉型過程中特有的腐敗形式——行政壟斷進行了較為詳盡的分析,認為我國行政壟斷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后舊體制留下來的問題,是中國經濟轉型中最嚴重的腐敗形式之一[4]。在我國經濟轉型的過程中,由于“政企不分”,使得尋租等腐敗行為相當普遍,而且腐敗供給方的主體主要是企業,不僅滋生個人腐敗行為,還產生系統性腐敗。過勇(2006)進一步分析了我國經濟轉軌過程中腐敗蔓延的原因,認為主要在于經濟轉軌和與之相伴的制度變革不同步[5]。具體而言,在中國經濟轉軌過程中,首先是轉軌過程破壞了非正式制度,造成道德敗壞,導致腐敗動機大幅度提高;其次是轉軌過程打破了原有的制度體系,而與新的經濟體制相適應的制度體系建立滯后,造成制度漏洞,腐敗機會大量增加;最后是轉軌過程削弱了制度執行力,造成腐敗行為被發現概率低,制度約束失效。正是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造成我國社會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權力腐敗的蔓延。
這一視角從中觀和宏觀層面關注整體腐敗形勢。在我國經濟體制的改革過程中,制度結構和環境發生了變化,資源從計劃分配到市場配置過渡,權力從中央向地方下放,政府對經濟和社會的管控,企業對政府保護的渴望和依賴,創造了大量的腐敗機會,腐敗的供給方和需求方的數量都大大增加。與此同時,舊的監督體系發生了動搖,而新的權力監督與制約機制又難以在短期建成并發揮作用,制度的缺陷造成了轉型期國家出現腐敗浪潮。
三、小結
從個體效用視角出發去理解和看待腐敗的產生和治理,有助于我們用理性的眼光看待腐敗問題。腐敗現象令人深惡痛絕,但也不是無法理解——以經濟人的思考方式就能很好理解。腐敗是掌權者一種理性自利的一種選擇,那就有可能通過各種手段使權力理性地選擇廉潔的道路。從社會轉型的視角看,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腐敗形勢趨于嚴峻,根本原因在于制度的破與立之間的錯位,反腐的關鍵就在于使制度建設與經濟社會體制改革相適應。十八大后,黨和國家高度重視反腐敗工作,反腐倡廉之戰的“赫赫戰果”也從側面反映了我國面臨的腐敗形勢依然嚴峻,客觀上要求我們繼續深入對腐敗問題的研究。
參考文獻
[1] 李懷.公共權力腐敗行為的經濟學分析及其政策導向[J].經濟研究, 1996(9).
[2] 程厚思,曹文.腐敗行為的經濟學分析[J].經濟體制改革,1997(6).
[3] 盛宇明.腐敗的經濟學分析[J].經濟研究,2000,35(5).
[4] 過勇,胡鞍鋼.行政壟斷、尋租與腐敗——轉型經濟的腐敗機理分析[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3(2).
[5] 過勇.經濟轉軌、制度與腐敗——中國轉軌期腐敗蔓延原因的理論解釋[J].政治學研究,2006(3).
作者簡介: 沈金茂,男,廣西防城人,四川省社會科學院2015級中外政治制度專業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