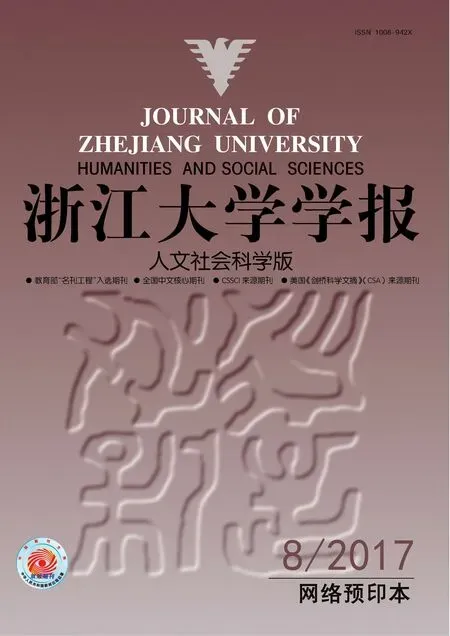《傳奇》的回旋敘事與張愛玲的反線性發展觀
黃 擎 楊 艷
(浙江大學 中國語言文學系, 浙江 杭州 310028)
《傳奇》的回旋敘事與張愛玲的反線性發展觀
黃 擎 楊 艷
(浙江大學 中國語言文學系, 浙江 杭州 310028)
意象、代際與色彩這三重回旋共同構成了張愛玲中短篇小說集《傳奇》的回旋敘事。意象回旋將時間體驗空間化,既支撐起了敘事空間,又使日常生活替代革命而成為永恒的時代主題,傳達了反線性的時間觀。張愛玲不僅從時間觀上反抗線性發展觀,更借助代際回旋將其抵制行為落實到具體的個人之上。代際回旋著眼于代際之間的命運問題,揭示了命運的循環相生,宣告了反種族進化觀立場。然而,反線性發展觀并非張愛玲回旋敘事的終點,而是通向個人價值的橋梁。色彩回旋彰顯了這一特質,紅色系回旋與前進、藍綠色系回旋與守舊分別建立起話語關聯。在紅與藍綠兩種色系的統攝之下,張愛玲塑造了存在于現實與記憶中的兩類人物,使存在的依據由真假判斷轉化為以個人性為標準的價值判斷。
張愛玲; 《傳奇》; 回旋敘事; 反線性發展觀; 意象回旋; 代際回旋; 色彩回旋
自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發掘并論證了張愛玲在中國現代文壇中的重要地位之后,半個多世紀(1961—2016)以來的張愛玲研究多在政治革命范式和社會文化范式下展開。作為對前者的調整,后者強調張愛玲的文學世界相對于政治的獨立性,也由此衍生出張愛玲研究中的現代性反思。受西方影響,中國的現代性觀念以直線前進的時間觀為核心,這既促成了五四時期“基于一個新和舊的價值分野和對立”[1]17的思考及論說方式,更強化了進化史觀在文學史敘寫中的指導性作用①關于這個問題,可參見張春田《革命與抒情》,(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7頁。根據張春田的研究,文學史寫作中存在“革命范式”與“現代化范式”。前者以革命發展為情節主線,突出歷史的進步;后者以現代化為線索,其核心仍是一種前進發展的觀念。。出于對現代性話語強權的不滿,以黃子平、王德威為代表的學者轉而借張愛玲小說與歷史記憶的對話來對抗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單線進化的文學史敘述常規”[2]67。這種詮釋思路便成為張愛玲研究的新風向之一。
其中,王德威以回旋詮釋張愛玲的敘事機制,認為其敘事傳達了一種“與革命或revolution所突顯的大破大立”相反的“反線性的、卷曲內耗的審美觀照”[3]22。王德威從張愛玲“反復改寫與雙語書寫”[4]215的沖動出發,延伸至對《對照記》借舊照悼亡傷逝的探討,體味到其“重復的陷溺的生命觀”[3]26。然而,回旋的提出也帶來了以下問題:第一,除反復書寫同一題材之外,以重復為基礎的回旋能否在文本內部的更多細節呈現中獲得體系性的確認?第二,張愛玲創作的回旋傾向折射出其反線性發展歷史觀,而這一歷史觀又是怎樣作用于個體本身的?第三,反線性發展觀是回旋的終點還是橋梁?換言之,在解構線性發展觀之后,張愛玲的回旋能否步出“重復的陷溺的生命觀”之窠臼并另創新意?本文擬通過探析張愛玲《傳奇》中的回旋敘事,對以上三個問題做出思考。
張愛玲在其最負盛名的中短篇小說集《傳奇》中既編織了一張意象、代際、色彩等多重回旋的網絡,又借此對盛極一時的線性發展觀進行了抵制與反抗。本文使用的回旋敘事概念包含文本和文化兩個層面的意涵:就文本層面而言,回旋敘事指話語層面以重復為基礎的敘事技巧,即包括意象、代際、色彩等要素在內的回旋;就文化層面而言,回旋敘事則指與線性發展觀相對的觀念、情感,甚或文化結構,可凸顯重復帶來的生成性意義。
一、 意象回旋: 對時間的空間性體驗
正如汪暉所言,現代性“首先是指一種時間觀念,一種直線向前、不可重復的歷史時間意識”[5]18,時間構成了現代性統領下的線性發展觀的核心。因此,張愛玲對線性發展觀的反叛必然會貫通于對時間的理解與掌控之中。從《傳奇》文本的時間處理到時代主題的勾畫,張愛玲對待時間問題的態度均呈現出與線性發展觀背道而馳的特點,突出體現在熟練運用意象回旋處理時間問題上。
其一,在敘事時間上,張愛玲以意象回旋的方式將時間物化,甚至轉化為一種空間性體驗。這種處理方式并不致力于打造“未來會很好”的線性發展結構,而恰恰是要構造一種獨立自足的封閉式結構。
張愛玲在《傳奇》中多次使用了意象回旋,通過意象的復現建立了小說文本內部敘事時間的潛在結構。如《金鎖記》的故事情節從月亮開始,又以月亮終結,月亮意象形成了敘事本身的回旋結構,呈現了有別于情節線索的另一條敘事理路。在這一理路中,月亮意象通過回旋的方式融入了時間性體驗。“三十年前的月亮”與“三十年前的上海/晚上/辛苦路/人/故事”微妙交纏,交疊為影影綽綽的幻影,三十年光陰攜著的三十年前的故事與回憶在月亮意象中得以實體化。作品以“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還沒完——完不了”*本文所引張愛玲小說均出自張愛玲《傳奇》,(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作結,月亮的短暫與故事的長久產生了意味深長的矛盾。
上述矛盾的意味深長之處在于它涉及了意象回旋作為“文字的生成者”的一面。意象回旋既可以被視作結構性的點綴,同時也能夠勝任文本其他部分的生成。布賴恩·理查森用“文字的生成者”來指稱這種由幾個精選的語詞生發出事件的做法,它以有別于情節線索的方式完成了敘事的“繁殖”,“成了敘事進程的另一種可供選擇的原則”[6]181。月亮這一意象回旋作為“文字的生成者”的一面直觀地體現在不同形態的月亮對事件的引導和生成意義上。如《金鎖記》以一輪圓月開啟一段對陳舊往事的回溯,待月光下的鳳簫、小雙議論完七巧的流言蜚語,天色已近明亮,天際掛著一彎“扁扁的下弦月”。月亮第三次出現,是在長安命運發生重要轉折的關鍵節點上。由于七巧的無理取鬧,長安決定提前結束學業。是日夜晚,她透過窗格子看到了一輪模糊的缺月。小說接下來兩次提及月亮分別是在七巧套取長白小夫妻間秘密的那兩個連著的夜晚,月亮的影像摻雜在對芝壽、長白、七巧三人畸形關系的描繪之中。張愛玲提到那兩個夜晚都有圓月,圓得好似臉譜,又像一輪白太陽。小說最后一次談及月亮則是在全文末尾,以作為對開頭的呼應。《金鎖記》以圓月的升起開篇,依次歷經下弦月、殘月、滿月,最后落下。這一升一落間,恰好完成了一次盈虧。月亮的回旋不僅承載著敘事進程的發展,亦把握著文章的敘事速度。七巧戴孝之前,長白和長安的故事還未展開,情節發展相對緩慢,月之意象只出現了兩次;而戴孝之后的文本矛盾迭起,月亮便屢屢出現在敘事中。
如前文所述,時間化的月亮不等于故事的時間線索本身,而是擔當了敘事速度的掌控者和敘事進程的生成者之角色。那么,文末“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還沒完——完不了”,看似暴露了月亮的短暫與故事的長久之間的矛盾,實則進一步強化了月亮回旋的反線性價值:三十年前照亮芝壽的那個“灼灼的小而白的太陽”沉了下去,但三十年后,在文本伊始之時,天際重又掛著一輪圓月。月亮的盈虧回旋無窮已,人生的故事也代代無終結。月亮意象的回旋不僅作用于三十年前的上海,也照耀著更為久遠的時間線軸上散落著的更多人物的故事。與之相似,封鎖的鈴聲既構成了《封鎖》的閉鎖結構,又主宰了小說由放松到緊張再復歸放松的敘事節奏。
其二,《金鎖記》中月亮意象的回旋暗含了敘事時間線索的自足性,而《傾城之戀》則借墻這一意象的回旋傳達了更為深遠的時間意義,準確地定位了張愛玲賦予文本的時代主題。流蘇初到香港,柳原便在淺水灣附近的墻邊對她說了一席話:
這堵墻,不知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類的話……有一天,我們的文明整個的毀掉了,什么都完了——燒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許還剩下這堵墻。流蘇,如果我們那時候在這墻根底下遇見了……流蘇,也許你會對我有一點真心,也許我會對你有一點真心。
流蘇與柳原關于墻的第一次對話就暴露了它在文中獨具的意義:墻是一個賭局,賭注不僅是感情的結果,更是文明的結局。無論錦衣玉食之時還是顛沛流離之際,流蘇對那堵墻的牽掛貫穿故事始終。那么,墻的結局又是怎樣的呢?張愛玲的回答傳遞了微妙的分化。劫后的香港,流蘇與柳原擁被而眠,篤信“淺水灣附近,灰磚砌的那一面墻,一定還屹然站在那里”。不僅墻沒有坍毀,而且流蘇身臨夢境般地在墻根下遇見了柳原。換言之,幻想中屹立的墻奇跡般地通向了現實里感情的真實。然而,愛情并不是墻唯一的寓意。在它關于文明的隱喻中,早在淺水灣的炮聲響起之時,“一間敞廳打得千瘡百孔,墻也坍了一面,逃無可逃了,只得坐下地來,聽天由命”,墻的意象早已傾圮。或許為了更明晰地傳達這一點,在描繪情愛之墻的屹立前,張愛玲再次借“斷堵頹垣”提醒讀者——“這里是什么都完了。剩下點斷堵頹垣,失去記憶力的文明人在黃昏中跌跌絆絆摸來摸去,像是找著點什么,其實是什么都完了”。
文明之墻的傾圮與情愛之墻的屹立揭示了張愛玲在文本中對時代主題的洞悉。一方面,文明之墻的傾圮暗示著文明進化的不可維持。有別于五四時期流行的單線發展的時間觀和不可逆轉的進化史觀,張愛玲借用文明之墻的陷落迫使時間在斷垣前停下腳步,將時間性的體驗鎖閉在墻的意象回旋的狹小空間之內。但從另一方面看,她的抱負絕不止于此。墻的意象回旋所顯示的分化顯而易見:文明的墻垣陷落了,但愛情之墻卻存留了下來。更確切地說,正是前者的陷落才成就了后者,“也許就因為要成就她,一個大都市傾覆了”。這里充分體現了張愛玲別具一格的歷史視野:在質疑文明前進發展這一時代主題的同時,借機將男女情愛所代表的日常生活推向了時代主題的寶座,完成了“歷史和日常生活的‘錯置’”[7]125。這是因為張愛玲認為尋常男女“心性與行為雖然難免庸俗卻正是生活的底色和社會道德基礎,于是她便決意逃避崇高宏大的敘事而鐘情于凡俗人物庸常生活的描寫”[8]29。比起線性發展的大敘事神話,張愛玲更認可日常生活通往永恒的可能。
為使意象作為回旋敘事的重要載體在《傳奇》中承擔起敘事時間、時間觀甚至時代觀的重任,張愛玲將時間具體化為月亮、墻等具體物象。而時間的物化體驗的終點是一種空間性:一方面,它既充實了文本的敘事空間,如借助月亮回旋鋪設敘事進程;另一方面,它也為時間與空間這兩個不同的維度構建起橋梁。一如墻之前的狹小空間,墻根前的相遇,墻腳旁的避難,甚或墻的坍塌,均借墻所構成的空間展現了隨著線性時間發展的文明觀的不可維持,日常生活則超越發展與革命成為其筆下的時代主題。
事實上,張愛玲早已注意到了時間與空間之間微妙的關聯。在《傳奇》的跋《中國的日夜》一文中,張愛玲提出,“時間與空間一樣,也有它的值錢地段,也有大片的荒蕪”。空間是計算時間的另一種方法,也是時間存留的另一種痕跡。張愛玲借用空間傳達了反線性發展時間觀:時間并不遵循進化模板,而是會形成與空間相似的荒蕪。
在西方現代性視野中,中國作為一個停滯的“他者”形象,襯托出線性進化史觀這一西方現代性體系核心的合理性。黑格爾就曾將中國視為一個處于時間與歷史之外,“自己產生出來,跟外界似乎毫無關系”[9]119的空間,單一恒久地重復著自己,而西方則在發展的時間敘事之軌上運行。然而,“黑格爾將中國的停滯絕對化,這樣不僅否定了中國的進步,甚至也否定了中國的停滯”[10]12,使得空間之于時間、中國之于西方、停滯之于發展構成線性進步史觀的內在機理。但在《傳奇》中,線性發展的時間敘事以意象回旋的形式為空間所吸納,向我們展示了時空相遇的另一種可能性:空間不再是時間的停滯和被動的“他者”,與之相反,看似重復、停滯的空間性恰恰突顯出線性前進的時間敘事的不可維持,構成對清末以來線性發展觀的基調的悖反。
二、 代際回旋: 進化的不可維持
張愛玲以日常生活替代革命并使之成為其文本永恒的時代主題,顯示了她對宏大歷史敘事的興致寥寥。相較宏大的歷史敘事,她更在意個體生命中的酸甜苦辣,也因此將反抗線性發展觀的決心最終落實到具體的個人身上。
在《評張愛玲》續篇中,胡蘭成稱張愛玲為一個“個人主義者”。解志熙敏銳地洞察到胡蘭成《評張愛玲》續篇是“胡蘭成為了幫助張愛玲應對迅雨的批評而臨時趕寫的”[11]141,指出其成文必然經過了與張愛玲的溝通,在很大程度上能夠代表她的心聲。由此可見,“個人主義”也構成了張愛玲針對迅雨提出的加強描寫人生斗爭一面的要求所做的辯解。換言之,張愛玲對革命進步的宏大敘事的反抗最終落實在了平凡安穩的人生百態上。具體到小說集《傳奇》,張愛玲反抗宏大敘事的態度突出表現在代際關系的回旋敘事之上。
代際是《傳奇》著意刻畫的主題之一,《金鎖記》《茉莉香片》《心經》等作品都從不同層面表露了張愛玲對代際主題的思考。這一方面與張愛玲偏愛探討人際關系的寫作趣味有關。1944年9月《傳奇》再版時采用了玉連環的封面,那些或勾連難解,或彼此獨立,或淡淡相挨的玉連環,在張愛玲看來正是書中人物相互關系的暗示。而代際關系正是一切人際關系之始,自然也是張愛玲關注的重點。另一方面,代際所反映的“下一代”問題恰是晚清與民國時期中國知識界的話語焦點。此時的中國飽受內憂外患的困擾,知識分子為尋求富國強兵之路,將目光投向西方世界。進步與發展的觀念作為西方現代性的核心與本質依據,隨著進化論的譯介傳入中國,也在中國語境下獲得了重新闡釋,并形成了“進化”內涵的單一向上限定及社會達爾文主義傾向這兩大特點。第一,“進化”內涵的單一向上限定。在西方思想界的語境中,“進化”一詞是過程性而非目的性的概念,既包括了向前的發展,也包含了向后的退化。然而,進化論傳入中國時,“進化”的內涵經過了本土化的選擇。如嚴復在翻譯赫胥黎的《進化論與倫理學》時,刪除了原文帶有退化之意的表述,“進化”的內涵被限定于其單一線性向上發展的向度。第二,社會達爾文主義傾向。社會達爾文主義指將社會視為與個體相似的有機體,遵從由低級生命形態向高級生命形態進化的觀念。處于現代轉型焦慮中的知識界普遍開始了在生物進化和社會進化之間構建話語聯系的嘗試。從嚴復以按語的形式在《天演論》譯本里為社會革新辯護,到魯迅“在進化的鏈條上,一切都是中間物”[12]卷一,302的表述,乃至當時的教育出版物,無不致力于建立種族進化與生物進化的共通性。而這種熱切的“進化”愿景往往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因此,文學作品甚至兒童刊物都以文字或圖片的形式頻繁地暗示兒童成長、發展和西化的可能。
在此情勢下,張愛玲也參與到了有關下一代話題的討論之中。1944年5月,《天地》月刊第7—8期合刊專設“生育問題特輯”,邀請蘇青、張愛玲、蘇復醫師等十位知識界人士就生育下一代的話題各抒己見。另九位作者或主張生育,或提倡節育,甚至懷有效仿西方“拿選擇人種與節制生育來達到科學化的改良人種,真的使人類留給下一代以優良的種氣”[13]49的目的,其中不難窺見種族進化與生物進化之間的話語勾連。然而,張愛玲的《造人》非但對時興的進化觀念置若罔聞,更是無情地拒斥了依靠繁衍獲得發展的可能:“多半他們長大成人之后也都是很平凡的,還不如我們這一代也說不定。”[14]36“平凡”和“不如我們這一代”即代表了張愛玲對下一代走向的兩種預測:停滯與退化。文末,她質問“憑什么我們要大量制造一批遲早要被淘汰的廢物”[14]37,更是將下一代物化,使繁衍完全偏離了遺傳與繼承的軌道,這無異于撕裂了物種進化與種族進化之間的結合點。
《傳奇》的結集與《造人》的刊發是在同一年,其中收錄的作品也充分展現了張愛玲對下一代的悲觀態度。《傳奇》呈現了停滯、倒退與發展三種代際傳承關系。在張愛玲筆下,代際之間的關系是回旋而非進化。回旋以重復而非發展為基礎,回旋的無方向性取代了進化的線性向上,暗含著向各個方向延伸的不同可能。
代際回旋最直接地表現為命運的重復。《金鎖記》多處呈現七巧與長安兩代人之間的糾葛。長安也曾有過與表哥無憂玩樂以及赴女中接受教育的美好時光,短暫的快樂卻在七巧的高壓管制下提前畫上了句號。盡管長安怨恨七巧的所作所為,但這種怨恨并沒有為她帶來《秋》中覺新式的覺醒,而只是在她重蹈母親命運的軌跡之際添加了一個悲哀的注腳。七巧的婚姻悲劇是在家人控制下造就的,隨著青春和愛情在畸形的婚姻中消磨殆盡,她自己也成了一個心理扭曲的母親。長安與世舫的戀情在七巧的管控中凋零,一如當初七巧的幸福所遭受的來自兄嫂的碾壓。長安與七巧命運的相似性是從何而來的呢?張愛玲似乎傾向于將答案引向遺傳。長安不僅遺傳了七巧的樣貌,還繼承了她的言行:“她不時的跟母親慪氣,可是她的言談舉止越來越像她母親了……誰都說她是活脫的一個七巧。”可悲的是,長安遺傳的恰是母親為人詬病的一面。初次約見世舫,長安擺架子不肯露面,蘭仙便說“安姐兒就跟她娘一樣的小家子氣,不上臺面”。七巧過世后,兩代人間命運的回旋卻并未隨之終結。正如謠言所傳,“七巧的女兒是不難解決她自己的問題的”,長安的命運沿著母親昔日的軌跡行駛,由最初向往愛情的少女變為麻木冷漠而幾無希冀的女人。《茉莉香片》中,聶介臣、聶傳慶這對父子之間的聯系也同樣令人唏噓。傳慶對介臣懼恨相織:之所以懼,是因為介臣將對碧落的憎恨轉移到傳慶身上,因此百般苛責傳慶,從而造成其孤僻壓抑的性格;之所以恨,是因為傳慶在潛意識里堅信是介臣的介入使自己失去了成為言子夜子嗣的機會。然而,傳慶卻悲哀地發現自己與父親不僅在五官外形上,甚至在動作姿態上都十分相似。就此,傳慶意識到自己再也無法逃離命運的魔咒,因為雖然“他有辦法可以躲避他父親,但是他自己是永遠寸步不離地跟在身邊的”。小說結尾處,傳慶在言子夜的女兒丹朱這位無辜者的身上發泄自己的痛苦,也印證了他不僅繼承了五官、動作等父親的外在特征,更陷入了“被害者—加害者”的循環。
當然,代際回旋的無方向性也為下一代提供了改變代際回旋、獲得前進的可能。但在張愛玲的言說中,一切試圖改變命運的努力都會回到原點。如《茉莉香片》中的傳慶在不幸的家庭環境中變得心理扭曲,將丹朱視為遺傳學上的仇敵。傳慶臆想著丹朱的死就能改變自己的命運,于是懷著“有了你,就沒有我。有了我,就沒有你”的想法狠狠地襲擊了丹朱。然而,傳慶并沒有改變臆想中的因果關系,因為“丹朱沒有死”,“隔兩天開學了,他還得在學校里見到她”,“他跑不了”。丹朱的存在提醒著傳慶他永遠只是禁錮于遺傳鏈條上的一環,任何逃離的舉動都將徒勞無功。《沉香屑·第二爐香》里的羅杰、《金鎖記》里的長安無不在掙扎后重蹈命運的回旋,遵從遺傳的預定軌跡。《心經》展示了子輩與父輩命運的糾纏所鑄成的悲劇。許小寒非但沒有追隨生命前行的腳步,反而陷溺在與父親的畸戀中難以自拔,不僅顛覆了自己的命運,也將整個家庭的命運引入歧途。
較之變異和進化問題,遺傳問題恰恰是達爾文的《物種起源》所沒有解答的難題。《物種起源》在遺傳問題上沿用了拉馬克的“獲得性遺傳”之說,即生物能夠通過主體性的努力改變遺傳性狀。直到孟德爾、魏斯曼時期新達爾文主義的出現,才宣告了“獲得性遺傳”在遺傳學上的漏洞,遺傳的先天性進而得到認可。雖然新達爾文主義在20世紀40年代的西方生物學界已經獲得共識,但由于中國大眾出版業相對滯后,主體能通過努力改變遺傳性狀的觀點仍是當時進化論出版物的主旋律。出于救國圖強的需要,知識界又將它引申到種族層面,即人類可以通過主體性的進化改變既定的命運。在宣揚進化話語的大環境下,張愛玲對主體能動性的否定無異于對盛極一時的進化論的公然挑戰。
張愛玲以代際回旋解構了進化論神話,從人的角度出發,動搖了向上發展的種族進化觀的根基,折射了她的反線性發展觀立場。這極為符合張愛玲在《等》與《再版的話》中對生命的理解:“生命自顧自走過去了”,“它有它的圖案,我們惟有臨摹”。“自顧自”與“臨摹”揭示了我們對生命進程的無能為力,下一代作為改變種族命運的工具性作用也就此消解。
三、 色彩回旋: 兩個世界與存在的價值判斷
張愛玲蒼涼的創作風格原本就為她帶來了諸如“徹底的悲觀主義者”[15]313之類的評價,隨著張愛玲研究中反線性發展維度的挖掘,這一評價更是被不斷強化。例如李歐梵體察到張愛玲“絕不是一個‘進步主義’的信徒,以為歷史是直線前進的,而且‘明天會更好’”[7]129-130,進而推斷出她人生哲學的悲觀基調。王德威也從《對照記》的回旋主題中看到她“似為自己死亡,預作宣傳”,認為體現出其“重復的陷溺的生命觀”[3]25-26。
上述研究者的論說鮮明地揭示了張愛玲有別于五四文學的反線性發展觀,但也給我們留下了亟待解決的問題:反線性發展觀是回旋敘事的終點嗎?當線性發展的高樓在回旋敘事的沖擊下分崩離析之后,在其廢墟之上能否重新綻放繁花?
答案其實就隱藏在張愛玲文學世界的色彩回旋中。受母親的影響,張愛玲對色彩的興趣經歷了由紅色系到藍綠色系的轉向。在母親角色缺席的孩提時期,因為紅色帶給她“溫暖而親近”[16]86的體驗,所以她喜愛紅色,還吵著要穿她認為最俏皮的小紅襖去見久別重逢的母親,并自述“我和弟弟的臥室墻壁就是那沒有距離的橙紅色,是我選擇的,而且我畫小人也喜歡給畫上紅的墻”[16]86。而母親留洋歸來后,張愛玲的色彩偏好逐漸由紅色系轉向藍綠色系。張愛玲親自將《傳奇》初版的封面設計為“整個一色的孔雀藍”,“以后才聽見我姑姑說我母親從前也喜歡這顏色,衣服全是或深或淺的藍綠色……遺傳就是這樣神秘飄忽”[17]6。
在張愛玲的言說中,“對照便是紅與綠”[16]72,二者承載著截然相反的意味。這對色彩詞的交鋒在《茉莉香片》中達到頂峰。《茉莉香片》中,從小父愛缺席的男孩聶傳慶得知自己的母親馮碧落本可以嫁給言子夜之后,對言子夜的女兒言丹朱產生了既愛慕又痛恨的矛盾感情。碧落與丹朱這兩位女性角色的命名絕非信筆之舉,而是色彩回旋的集中體現。
根據《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馮碧落名中的“碧”有“青綠色”之義[18]73。提及碧落時,張愛玲又用“青郁郁的眼與眉”形容其外貌。“青郁郁”在此不僅是描述深青的色彩詞,“郁郁”二字更影射了憂悶愁苦的郁結之情。碧落出身于守舊的馮家,渴望上學而不能,同子夜的戀愛也受到家庭阻攔。當子夜決心出國留學之時,她亦缺乏比翼雙飛的勇氣,因而錯過子夜,嫁入聶家郁郁而終。借助碧落生命軌跡的具象化表述,《茉莉香片》對綠色的回旋體現出有別于自由啟蒙的現代化吁求的守舊傾向。綠色回旋與守舊意涵的聯結也體現在《傳奇》收錄的其他作品之中,如《沉香屑·第一爐香》就用綠色來形容梁太太的房子猶如古代的皇陵。時值民國中期,帝制早已廢除,而梁太太卻仍然在自己綠色的皇陵中做著舊夢,這又何嘗不是對崇尚進步發展的時代潮流的逆反?
而言丹朱名中的“丹”“朱”二字均含“紅色”之義[18]252,1696。紅色也的確是丹朱帶給讀者的第一印象,“像美國漫畫里的紅印度小孩。滾圓的臉,曬成了赤金色”。紅色往往同激蕩、奮進的意涵相對應,正如丹朱對于傳慶的意義那般:“你不單是一個愛人,你是一個創造者,一個父親,一個母親,一個新的環境,新的天地。你是過去與未來。你是神”。丹朱不但是子夜的血脈,而且活潑大方,主動接近并試圖改變在自我封閉的世界中顯得格外孤寂的傳慶。傳慶對深藏在自己體內的聶介臣的血脈深惡痛絕,丹朱因而成為他卑怯、畏縮的現實生活里積極、樂觀、上進的幻想性寄托。
碧落之綠是退縮、封閉的守舊之俗的代表,而丹朱之紅則象征了積極進取、崇尚改變的新派作風。然而,丹朱試圖改造傳慶的計劃并未如愿以償,反而以傳慶對她的打罵告終,其中便已顯示出守舊性的綠對于進步性的紅的壓制地位。如予細究,綠與后退、守舊意涵的聯結在《傳奇》中甚至呈現泛化的趨向。換而言之,綠有諸多“衍生色”,雖然它們在視覺上并不等同于綠色,但從不同側面表現出張愛玲的色彩回旋對守舊意涵的倚重。例如藍色作為綠色的相近色,在《花凋》中寓示著川嫦年輕卻封閉的人生。再如白色雖不是藍綠的鄰近色,但在張愛玲筆下,白與藍綠之間往往存在連接與轉換,“青白色”“白得發藍”等表述屢見不鮮。
由此可見,《傳奇》中的色彩物語背后,離不開兩大色系的糾纏牽絆。藍綠色系對紅色系的壓制所傳達的更是另一種以超越現實的“不自覺的記憶”構建幻景并代替現實主義潮流的書寫方式。王德威曾直言張愛玲以兩種語言四次書寫同一題材表現了一種反寫實主義立場,“回歸過去,‘重復’自己,一再拆解記憶,重新拼湊”[3]9-10。他的落腳點在于張愛玲以認同虛擬寫實的方式質疑我們信以為真的世界。其實,我們還可以進一步看到張愛玲的質疑背后意欲確立的信仰。
在藍綠色系與紅色系的意義趨向統攝之下,張愛玲筆下的人物形成了兩種類型,也代表了兩種存在的方式:存在于現實中與存在于記憶里。區別于前者的開放發展,存在于記憶里的人生是封閉自足的。藍綠色系的人物,如《花凋》中的川嫦,體現了以記憶構成的存在方式。而紅色系的人物,如《茉莉香片》中的丹朱,則代表了以現實構成的存在方式。
張愛玲通過以上兩種存在方式的并存消解了真假判斷的重要性,代之以價值判斷,即根據何種存在方式對具體對象而言更有價值來歸屬存在方式。按照這一邏輯,“有價值的生活”不一定存在于現實中,而是依賴于特定對象對價值的理解。
《花凋》中的川嫦因病困守床榻,感到“她自己一寸一寸地死去了,這可愛的世界也一寸一寸死去了”。“凡是她目光所及,手指所觸的,立即死去。余美增穿著嬌艷的衣服,泉娟新近置了一房新家具,可是這對于川嫦失去了意義。她不存在,這些也就不存在。”外面的現實世界逐漸棄她而去,以致她只能依靠昔日的照片維系記憶世界殘存的影像。門外的現實世界之于她,是飛漲的物價,是缺乏憐憫的世人,是茫然而陌生;她之于門外的現實世界,則“是個拖累。對于整個的世界,她是個拖累”。由此可見,川嫦真正能夠立身的不是門外的現實世界,而是她在病榻上靠記憶維系著的世界。唯有在這個記憶構建的圖景中,川嫦才感受到了自己的價值。而在現實世界里,“她不存在,這些也就不存在”。
從張愛玲對川嫦等的描摹,可見在《傳奇》的文本世界中,價值判斷代替真假判斷成為存在的依據。一方面,由藍綠色系回旋引領的人物在記憶世界中獲得了價值肯定:傳慶沉溺于母親與子夜的過去中,幻想自己若是二人的孩子,必將在各方面遠勝現實中的自己;煙鸝在自己與現實世界之間筑造起一層白的膜,很長一段時間中,她都在膜保護的范圍內蝸行,忠心掩飾振保的放浪。他們如川嫦那般在自己的思維宮殿中找到了比在現實世界中更大的寬慰,因而在此駐足。另一方面,紅色系主導下的人物傾向于在現實世界中追尋價值。丹朱作為積極、進取與勇敢的化身,既在現實世界中游刃有余甚至萬眾矚目,又成為傳慶記憶世界里的假想敵。與身處藍綠色系縈繞下的川嫦、傳慶等人以記憶性書寫為主的心理描寫不同,紅色系主導下等人物的心理活動是緊密圍繞現實世界展開的。《茉莉香片》里唯一一處有關丹朱的心理描寫是在傳慶向丹朱吐露了自己的痛苦之后,丹朱以為傳慶愛上了她,進而內心經歷了驚訝、原諒、滿足的變化。但丹朱的心路完全圍繞著兩人的現實處境展開,最終也回歸于如何處理兩人關系的現實問題。這是因為,在現實世界游刃有余的紅色系人物已不需要借助記憶世界為自己的價值增色。
有研究者質疑張愛玲文學世界的真實性,認為《金鎖記》之后,“出于政治偏見,張愛玲滿足于浮光掠影,道聽途說,不能深入地描寫真實的生活”[19]369。此處的“真實”無疑單純指涉現實世界的真實。而事實上,出于對個體命運的關心,張愛玲將“何為真實”轉化為了“何為存在”這個命題。在色彩回旋的映照下,存在不再是一個真假判斷,而是基于個人性的價值判斷。線性發展觀在此維度上走向破碎,這是因為線性發展觀既強調現實世界層面的發展,又將“新”作為“好”的標準,而張愛玲關于存在的價值判斷恰與這兩個原則針鋒相對。如若以價值判斷來衡量存在,那么籠罩在現實世界陰影之下的記憶世界便會浮出水面,形成與前者勢均力敵的存在;以“新”為“好”的信條也將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以自我價值確認為標準的極具個人性的好壞判斷。由此,張愛玲不僅從時間觀念出發解構線性發展觀,還將反線性發展觀由宏觀的時間觀落實到生命個體中,宣揚了個人的價值判斷這一極具個體特殊性的標準。
四、 結 語
張愛玲《傳奇》的回旋敘事對線性發展觀的解構并非僅停留于同一題材的反復書寫上,而是在意象回旋、代際回旋和色彩回旋諸方面形成了體系性的建構。意象回旋將時間體驗空間化,既支撐起了敘事空間,也構建起了時空之間的橋梁。它向讀者展示了時間何以背離進化線索,又何以呈現類似空間的荒蕪,并據此揭示了線性發展的時間敘事和文明觀是難以維持的。與宏大歷史敘事相比,張愛玲更關注歷史長河中的微小個體,將反抗線性發展觀的行為落實到她對個體生命的體察中。因此,《傳奇》的代際回旋由時間層面的反線性發展轉向生物學層面的反進化敘事,劍指盛極一時的進化論。完成了解構線性發展觀之后,張愛玲再次展示了她的野心:反線性發展觀不過是她通向個體性的橋梁,而非最終目的。她從藍綠色系與紅色系的回旋相生出發,發現存在的根基并非真假判斷,而是極具個人性的價值判斷。
在張愛玲的《傳奇》中,無論采用的是哪種形式的回旋敘事,最終都將矛頭指向了進化論孕育下在中國扎根、萌芽的線性發展觀。在清末到民國救國存亡的大環境下,進化與發展相捆綁,從生物學滲透到各個領域,不僅指涉政治、經濟、教育等的進步,更代表了“一種思考的方式,一種敘事的方式,一種嘗試面對急劇歷史變革的方式”[20]3。在線性發展的進步史觀的框架中,重復帶來的迂回不是開頭,而是結尾,重復因此成為線性發展觀所要極力避免的情形。與之相反,回旋敘事將重復變成了開端,它帶來的是方向的不確定和無盡的可能性。正如王德威所言,“革命可能會對反動的目的有所幫助,回旋反而可能在無目的性的情況下引起真正的改變”[21]33。在回旋敘事的框架中,重復不只是現象的模仿者,也可能是意義的創造者,更是線性發展觀的反叛者。
[1] 李歐梵: 《未完成的現代性》,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L.Lee,IncompleteModernity,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2] 黃子平: 《講評》,見劉紹銘、梁秉鈞、許子東編: 《再讀張愛玲》,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年,第66-67頁。[Huang Ziping,″Comments,″ in Liu Shaoming, Liang Bingjun & Xu Zidong(eds.),RereadingEileenChang, Jinan: Shandong Pictorial Publishing House, 2004, pp.66-67.]
[3] 王德威: 《落地的麥子不死》,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年。[D.Wang,AGrainofWheatFallingintotheEarthDoesNotDie, Jinan: Shandong Pictorial Publishing House, 2004.]
[4] D.Wang,″MadameWhite,theBookofChange, and Eileen Chang: On a Poetics of Involution and Derivation,″ in K.Louie(ed.),EileenChang:RomancingLanguages,CulturesandGenre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215-241.
[5] 汪暉: 《關于現代性問題答問》,《天涯》1999年第1期,第18-34頁。[Wang Hui,″Answers to Questions of Modernity,″Frontiers, No.1(1999), pp.18-34.]
[6]
[美]布賴恩·理查森: 《超越情節詩學:敘事進程的其他形式及〈尤利西斯〉中的多軌跡進展探索》,見[美]詹姆斯·費倫、彼得·拉比諾維茨編: 《當代敘事理論指南》,申丹、馬海良、寧一中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73-189頁。[B.Richardson,″Beyond the Poetics of Plot: Alternative Forms of Narrative Progression and the Multiple Trajectories ofUlysses,″ in J.Phelan & P.Rabinowitz(eds.),ACompaniontoNarrativeTheory, trans. by Shen Dan, Ma Hailiang & Ning Yizhong et al.,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173-189.]
[7] 李歐梵: 《李歐梵論中國現代文學》,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L.Lee,LeoLee’sDiscussiononModernChineseLiterature, Shanghai: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8.]
[8] 解志熙: 《“反傳奇的傳奇”及其他——論張愛玲敘事藝術的成就與限度》,《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9年第1期,第23-37頁。[Xie Zhixi,″′The Legend Against Legend′ and Other Things: The Achievements and Limitations of Eileen Chang’s Narrative Arts,″ModernChineseLiteratureStudies, No.1(2009), pp.23-37.]
[9]
[德]黑格爾: 《歷史哲學》,王造時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G.Hegel,ThePhilosophyofHistory, trans. by Wang Zaoshi,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2001.]
[10] 周寧: 《在西方現代性中發現中國歷史》,《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5期,第5-14頁。[Zhou Ning,″Searching Chinese History in Western Modernity,″JournalofXiamenUniversity(Arts&SocialSciences), No.5(2005), pp.5-14.]
[11] 解志熙: 《走向妥協的人與文——張愛玲在抗戰末期的文學行為分析》,《文學評論》2009年第2期,第137-149頁。[Xie Zhixi,″Tendency to Compromise: Analysis on Eileen Chang’s Literary Behaviors at the Later Stage of Anti-Japanese War,″LiteraryReview, No.2(2009), pp.137-149.]
[12] 魯迅: 《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Lu Xun,CompleteWorkofLuXun,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5.]
[13] 蘇復醫師: 《節育的理論與方法》,《天地》1944年第7-8期合刊,第49-53頁。[Doctor Su Fu,″Theory and Method of Birth Control,″Tiandi, No.7-8(1944), pp.49-53.]
[14] 張愛玲: 《造人》,《天地》1944年第7-8期合刊,第36-37頁。[E.Chang,″Making People,″Tiandi, No.7-8(1944), pp.36-37.]
[15] 夏志清: 《中國現代小說史》,劉紹銘、李歐梵、林耀福等譯,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5年。[C.T.Hsia,AHistoryofModernChineseFiction, trans. by S.M.Lau, L.Lee & Lin Yaofu et al.,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5.]
[16] 張愛玲: 《自己的文章》,北京:京華出版社,2005年。[E.Chang,MyOwnArticles, Beijing: Jingwah Press, 2005.]
[17] 張愛玲: 《對照記》,哈爾濱:哈爾濱出版社,2003年。[E.Chang,Reflections:WordsandPictures, Harbin: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2003.]
[18]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 《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Dictionary Editing Room of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ed.),ModernChineseDictionary(7thVersio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
[19] 唐弢: 《西方影響與民族風格》,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Tang Tao,WesternInfluenceandNationalStyle,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9.]
[20] A.Jones,DevelopmentalFairyTales:EvolutionaryThinkingandModernChineseCultu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21] D.Wang,Fin-de-SiecleSplendor:RepressedModernitiesofLateQingFiction, 1849-1911,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InvolutionaryNarrativeofChuanqiandEileenChang’sNonlinearViewpointonDevelopment
Huang Qing Yang Yan
(Department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ZhejiangUniversity,Hangzhou310028,China)
As an effort to resist the adoption of a linear viewpoint on development, research on Eileen Chang’s involutionary narrative shows potential for breaking the linear and progressive narrative conventions regarding history. In this context, the definition of involutionary narrative, the expressions and objectives of involutionary narrative in Chang’s works, and the constructive contribution of involutionary narrative besides a nonlinear viewpoint on development serve as crucial issues concerning the research on Chang’s involutionary narrative. The connotation of an involutionary narrative is twofold. First, from the aspect of the text, involutionary narrative denotes the repetition of certain elements within works. Second, in the aspect of culture, involutionary narrative indicates an introverted tendency, a spirit opposite to a linear viewpoint on development.Chuanqiis a famous short story and novella collection by Eileen Chang. It conveys Chang’s resistance to a linear viewpoint on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involution of images, generations and colors, thereby confirming the systematic existence of an involutionary narrative in her works. The three aspects outlined below are related to the involutionary narrative inChuanqi.
First,Chuanqiuses the involution of images to deal with the time issue and spatializes the experience of time. On the one hand, in the aspect of narrative time, Chang materializes and even spatializes time by the involution of time, creating the closed and self-contained structure of works. For example, the involution of the moon inTheGoldenCangueserves as the controller of the narrative speed as well as the producer of the narrative process. On the other hand, involutionary narrative links time with space and expresses the era theme in certain milieu. For instance, the involution of a wall inLoveinaFallenCitynot only surpasses the role of the stagnant ″other,″ but also reflects the unsustainability of the linear viewpoint on cultural development, thereby considering the era theme of her works as ordinary life instead of revolution.
Second, Chang focuses on specific individuals by resisting the linear viewpoint on development with the aid of the involution of generations. The involution of generations inChuanqiis characterized by nondirectional involution instead of optimistically linear evolution and deconstructs the myth of evolutio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ividuals. On the one hand, the repetition of fate is the most common expression of generations. The involution of generations is shown inTheGoldenCangue,AloeswoodIncense:TheFirstBrazierandTheBookofHeart. InTheGoldenCangue, Chang’an inherits not only her mother Qiqiao’s appearance and manner, but also her fate. On the other hand, although the possibility of development is heralded by the nondirectional involution of generations, any effort to change fate proves invalid in Chang’s works. InJasmineTea, Chuanqing attacks Danzhu in order to change his fate. Unfortunately, he finds himself trapped in the chain of heredity forever.
Third, the nonlinear viewpoint on development is the bridge to individual values rather than the destination of an involutionary narrative. The involution of red tones is intertwined with the involution of blue and green tones inChuanqi, forming two opposite meanings and existence genres. The former is often associated with a regressive action as well as characters existing in recollection, whereas the latter points to positive and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as well as characters existing in reality. The involution of red tones is overtly overwhelmed by the involution of blue and green tones inChuanqi, which is reflected inJasmineTeaandAWitheredFlower. Danzhu, a character of the red tones inJasmineTea, fails to transform Chuanqing, a character of the blue and green tones. Thus it can be seen that Chang not only resists a linear viewpoint on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ime, but also relies on specific individuals to express her resistance, thereby turning the basis of being from a true/false judgment into a judgment on independent volition and value.

Eileen Chang;Chuanqi; involutionary narrative; nonlinear viewpoint on development; involution of image; involution of generation; involution of color
10.3785/j.issn.1008-942X.CN33-6000/C.2017.02.091
2017-02-09
[本刊網址·在線雜志] http://www.zjujournals.com/soc
[在線優先出版日期] 2017-08-18 [網絡連續型出版物號] CN33-6000/C
1.黃擎(http://orcid.org/0000-0002-6212-7790),女,浙江大學人文學院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文學博士,主要從事文學批評、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 2.楊艷(http://orcid.org/0000-0002-3402-4938),女,浙江大學人文學院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敘事學、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