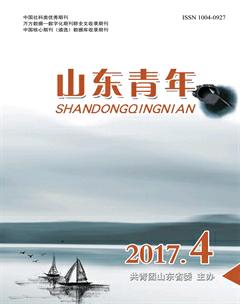環境公益訴訟原告資格研究
麻寶寶?オ?
摘要:
原告資格問題作為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的核心,打破了傳統“訴之利益”理論,在訴權理論、環境權理論、公共信托理論、私人檢察長理論支撐下,辯證分析公民個人、檢察機關、環保組織作為原告主體資格的合理與不足之處,并從完善激勵機制、規范起訴順位、限制起訴資格等方面規范環境公益訴訟制度,旨在解決實踐中無人起訴、起訴難問題,從而促進環境公益訴訟與我國實情相適應。
關鍵詞:環境公益訴訟;原告資格;公民;檢察機關;環保組織
一、環境公益訴訟概述
環境公益訴訟是指有權國家機關、社會組織或個人為了環境公共利益而針對環境破壞、污染行為提起的一種公益訴訟,訴訟請求一般包括停止侵害、恢復原狀、損害賠償等。環境公益訴訟制度是針對“環境損害”而確立的制度,明顯帶有區別于私益訴訟的特征:
(一)訴訟主體的廣泛性
環境公益訴訟的理論與實踐難題與重心是原告資格,傳統訴訟受訴之利益影響,原告須與被訴法律行為有法律上直接利害關系,而環境公益訴訟由于其環境侵害對象的特殊性、環境影響范圍的廣泛性,導致起訴主體范圍不再局限于傳統訴之利益理論,從而能夠避免環境侵害行為發生后無人起訴的窘境。當發生環境損害時,有權國家機關、社會組織、個人都有權為了公共環境利益以環境公益訴訟原告身份起訴。環境公益訴訟突破了原有權利框架,賦予廣大公民、社會組織、檢察機關以訴訟起訴權。在原告主體資格范圍上,突破了“直接利害關系人”,理論限制,主體范圍更廣。
(二)訴訟目的與訴訟對象的特殊性
環境公益訴訟基于自身公益性,其起訴目的當然須為社會公共利益,是為保護公共環境不受損害。區別公共與私人的關鍵在于是否站在公共利益的立場上,是否主張對個人的損害賠償。為了環境公益訴訟濫訴現象,有必要對訴訟利益進一步限制,訴訟主體不得通過訴訟來謀求私利,即不得假借訴訟謀取金錢利益。
在實踐中,提起環境公益訴訟,訴由一般是基于對環境的損害或者對人的損害。這兩種損害一般表現為兩種情形:一種是現行侵權行為法已經明確規定的損害——財產損害、人身損害、精神損害,即“對人的損害”;另一種是現行侵權行為法尚未明確規定的損害——環境污染、生態破壞,即對“環境的損害”。[1]如果將訴由限于對人的損害,涉及的是私人利益,會產生所謂的“正外部性”或“反射利益”,但如果某一個環境污染行為并沒有產生具體侵害的結果,會導致案件無人起訴,待“對人的損害”結果出現為時已晚。環境公益訴訟應以預防性為原則,不應單獨強調“對人的損害”這一片面結果。但若將訴由限于對環境的損害,原告主體范圍相應放寬,會出現“搭訴訟便車”現象。
二、公民個人作為原告主體的探究
(一)公民作為原告主體的合理性
環境權理論——公民有權起訴的理論支撐。環境權是一種概括性權利,是指公民享有在不受污染和破壞的環境下生活和利用資源的權利,具體包括清潔空氣權、清潔水權、風景權、通風權等。作為世界性環境危機和環境保護運動的產物,在《人類環境宣言》已對環境權有所體現。實踐中有將環境權以基本權利的形式在憲法中予以確認,如巴西。環境權是一項特殊權利,將其包含于所有權會與所有權所要求的可支配性相沖突,因所有權是一種絕對權,法律主體無權對他人享有的物權主張環境質量權利。如果將其看成一種人格權,對通風、采光等舒適性無能為力;從相鄰權角度來講,作為一種法定權利,受到相鄰不動產物權及必要方便為前提,對海洋、大氣等污染愛莫能助;從地役權制度上看,作為一種約定權利,使用范圍有限,以雙方存在土地權利且大致毗鄰為前提,且需支付對價,對本身弱勢的公民來講更是平添阻力。侵權責任制度也有其不足,該制度同時要求權利與損害,此依賴性和滯后性與環境保護的預防性相悖。在現行法律框架下,尚無制度可以全面覆蓋環境問題,因此有必要創設一個獨立的權利—環境權。目前國際上很多國家將其具體化,如美國以私人檢察總長為理論基礎而創設的公民訴訟制度,并為防止公民濫訴而設置60天通知義務、窮盡救濟原則。[2]公民被賦予環境權后因享有法定權利而成為直接利害關系人,當然有權具備起訴資格。在環境權理論的支持下,凡涉及環境污染或生態破壞,有關個人都有權作為原告提起環境公益訴訟。
(二)公民作為原告主體資格的限制
1.公民起訴會受到專業技術限制
公民作為弱勢群體,技術專業性不強,針對成因復雜,比如跨地區的工業污染、尾氣污染,以及霧霾等環境污染問題,易受到起訴對象不明困擾,會產生“欲而不能”的起訴窘境。在案件調查取證過程中,基于環境公益案件的復雜性,對證據采集、損害事實的認定、損害結果的認定等環節均需專業機構來實行,而我國此類機構欠缺,從客觀方面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公民的起訴。
2.在訴訟期間會面臨訴訟費用承擔及濫訴現象。
環境公益訴訟案件涉及公共利益,案情復雜,案件一般較大,訴訟成本高,整個案件下來原告通常花費巨大,很多普通公眾缺乏資金而無力提起訴訟。公民作為原告極大地擴大了原告的資格范圍,這與為防止權利濫用而設的“直接利害關系人”的當事人適格理論相矛盾,隨之帶來的可能是當事人濫訴現象,公民可能出于私怨或為謀求不正當利益而提起訴訟,一方面加大了法院的工作量,降低司法效率,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對企業帶來困擾,不利于市場經濟的發展。
3.因法律上的欠缺公民起訴缺乏有力的法律支持
新環保法賦予符合條件的社會組織環境公益訴訟起訴權,換句話說從法律層面否定公民原告資格,公民提起環境公訴會遇到法院不予受理的決定,致使公民因缺乏法律依據而無法提起公訴。
三、檢察機關作為環境公益訴訟原告資格探究
(一)檢察機關作為起訴主體的實踐
檢察機關作為我國監督機關,具有公訴職能,負有保護國家集體利益職責。當存有訴訟阻礙情形,人民檢察院為維護國家、公共利益和避免非法行為為落腳點,以公力干預的法律措施提起公益訴訟,該當認定符合訴之利益。自1972年檢察院提起環境公益訴訟后目前全國已有多起,如2008年貴州省貴陽市清鎮市人民檢察院提起的環境公益訴訟案件,2017年山東煙臺檢察院對鮑德萍、玉常山污染環境一案提起民事公益訴訟。在這里我們以環境行政公益訴訟案件展開研究。endprint
2016年12月16日,山東省慶云縣檢察院以縣環保局監管不合法,基于全國人大常委授權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訴訟。檢察院在處理某污水處理廠廠長涉嫌環境犯罪時,查明此廠是在環保設施竣工驗收尚未結束前從事違法作業,非法排放污水導致環境污染,黨委政府責成環保部門嚴格履行監管職能。檢察機關查明縣環保部門雖已作出行政處罰,但仍在監管上存有違法行為,致使國家、社會公共利益遭受嚴重損害,遂經嚴格落實訴前程序,依法對縣環保部門不依法履行職責,提起行政公益訴訟。慶云縣檢察院是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授權展開的試點工作,盡管未提起環境民事公益訴訟,但對于檢察院提起環境公益訴訟的實踐史上是一次偉大的實踐。在公民無力起訴、環保機關怠于履行職責情況下,有“必須要設定一個能夠代表公共利益,而且擁有足夠有效法律手段和權威的主體代表國家提起訴訟、參與訴訟。[3]檢察院通過此次成功的訴訟實踐,進一步夯實了檢察機關提起環境公益訴訟的根基。
(二)檢察機關作為原告分析
檢察機關享有公共信托理論的支持,作為國家代表機關,當然有權在國家環境資源遭受損害時行使環境訴權以保全公共財產。檢察機關身為國家監督機關的身份有利于其獨立、公正行使訴權;且檢察機關內部享有完善的業務部門和法律知識豐富的法律人才,方便取證,符合對審判效率追求;此外,檢察機關的公訴職能使得其具有權威與威懾力,可起到警示環境污染者作用,預防環境污染。不可否認,檢察機關作為原告存有加重業務負擔弊端,但隨著反貪職能從檢察機關的調離,一定程度可減輕該弊端;檢察機關的該項權力一定程度上與環保機構存在重疊,可能導致權力推諉,降低環保機構責任;與此同時,檢察機關接入訴訟,可能導致平等的民事關系被打破,使被告處于一種弱勢地位。隨著法律的不斷完善,法律實踐的不斷豐富,其在環境保護方面的優勢更加突出。
四、環保組織作為原告主體資格的探析
(一)環保組織優勢
環保組織身為社會團體,專業性、針對性突出,利于環境損害的調查取證、災害評估、環境評價、損失統計,且一般有相應資金來源,方便承擔相應訴訟費用;基于我國法律對環保社會組織的非營利性要求,能有效滿足環境公益訴訟有關保護公共環境利益的訴訟目的;與行政機關相比,環保組織更易針對行政機關不作為提起的環境行政公益訴訟,目前行政體制下行政機關不輕易為“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的行為。
(二)環保組織作為原告資格在我國新環保法上的體現
新環保法在賦予環保組織權利的同時也對其做了嚴格限定:在設立上,應滿足在設區的市級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門登記這一要件;在行為上,要求專門從事環境保護公益活動連續五年以上且無違法記錄。目前我國符合前款規定的社會組織數量較少,與頻發的環境損害現象相矛盾,因此應適當放寬條件,使更多符合要求的社會組織加入進來,如對于有一定規模、專業水平高、組成人員素質高的社會組織可以將連續五年調整為連續三年。也可將社會組織等級化,每一級別設計對應條件。為了鼓勵環保組織提起訴訟,國家應給予政策優惠,將訴訟費用與社會保障機制相結合,可通過案件勝訴后政府補助形式或采取訴訟成本有利于原告原則等措施。
五、針對原告資格問題的建議
(一)應建立完善的激勵機制
完善的訴訟激勵機制能最大程度帶動主體參與到環境公益訴訟中。在立法層面應賦予檢察機關、公民一定程度的環境公益起訴權,彌補法律規定的空白,保障權利的行使有法可依;在訴訟費用層面,應給予起訴主體一定財政支持以達到鼓勵起訴目的,改革律師費用制度,可借鑒美國的司法實踐規定案件勝訴由被告承擔律師費用;[4]基于任何人都不得從其違法行為中獲利標準,應提高環境污染行為的違法成本,改變“違法利潤大,處罰成本小”現狀,給予違法者一定程度的法律威懾力。
(二)規范起訴順位
因公民、檢察機關、環保組織等多類主體就提起環境公益訴訟均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因此有必要規范其起訴順位。環境權理論下,公民和環保組織因成為直接利害關系人很自然地被賦予了起訴第一順位;環保機關為第二順位,當環境權人未在法定合理期間內起訴而影響到環境公益的,環保機關有權提起訴訟。存在環境保護不作為或濫用權力行為時,環保機關起訴具有很大程度的不現實性,故該順位的設置應以環保機關合法行使權力為前提;檢察機關為第三順位,在公民、環保機關經催促仍怠于行使權利時有權為了國家、社會公益提起訴訟,但應以提起檢察建議為前提。自然資源所有權基礎下,環保機關作為國家所有權代表人而享有第一起訴順位,檢察機關為第二順位,公民、環保組織為第三順位。制度設計上應建立與起訴順位相配套機制,美國立法規定了公民或社會組織在起訴前應提前60天通知污染者或主管機關,可借鑒美國建立訴前通知制度,同時基于訴訟效率考量設置45天訴前通知義務。
(三)對公民、檢察機關、環保組織起訴資格的限制
公民雖不受“直接利害關系”約束,但并非意味著任何公民可以無節制地提起訴訟,應與案件有“間接利害關系”,且遭受的事實損害具有現實性或高度危險性。[5]檢察機關因其身份上的特殊性,為避免使訴訟陷入不平等狀態應在起訴順位上規范其權力,即在前起訴順位主體怠于起訴時,為公共環境利益提起訴訟;同時為協調檢察機關內部部門職權關系亦提升案件處理效率,建議應設立專門環境公益訴訟部門,引進環境方面專業人才,準確把握起訴的平衡點。
結語
環境公益訴訟制度在我國呈現不斷完善趨勢。立法層面已有關于檢察機關提起環境公益訴訟的試點決定,但仍未以法律形式給予公民、檢察機關起訴權。在理論與實踐不斷完善下,必會不斷促進我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的完善,切實保障社會公共環境利益。
[參考文獻]
[1]呂忠梅.環境公益訴訟辨析[J].法商研究,2008,(06):131-137.
[2]張鋒.我國公民個人提起環境公益訴訟的法律制度構建[J].法學論壇,2015, (06):71-77.
[3]江偉.略論檢察監督權在民事訴訟中的行使[J].人民檢察,2005,(18):5-8.
[4]曹明德.中美環境公益訴訟比較研究[J].比較法研究,2015,(04):67-77.
[5]李傳軒.環境訴訟原告資格的擴展及其合理邊界[J].法學論壇,2010,(04):82-87.
(作者單位:山東師范大學法學院,山東 濟南 250358)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