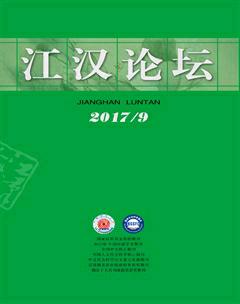文學闡釋的疆域與文本接受的向度
摘要:張江教授針對文學本體研究的弱化與文學闡釋的無邊化提出強制闡釋論,固然抓住了當今文學闡釋的一些亂象,一針見血地指出了一些批評者脫離文本實際所滋生的教條化、僵化的癥候,但其所提出的“場外征用”、“抹煞文學理論及批評的本體特征,導引文論偏離文學”,只是一種可能性,另外的可能性或許是給文學闡釋帶來新的路徑,帶來新的啟迪,甚至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刷新我們的認知。在現代長篇小說接受研究上,“征用”經濟學理論與存在主義理論就可以解決并刷新學界有關《種谷記》《高干大》及《圍城》等的藝術問題,因此不能一概而論。
關鍵詞:強制闡釋論;場外征用;經濟學;存在主義;《種谷記》;《高干大》;《圍城》
中圖分類號:I20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54X(2017)09-0088-05
文學闡釋是否應恪守文學的疆域,遵循文學本體的法則,許久以來似乎是一個無需辯駁的問題。但隨著20世紀西方現代文論的強勢涌入,特別是近幾十年來經學院派的傳承與實踐,運用精神分析理論、符號學、現象學、知識考古學、接受理論、結構主義、俄國形式主義、存在主義、女權主義、后現代主義等西方文史哲學觀念闡釋文學,已成為許多學人刷新存在感的自覺追求。不僅如此,自然科學中的一些范疇如控制論、概率論、統計學等也被嫁接過來,生成文學研究的新范式,文學闡釋也由之前單一的批評樣式擴展為多樣的、跨專業的、融交叉學科為一體的多元共生的批評格局。這無疑極大地拓展了文學研究的新疆域,豐富了人們的認知結構,當然,也帶來了另一個令人焦慮的問題,即:文學本體研究的弱化與文學闡釋的無邊化,特別是當一些學人越來越熱衷于簡單地“拿來”西方現代文論并生吞活剝、生搬硬套時,這種因過度闡釋而偏離文學本體甚至跨越文本所應有的接受向度以至以訛傳訛、惡性循環的現象更令人憂慮。有學者將之總結為“強制闡釋論”,并將這一特點概括為場外征用、主觀預設、非邏輯證明和混亂的認識路徑四種模式。① 應該說,這一批評確實抓住了當今文學闡釋的一些亂象,一針見血地指出了一些批評者脫離文本實際所滋生的教條化、僵化的癥候,對我們構建契合文學實踐的新理論體系以回歸文學本體批評,防止錯位闡釋,過度闡釋,有十分重要的警醒作用。但是,這也由之引發了人們的另一番思索:文學闡釋是否具有恒定的疆域?文學接受是否存在既定的向度?世上是否存在一把包開文學闡釋的萬能鑰匙?答案顯然是不言而喻的。因為人的創造力決定著文學疆域的不斷拓展,決定著接受視閾的不斷拓新,這是人類文學創造力的自然體現,也是文學接受不斷發展的歷史必然。對于闡釋者而言,就如同一個科學的探路人,對于一切新生事物或未知的事物都充滿著好奇。當一種新的方法有可能打通文學的疆域進而衍生新的闡釋向度時,他會毫不遲疑地闖入新的領地,用自己的智慧開啟文學闡釋的另一扇門。雖然這種急切地闖入或許會因魯莽而顯得缺乏周密性,甚至有可能破壞原有的結構,但它畢竟打開了文學世界的另一扇門,激活了文學應有的、開放的、自在的,但又銳新的序列,為文學的血液注入了新的活力。“闖不闖”是一回事,“對不對”是另一回事,只有永葆銳意進取的心態,才能不斷地打開文學闡釋的新疆域、拓新文學接受的新向度,文學生命才能活力四射,歷久彌新,文學研究也才能推陳出新,生機盎然。因此,《強制闡釋論》一文雖指出了問題的實質,但過于強調“強制闡釋”的偏離性而輕視“強制闡釋”的拓新性,忽視文學疆域的打開與接受向度的新拓展所帶來的積極意義,是值得商榷的。因筆者主要從事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的研究工作,故想從現代長篇小說闡釋疆域的打開與接受向度的新拓展對現代長篇小說傳播接受的意義與影響的角度就教于張江教授,又因限于篇幅,僅討論“場外征用”與現代長篇小說接受的新向度問題。不當之處,敬請張江教授批評指正。
一
“場外征用”依張江教授的理解是指“廣泛征用文學領域之外的其他學科理論,將之強制移植文論場內,抹煞文學理論及批評的本體特征,導引文論偏離文學”②。乍一看,這一界定很有道理,但琢磨后就會發現,“場外征用”“抹煞文學理論及批評的本體特征,導引文論偏離文學”,只是一種可能性,另外的可能性或許是給文學闡釋帶來新的路徑,帶來新的啟迪,甚至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刷新我們的認知。因此,筆者認為,“場外征用”不宜簡單地判定為一種走向,就其效果而言,其利大于弊,其得大于失,值得我們認真研討。
我們的討論不妨先從柳青的《種谷記》和歐陽山的《高干大》的闡釋與接受說起。
《種谷記》和《高干大》是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后解放區長篇小說創作的首批成果,1947年出版后受到了解放區文藝界的普遍歡迎。如雪葦就認為,《種谷記》“以體驗的深刻與技巧的優越突破了從文學來表現革命的農民及其生活和斗爭的作品的一般水平,給《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立下了一座實踐的豐碑”③。趙樹理也認為,《高干大》“是一本反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的小說”④。按理說,這樣一部實踐講話精神的開創性作品應該在之后的文學史中被迅速納入文學的“方向”中并予以肯定或被“經典化”。1949年5月出版的《中國人民文藝叢書》已將這兩部作品收錄其中,可見已初步邁入了“經典化”的門檻。然而,令人意外的是,之后小說不僅沒有“經典化”反而在當時的文學語境中被迅速邊緣化,即便是在1950年代初期革命文學經典化進程中的文學接受和文學史敘述里,這兩部從未因政治傾向問題受到批判的作品也未引起真正的重視。誠然,小說在藝術上略有瑕疵,如《種谷記》讀來有些拖沓,結構也有些松散,主題給人以含混之感;《高干大》中段情節急轉,主次情節稍顯混亂,影響了小說的整體性。但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瑕疵?它們被迅速邊緣化是否與之有關呢?對于這個問題,學術界至今未能給出令人滿意的回答。筆者由此想到,既然《種谷記》和《高干大》都是以陜甘寧邊區經濟建設為題材的長篇小說,那么,我們“征用”經濟學的理論去審視這兩部作品,也即是當我們以邊區經濟建設中的“經濟邏輯”探尋文本時,會不會有新的發現呢?endprint
我們知道,現代經濟學的構建以私有產權、市場和資源稀缺性為前提,在經濟主體做出決策時有四條原理:權衡取舍的必然存在、成本意識、邊際變量的考慮和對激勵的反應。⑤ 基于以上四條原理,我們將參與經濟的主體依據經濟學基本原理進行決策追求預期效用最大化的思維方式稱為“經濟邏輯”。《種谷記》和《高干大》所表現的正是邊區經濟建設中如何利用經濟原理實現利益最大化的故事。《種谷記》寫王家溝農會主任王加扶欲響應上級的號召動員全村農民以變工隊的形式集體種谷,村主任王克儉卻并不積極,富家王國雄也從中挑撥,變工互助工作無法進行(王克儉還同其它8戶人家自己種了谷)。看到集體種谷的計劃無法實現,王加扶將這一情況通報給上級并在區長的支持下撤換了王克儉的職務,與其他積極分子一起實現了集體種谷的愿望。《高干大》寫任家溝合作社主任任常有不為民辦事,群眾意見很大。副主任高生亮(高干大)有感于村里沒有醫生造成孩子夭折,主張成立醫療合作社,受到群眾歡迎。由于高干大為民著想,辦實事,合作社辦得十分興旺,并利用積累的資金,辦起了紡織廠、信用社、運輸隊。而郝四兒為鄉長弟媳“趕鬼”時出了人命,嫁禍于合作社被高干大訓斥,便對高干大懷恨在心,不斷地制造事端,挑撥是非,裝神弄鬼,直到裝鬼的郝四兒摔死,鬧鬼的事才真相大白。之后,合作社分了紅,區領導也肯定了高干大正確的方向,高干大被選為總社主任,成為陜甘寧邊區的勞動英雄。表面看來,兩部小說都在寫邊區經濟建設中如何組織好農民建好合作社的問題,但實際上所表現的“方向”卻大不相同:《種谷記》認可的是源于上級行政手段的“集體種谷”,故以對上級行政命令的執行與否作為人物命運與故事結局的最終結果;《高干大》肯定的是源于農民實際利益最大化的“經濟邏輯”,故以農民現實利益的受益度作為衡量的標準并予以認同。這其中雖有政治的取向,但顯然是兩個不同的“方向”。同樣的“命題”創作,為什么會有不同的“方向”呢?原來,《高干大》寫作的時期恰是邊區政府放棄包辦代替,允許民辦公助并將經營權放回民間、尊重市場規律的時期,而《種谷記》則是政府包辦,以“突擊運動”的方式組織農民進行生產經營的時期。指導方針不同,創作的旨向自然不同。但“經濟邏輯”終究是關于“主體”進行決策的邏輯,追求的是經濟主體的自身利益,當自身利益與整體利益發生矛盾時,如何取舍自然擺在了每個利益者面前。為解決邊區政府的經濟困難,也為了謀求利益的最大化,邊區政府自然鼓勵農民發家致富與邊區政府擴大稅源的利益相一致的個人訴求,相應的政策也會得到積極的貫徹落實。但如果農民發家致富的愿望與邊區政府的舉措并不一致,農民不能從中得到實惠反而需負重時,農民就會采取不同的方式予以抵觸,甚至消極對抗。
在《種谷記》與《高干大》中,我們也正好看到了這樣的情形:農會主任王加扶行動積極,村主任王克儉卻消極抵觸。對此,小說還特意寫到了王克儉的顧慮:“狗為了一塊骨頭互相咬得皮破血流,滿嘴是毛;兩個牲口拴在一個槽上,互相踢得神嚎鬼哭;雞啄到一條毛毛蟲,連忙夾在嘴里跑開雞群獨吞了,人比它們更會耍心眼。工作人員之所以不顧一切地發展變工,那是為了朝他們的上級顯功……減租算賬說是為了日子過不了,撲在前邊還有理由,這變工又是為了什么呢?”王克儉沒有從中看到自己應得的實際利益。高干大也在反駁任常有時說:“我的好神神!咱們憑良心說,合作社辦了五年,給過全體人民什么利益?人家正是問咱們要利益嘛!——咱們光會口說,實地上什么利益也沒給別人拿出來!”只有讓老百姓得到實際的利益,合作社才能辦下去,也才能辦好。所以,當區里強行征收股金時,他元氣充足地說:“政府有困難,老百姓又有意見,這件事叫我合作社給咱辦!這樣的事也辦不了,合作社還有個球用!只要政府里能夠答應遲半年用錢,我合作社把公債都包了。不要政府費事,又不要老百姓出一個錢,將來還能夠給老百姓分紅利!”農民看重的是實際的利益。但藝術的呈現也恰恰在這里出現了問題:作為信服講話精神的柳青和歐陽山,既要表現農民響應黨的號召組織起來進行生產的必要性,又要以現實主義的眼光如實摹寫這一產生方式對農民實際利益的影響與沖擊;既要表現黨的政策給農村合作社帶來的新變化,又要真實地反映自主性的經營模式給農民帶來的實惠和積極性。于是,文學的政治功利原則與現實主義精神之間就產生了無法顧全的矛盾。也由此,我們看到了這樣的現象:一方面,柳青理性地刻畫出“引路人”王加扶的帶頭作用,另一方面又客觀地描寫出“蛻化者”王克儉的退坡思緒;一方面極力支持,大力倡導黨的引路意義,另一方面又十分理解、暗自同情自耕農的自主行為。寫“引”緣自于黨的方針政策,緣自于作家的黨員身份;寫“蛻”緣自于經濟邏輯,緣自于作家的農民出身。黨員作家的身份使他撤換王克儉的職務將王加扶推向前臺,將現實的可能性轉化為歷史的必要性;底層農民的身份又使他理解王克儉的現實選擇,將歷史的必要性轉化為現實的復雜性。兩種矛盾相互糾結,小說就不是路線斗爭的線性展示,而是鮮活的陜北生活氣息與日常生活化的詩意書寫,雖然王加扶最后取得了勝利,但舒緩而略顯拖沓的情節與松散的結構無形中削弱了“引路人”的意義,也使主題變得含混起來。歐陽山亦同樣如此。一方面他塑造了支持任常有的區長程浩明,另一方面又著力刻畫了贊成高干大的區委書記趙士杰;一方面他寫到了錯誤的方針政策使任常有的合作社走向了死胡同,本人也酗酒死去,另一方面也寫到了新的經濟政策使高干大的合作社興旺發達,生機勃勃,本人還被樹為當地的勞模。所不同的是,歐陽山所表現的是整風運動前農村的經濟建設行為,當時延安建設廳提出的是“克服包辦代替,實行民辦公助”,因此,他對高干大的刻畫就顯得較為直截,只需表現出高干大如何與邊區政策相一致,以“經濟邏輯”為杠桿走群眾路線并且卓有成效就行。但因反巫神是當時一項重要的政治運動又不能不表現,作家就把它與故事的情節串聯起來了。又由于敗了合作社家底的任常有突然死亡,反巫神運動又不能不交代,于是小說就出現了中段情節急轉,主次情節稍顯混亂的藝術瑕疵。當文學進入政治一元化時代后,因柳青在表現中國農村現實的可能性轉化為歷史的必要性時孕生了“不必要”的糾結情緒,而歐陽山所表現的“民辦公助”也時過境遷,《種谷記》與《高干大》的“不合時宜”也就愈發凸顯,被邊緣化也就在所難免了。這就是《種谷記》和《高干大》之所以出現藝術瑕疵以及因何邊緣化的緣由。endprint
二
如果說“征用”經濟學理論可以解釋《種谷記》和《高干大》之所以出現藝術瑕疵以及因何邊緣化的問題,那么,“征用”存在主義理論會有怎樣的發現呢?下面,我們再以《圍城》為例談談存在主義哲學理論對《圍城》文學史意義的確立及其意義。
錢鐘書的長篇小說《圍城》出版于1947年5月,小說一經出版即引起轟動。但由于不久社會形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錢鐘書與他的《圍城》隨之也噤聲,直到1979年夏志清在其《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專章稱贊錢鐘書其人其文并高調斷言“《圍城》是中國近代文學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經營的小說,可能亦是最偉大的一部”⑥ 后,錢鐘書與《圍城》研究才重新被激活并促成了內地的反沖力,《圍城》的接受也從此步入正軌。
據筆者探析,自1979年至今,《圍城》接受在現實主義視閾、新批評視閾、存在主義視閾、比較文學視閾等四個視閾中顯示出學術進展軌跡。其中,現實主義視閾雖最先沿用卻因接受者先驗地以現實主義框架去套驗現代主義的文本,從而使接受視閾與文本旨向發生了錯位,落入了尷尬的境地;新批評視閾一度因文本中心主義等形式主義方法契合了轉型時代的接受訴求,加之夏志清的沖擊效應,彰顯出蓬勃的生機;比較文學視閾是探析《圍城》世界性因素的重要視閾,接受者以平行研究為重點,將重心放在展示錢鐘書與《圍城》同世界文學大師及其代表作的精神聯結上,意味著兩種世界同樣的偉大;而存在主義視閾因《圍城》的存在主義質素為接受者尋求中國現代文學與世界同步、與時代同脈的文本提供了理想的標本,實現了《圍城》接受的歷史性跨越。⑦ 為什么在四種主要的接受視閾中,只有存在主義視閾實現了《圍城》接受的歷史性跨越呢?
1947年7月,競文書局出版《英文新字辭典》,收錄Existentialism一詞,解釋為:“現代法國文學里的一種哲學。”戴鎦齡先生看后覺得不妥,便在《觀察》第3卷第4期發表《評英文新字辭典》一文,對該詞條的釋義進行了匡正。錢鐘書看后說:“這不大確切,只能說一派現代哲學,戰前在德國流行,戰后在法國成風氣。我有Karl Jaspers: Existenzphilosophie(卡爾·雅斯貝爾斯:存在主義哲學)就是1938年印行的,比法國Sartre. LEtre et le Nnant.(薩特:生命與虛無)Camus. Le Mythe de Sisyphe(加繆:西西弗斯神話)要早四五年。近來kierkgaard(克爾凱郭爾)Heidegger(海德格爾)的著作有了英譯文,這派哲學在英美似乎也開始流行。本辭典為‘存在主義下的定義也不甚了了。”⑧ 這是錢鐘書為辭典所寫的一個補評,并非是針對戴文提出意見,但這卻表明,錢鐘書對存在主義哲學的來龍去脈知根知底,也從另一方面證明錢鐘書以存在主義思想燭照中國社會的現實狀況與人的生存狀態,自有其潛在的哲學基礎與思想根基。因此,從存在主義哲學的視閾揭示《圍城》的意蘊絕非無根之木,無源之水,而是更接近錢鐘書本意的一種“場外征用”,一種對《圍城》的價值與文學史意義更為契合的有效路徑。
的確,表面看來,《圍城》通過“對抗戰時期古老中國城鄉世態世相的描寫,包括對內地農村原始、落后、閉塞狀況的揭示,對教育界、知識界腐敗現象的諷刺”⑨,同時借留學生方鴻漸的遭遇,從新式知識分子的角度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深刻的反省與批判,為民族的精神危機樣態把脈,對人的現代意義進行哲理的思考。實際上,《圍城》是以存在主義思想書寫人的存在主義主題,即:人生處處是困境,永遠無法擺脫,生活如此,精神亦如此,無法安妥的存在便是人的存在。這也是《圍城》的深層主題。
眾所周知,錢鐘書在《圍城》中關于“圍城”的旨意出現在小說中褚慎明與蘇小姐的一段對話里:“慎明道:‘關于Bertie結婚離婚的事,我也和他談過。他引一句英國古話,說結婚仿佛金漆的鳥籠,籠子外面的鳥想住進去,籠內的鳥想飛出來;所以結而離,離而結,沒有了局。蘇小姐道:‘法國也有這么一句話。不過,不說是鳥籠,說是被圍困的城堡fortresse assiégée,城外的人想沖進去,城里的人想逃出來。”這是對《圍城》主題的形象描述。其實,錢鐘書曾借方鴻漸之口點明,城里的人想出來,城外的人想進去這一“圍城”現象,不僅指愛情,也指人生。也就是說,人生也罷,婚姻也罷,莫不如是。若我們將這一哲理加以引申的話,我們就會發現,錢鐘書先生其實是在探索人的存在哲學的問題,即:人是一個不斷探索“我將何為,我將何去,我將何在”的存在物,人生也就是不斷探索這一目的的循環往復的過程。你看,從方鴻漸國外游學→上海工作→途中流離→三閭大學→返回上海的人生經歷中,作家不正是表現了進城→出城→進城的人生循環嗎?不正是思考人將何為→人將何去→人將何在的意義嗎?再聯系其他人物如趙辛楣、孫柔嘉、蘇文紈、唐小芙、褚慎明、曹元朗等人的命運,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因此,《圍城》表達的正是“人生充滿不確定性,生活充滿無目的性,婚姻也與盲目與偶然相關聯,生存的危機也隨之而來,焦慮與不安、悲觀與失望、孤獨與寂寞、空虛與惆悵等思緒就上升為主導情緒,并迫使人們不得不思考存在的價值與意義。這一切都是因為人本身的意義與命運的必然性被無意義與偶然性所替代,人對過程、對結果、對手段、對目的的探尋,都失去了對意義本身的探尋,于是,人生不是一個個有希望的聯結點,而是一個個無意義的虛枉的再生點。這就是《圍城》對人的非理性的深入思考,也是對人生處境的荒誕性的哲學思考,即:對存在主義哲學的形象的詮釋與準確的表達。”⑩ 從這個意義上說,夏志清先生認為:“《圍城》是一部探討人的孤立和彼此無法勾通的小說”{11},是很有見地的。也正是作家以存在主義觀念審視人生,也才能在主體取向上,以一種徹底的虛無主義的態度洞察人生,剝奪人們對意義本源的探尋,撕破人們對終極意義的關懷,將塵世間的荒涼、虛無與荒誕直面地坦示于人間,也才能以反諷與悖論的寫作姿態為人們奉獻出一部思考人的存在處境及其荒誕性的經典之作。也由此,當解志熙從存在主義視閾給《圍城》重新定位時,人們認為他打開了《圍城》接受的新疆域,實現了《圍城》接受的歷史性跨越,因為“通過對方鴻漸那種消極逃避,怯懦認命的人生態度的嚴厲的批判,錢鐘書在召喚一種不畏虛無的威脅而挺身反抗這虛無以肯定自我存在的勇氣,在張揚一種勇敢地承擔根本虛無的壓力并且明知無勝利希望而仍然自決自為的人生態度。這樣錢鐘書就由對虛無和荒誕的揭示走向了對虛無和荒誕的反抗。這既是《圍城》這部現代經典的主旨之一,也是錢鐘書與西方存在主義者在思想上的契合之處。”而且,“無須比較我們也可以看出,錢鐘書的《圍城》和薩特的《理性的時代》是殊途同歸,而與加繆的《局外人》則如同一轍。如果說薩特的《理性的時代》是直接從正面來肯定個人的自由和自為的勇氣,并把這種自由和勇氣推到極端的話,那么錢鐘書和《圍城》和加繆的《局外人》則是從反面來啟示人們,當孤獨的個人面對虛無的人生和荒誕的存在處境時,有沒有一種個體主體性,有沒有一種敢于獨立自為的勇氣,一種不畏虛無而絕望地反抗的勇氣,就是生死攸關的事了。而不論是從正面揭示也好,還是從反面暗示也罷,錢鐘書、薩特和加繆的出發點與思路在根本上是相通的,而且他們都以獨特的創作表現了無畏的勇氣,確定了他們各自存在的獨特價值。”從這個意義上說,“錢鐘書敢于通過《圍城》的創作來表達他對人生之虛無與存在之荒誕的認識,這本身就意味著對這虛無和荒誕的蔑視與反抗;而他也由此為20世紀世界文學貢獻了一部經典之作,確立了自己的不朽地位。”{12} 我們也據此說,《圍城》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部以現代主義思想出色地傳遞現代人觀念的優秀長篇小說,是中國現代長篇小說與世界意識同步構建的重要標志。而這一觀點我也曾多次在教學中談及。至此,《圍城》的主題意義與文學史意義在存在主義哲學的“征用”下得到新的闡發。
當然,我們還可以“征用”敘事學理論、符號學理論等其他理論對現代長篇小說作進一步的探討,限于篇幅,這里就不再具體展開了。
文學的疆域看似有邊實無邊,文學的探索看似有度實無度,以探求之心打開未知的視閾,以創造之意開啟文學這扇神秘莫測的門,是文學不斷煥發生命力的根本動力。在探索的道路上,要鼓勵探索,允許先破再立,不破不立。“場外征用”亦是如此。“偏離”是一種可能,但“刷新”同樣是另一種可能。或者我們換一個角度思考:“偏離”是否意味著“刷新”呢?只要我們以開放的胸懷面向文學,我們的世界將無比寬廣。
注釋:
①② 張江:《強制闡釋論》,《文學評論》2014年第6期。
③ 雪葦:《讀〈種谷記〉》,《論文學的工農兵方向》,大連光華書店出版1948年版,第158頁。
④ 趙樹理:《介紹一本好小說——〈高干大〉》,《人民日報》1948年10月7日。
⑤ 參見曼昆:《經濟學原理·微觀經濟學分冊》,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3頁。
⑥{11} 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劉紹銘等譯,香港友聯出版有限公司1979年版,第380、385頁。
⑦ 陳思廣:《〈圍城〉接受的四個視閾——1979——2011年的〈圍城〉接受研究》,《新疆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6期。
⑧ 錢鐘書:《補評英文新字辭典》,《觀察》1947年第5期。
⑨ 溫儒敏:《〈圍城〉的三層意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9年第1期。
⑩ 陳思廣:《中國現代經典長篇小說的審美構成與藝術貢獻》,《河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4期。
{12} 解志熙:《生的執著——存在主義與中國現代文學》,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17-234頁。
作者簡介:陳思廣,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四川成都,610064。
(責任編輯 劉保昌)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