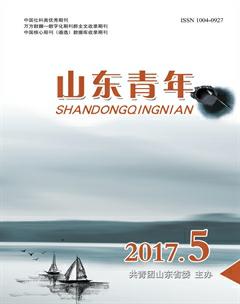宗教生活世俗化的趨向
古珊子
摘要:新的歷史時期下,中國穆斯林群體在不斷壯大、發展,特別是流動穆斯林群體,相較以往,大量涌入東部、東南部地區,已經在我國各大城市流動人口中占有相當大的比例。而在眾多因素的作用下,中國穆斯林的宗教生活也在不斷的變化發展,在哲瑪提多樣化,宗教派別差異以及朝覲政府管理等方面呈現出不同程度的世俗化傾向,通過探討這些方面具體表現,可以對近年來中國一些穆斯林宗教生活進行深層次理解,對涉及當前中國穆斯林宗教生活的其它方面進一步認識、研究。
關鍵詞:哲瑪提;宗教差異;流動穆斯林;朝覲組織
一、 前言
伊斯蘭教傳入中國至今有一千多年的歷史,發展至今,中國信仰民族眾多,現有回、維吾爾、哈薩克、柯爾克孜、撒拉、塔吉克、保安、塔塔爾、東鄉、烏茲別克十個民族信仰伊斯蘭教,伊斯蘭教教義、禮儀等許多方面已經滲透到其生活的各個方面,伊斯蘭教宗教生活是他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些穆斯林現已成為當代中國相當大的宗教群體。然而,新時期下的這些中國穆斯林宗教生活又有著新的變化,就筆者觀點認為,其主要趨勢是越來越世俗化的宗教生活。本文將從中國穆斯林的哲瑪提社區、宗教派別和朝覲管理等三個方面來具體表述,說明這種宗教生活的世俗化趨向。
二、 哲瑪提多樣化
Community(社區)在英文中的本義與伊斯蘭教中的Jamaat(哲瑪提)非常近似,都包含有共同體、集體的意思,指宗教信仰、種族、職業等方面相同的人構成的集體。“對于大部分回族穆斯林來說,Jamaat是他們的社會存在形式—一個與強勢的漢文化社會分立、結合的普遍形式。”[1]而清真寺又是哲瑪提中極為重要的部分,與其他宗教活動場所相比,清真寺不單是宗教活動場所,更是一個民族聚居社區的中心,也是哲瑪提族群性中地緣、社緣特征的重要體現。地緣是指寺坊意識很強,該意識表現在個體上就是穆斯林不愿意輕易搬離自己長期生活的哲瑪提;社緣是指有強烈的民族認同感和民族凝聚力,甚至這種共同的族群認同意識往往成為他們地緣結社的內在精神力量。
(一) 清真寺功能的演變
傳統社會(以及現在有條件的地方)穆斯林是不能離開清真寺生活的,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大量流動穆斯林進入城市,清真寺除了宗教功能,為了滿足穆斯林需求的多樣,而呈現出更多現代性與世俗化。比如南京的草橋清真寺現在不但可以幫助穆斯林舉辦伊斯蘭教傳統婚禮儀式,而且還組織了一個穆斯林婚姻介紹所,幫助青年穆斯林找到志同道合的另一半。
在教育上,雖然也有傳統的經學教育,但是由于現在穆斯林孩子普遍需要到學校學習漢文化,所以為了青少年穆斯林能夠學習一些簡單的宗教知識,一些清真寺利用暑假和雙休日開辦了阿拉伯語學習班和宗教知識講座,甚至利用假期組織青年穆斯林大學生開展健康有益的文藝、郊游、談心會等活動。比如天津清真寺南大寺曾經組織以流動穆斯林子弟為主的小學生暑期夏令營活動,帶學生到北京牛街參觀清真大寺等。
割禮是阿拉伯語“海乃特”的意譯,俗稱“遜乃提”,被視為履行天命和遜乃的圣行,意味著男孩在宗教上趨向成丁,開始步入承擔宗教義務的階段。以往割禮主要在清真寺舉行,一般是請專門的宗教人員施行。但是由于衛生觀念的影響,現在在醫院進行較多。醫院手術安全、傷口愈合得快,割禮地點的變化使這一圣行的宗教含義淡化了許多。有時除了進行手術外,傳統的宗教儀式不再舉行,保留的僅是割禮的醫學解釋以及對教義和民族文化的認同。
(二) 它樣哲瑪提的出現
在流動穆斯林進入城市以后,存在著原有的清真寺已經不能夠滿足大量穆斯林和清真寺距離較遠的問題。政府公開允許的深圳市宗教活動場所只有上梅林清真寺,另外還有兩個特許活動點。這樣的分布不能滿足流動穆斯林的需要,因此他們就只好采取一些特殊的方法來解決問題。其一是在比較大的清真飯店開辟一間專門供客人禮拜用的房間,這樣的禮拜房間,沒有專職的宗教工作人員,但是可以滿足人們的一些宗教功課需要。其二是在一些條件較好的穆斯林家中舉行小型集體禮拜活動,也可以稱做家庭聚會。這樣的家庭聚會一般在西北地區是不容易見到的,但是在流動穆斯林集中的地方如深圳、上海和南京都已經出現,且還不是個別現象。由于有了家庭聚會和清真飯店禮拜房間的開設,流動穆斯林的禮拜場所問題得到了一些緩解,結果卻導致流動穆斯林對清真寺依賴程度不斷降低,部分穆斯林的宗教活動得以離開清真寺。隨著流動穆斯林人數的進一步增長,這種以家庭和朋友為單位的流動的“哲瑪提”(小型集體禮拜)就可能會成為都市流動穆斯林的主要活動形式。
同時,網絡哲瑪提也是穆斯林活動的新型社區。正如馬強在研究中提出:“哲瑪提是一種特制的社區—宗教社區”,他認為這種社區實質“強調的并不是地域,而是共同的價值取向和具有同一文化的同質人口以及她們之間的互動關系”。[2]廣州穆斯林網絡互動社區成員主要是來廣州的翻譯隊伍和學生,以及部分全國各地的年輕穆斯林。網絡哲瑪提打破了時間和地域界限,已經成為廣州穆斯林相互之間聯系的重要渠道,他們在虛擬的網絡中共同尋求文化的認同,及時傳達著信息以及對伊斯蘭、穆斯林事務的理解。
三、 宗教派別差異弱化
中國伊斯蘭教的派別是國外伊斯蘭教不同教派思想傳入后,與我國穆斯林地區的實際相結合,并吸收中國文化的內容和傳統習俗,經過變革而民族化的結果。但是當下,中國的伊斯蘭教派呈現出不同程度的弱化,這種趨勢在流動穆斯林中尤為明顯,參考《熟悉的陌生人—大城市流動穆斯林社會適應研究》一書中對流動穆斯林的調查研究:“調查中,無論是天津、深圳、上海、南京、廣州、義烏,流動穆斯林的教派矛盾幾乎已經被完全消解。”
[3]
流動穆斯林到城市的主要目的是進行經濟活動,尋找經濟收入來源,并不是來傳教的,他們到清真寺的主要目的是完成自己的宗教功課,因此他們對不同教派門宦能夠相對寬容。客觀上來看,流動穆斯林面臨的生存環境相對一致,有利于他們整合成為一個整體,在城市中生存下去。比如義烏商貿城已經成為穆斯林一大社區,義烏的穆斯林主要來自寧夏,他們大多數在家鄉學過一段時間阿拉伯語和宗教知識,是非常虔誠的穆斯林。義烏商貿城水房小,同時來的穆斯林很多,沒有時間在那里等著大小凈,那么大家就采取一些變通的方法來解決。一些穆斯林在時間不允許的情況下就會用手摸一下腳,舉意后就上殿了。部分在義烏的流動穆斯林簡化宗教功課程序雖然不合宗教規范,但確也說明,流動穆斯林的伊斯蘭教教派分歧由于客觀條件的限制正在逐漸減弱。endprint
四、 朝覲政府管理現代化
1985年經國務院批準,開始實行有組織、有計劃的朝覲政策。中國穆斯林朝覲必須公開、公平、公正的進行報名排隊,身體健康和經濟富裕是基本條件。在獲得朝覲資格后,根據我國出入境管理規定完備體檢、政審以及申領護照及其它各項手續。在確定參加朝覲后,還要積極參加各地對朝覲人員進行的各項培訓,服從地方各級朝覲組織部門的安排,參加到指定的分團,注射疫苗,乘坐包機前往目的地等等,可見中國穆斯林朝覲已經不是單純的個人宗教信仰行為,而是政府組織管理下的團體行為,雖然它的宗教性質并沒有變化,但是具體的事象已經涉及世俗化。
中國穆斯林的朝覲活動已經有一套較為完備的指導體系,政府認為朝覲涉及國家安全、社會穩定、民族發展進步等重大問題,屬于政府必須管理的宗教事務,黨員干部不得參加朝覲,不得為親屬爭名額。中國伊協統一組織我國公民出國朝覲活動,國家宗教事務局還會同中國伊斯蘭教協會編寫了《朝覲團帶隊人員工作手冊》、《朝覲團教務指導人員工作手冊》、《朝覲團安保工作手冊》等培訓和工作材料。甘肅、新疆選派經學院優秀高年級學生隨團工作,云南開設了志愿者工作站,多名具有醫療專業技術職稱、阿拉伯語和英語對話能力的中青年朝覲人員為哈吉們服務。從上面這些可以看出政府對于朝覲是具有政治性質的管理,而種種條例的施行,鞏固了朝覲的規范性。
五、結語
綜上所述,當代中國穆斯林的宗教生活或者為了更加適應個體自身發展要求,或者為了使中國伊斯蘭教更好的傳播,一定程度上呈現出了世俗化的傾向,不僅在哲瑪提社區、宗教派別和朝覲管理上有所展現,甚至在宗教意識上,改變也在發生。以昆明聚居的新街回族社區,西華園穆盛達商貿公司和呈貢斗南奶牛合作社為例。居住在這兩個社區的新街回族,都以經商為生,其中西華園穆盛達商貿公司租地建設了集體宿舍,有近83戶近300名新街回族聚居在這里,是一個典型的回族“城中村”,形成了特殊的族群聚落。離開了幾世同堂的多代聯合家庭,新街回族農民進入城市后,新一代的孩子沒有在潛移默化中向長輩學習民族傳統知識和模仿的對象,加之家庭教育、社區教育與學校教育在傳統知識上割裂,家庭作為文化傳承載體的弱化,給傳統文化的傳承帶來了阻力。除了正式的宗教場合,他們不再穿戴傳統的小白帽、蓋頭,許多年輕人教門意識越來越淡漠,很少到清真寺、禮拜房。[4]然而這種變化在社會經濟發展下是不可避免的,中國穆斯林的宗教生活世俗化是必然的趨勢,同時做出一些新的改變可能更加有力于激發中國穆斯林的活力,進一步說也是促進了中國伊斯蘭教的發展。
[參考文獻]
[1]楊文炯,張嶸.Jamaat:都市中的亞社會與族群文化—以蘭州市回族穆斯林族群調查為個案[J].西北民族學院學報,2001,(03).
[2]馬強著.流動的精神社區 人類學視野下的廣州穆斯林哲瑪提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14-15.
[3]白友濤,尤佳,季芳桐,白莉著.熟悉的陌生人—大城市流動穆斯林社會適應研究[M].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10:88-90.
[4]周大鳴,馬建釗主編. 城市化進程中的民族問題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5:184.
(作者單位:云南大學 文學院,云南 昆明 650000)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