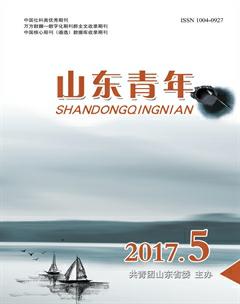淺談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楊悅
摘要:自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時代開始,有關政府和市場關系的討論已有悠久的歷史。在當前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必須正確理解有關政府和市場關系的歷史邏輯和理論邏輯,這是平衡政府和市場職能的關鍵。市場和政府是調節資源配置的兩種不同機制,二者相輔相成、相互補充,最終均衡于保護社會公共利益。
關鍵詞:市場和政府;均衡;社會公共利益
長期以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一直是經濟學中爭論不休的核心議題,各種理論觀點相互碰撞,常談常新。經濟自由主義時期,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經濟學家主張經濟的完全自由,政府只要做好"守夜人"的角色;到20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國家出現了大蕭條,凱恩斯主義在這種情況下應運而生,這一時期的主流思想是政府干預主義;到了20世紀70 年代,西方世界普遍出現了滯漲現象,對凱恩斯的政府干預主義提出了嚴峻挑戰,新經濟自由主義迅速崛起,重申要以經濟自由為主,但是承認經濟自由不是無限度的自由,認為政府在一定限度內可以對經濟進行一些干預。
一、明確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將上述歷史演變過程綜合起來看,我們可以發現,各學術流派的爭論可以歸納為自由主義和政府干預主義之爭。國家干預主義與經濟自由主義,是資本主義國家在發展市場經濟中對政府和市場關系所采取的兩種不同政策取向。而如何正確看待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成為制定一國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的重要指針,這需要從各自國情出發,依據市場在資源配置領域發揮決定性作用的定位重塑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實際上,“國家干預與自由放任這兩派都沒有絕對地否定或拒斥市場和政府的各自作用,而是爭執于政府與市場誰更有效的問題。因此,政府與市場孰大孰小不是問題的關鍵,有效的政府與有效的市場以及如何促成政府、市場的雙有效才是應有之義。”①但一般講來,各學派的理論均包含了自由主義和政府干預的思想,他們的分歧主要在于自由多一點還是干預多一點,并在各自的基礎上,提出不同的政策主張。
(一)市場是現代化過程中的第一選擇
市場經濟體制是人類發明的社會制度中最接近大自然的運作機理的制度。因為符合趨利避害、計算得失的人類本性和優勝劣汰的自然規律而具有無可比擬的長期效率、整體效率。世界范圍內各國現代化經驗也表明,對市場價值的尊重、對市場經濟體制的構建,往往是一國取得長遠發展的基礎。因此,新時期,我國政府首先必須尊重市場價值,讓市場機制在更廣更深的領域發揮積極作用,用市場選擇來保障我國現代化的基本的、長遠的效率。
(二)政府干預保障現代化的秩序和速度
政府干預的必要性分析。原則上講,市場能夠解決的事應全部交由市場去辦,但問題是能夠體現高效率資源配置的完全競爭市場只是一種純理論化的抽象,現實的市場機制無法提供完全符合其假的樣本,也就是說,市場理應在價格的引導下提供各種勞務,但由于不完全競爭的存在,市場不一定做得到。此外,市場還存在信息不充分和不對稱、外部性問題、公共產品供應不足、社會分配不公平等固有的缺陷。這就決定了在某一時期當市場的諸多缺陷暴露無遺并聯合作用導致市場失靈,秩序混亂,經濟衰退的時候,應輔之以適度的政府干預。
政府干預的可能性分析。我認為,政府干預必須同時具備兩個條件:一是市場確實不能有效的配置資源;二是政府的干預確實矯正了市場失靈而不是加劇了配置失效的程度。第一點談的是該不該干預,第二點談的是如何做才能有效的干預。只有當兩個條件都滿足的時候,合理有效的干預才成為可能。適度的政府干預能解決市場功能的扭曲,調節市場失靈,使全社會的經濟福利最大化;能通過稅收、社保和公共部門服務實現收入分配的均等化,能通過管理確保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在宏觀層面上,通過財政、貨幣和其他經濟政策來實現控制通貨膨脹和失業等目標。
如果政府對市場經濟行為干預過多,則違反市場決定資源配置這一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因為微觀經濟領域中政府的介入,使政府在“市場參與者”和“市場監督者”兩者角色之間很難有一個準確定位。由于政府掌握重要經濟資源配置權并控制重要生產要素的價格,從而會削弱政府對市場活動規范性監督的職能,并使企業缺乏自主發展的動力。
(三)在市場經濟中,政府干預和市場機制相互替。
這種替代機制的作用機理是:市場失靈對政府干預產生了需求,當政府干預的預期收益大于干預成本時, 政府干預便替代市場機制干預微觀經濟活動。當干預的預期收益小于干預成本時, 政府干預將讓位于市場機制, 也就是說政府將放棄干預。當政府干預所帶來的邊際預期收益等于干預的邊際成本, 政府干預就達到了最優水平。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不是一成不變的, 政府干預與市場機制的相互替代是一個動態過程。市場失靈和干預失靈界定了政府與市場的行為邊界, 在動態經濟中, 這種行為邊界是比較模糊和發展變化的。當出現市場失靈, 市場經濟的發展和規范運行需要政府干預; 同時, 隨著市場條件的變化、市場結構的動態調整和干預績效的變化, 政府干預行為也應該相應發生變化。但須遵循一個原則,即市場的經濟自由優先于政府的干預并決定政府干預的限度。
二、社會公共利益最大化是政府干預和市場自由的均衡點
在諸多流派里面,主張政府和市場折中的逐漸占主流。經濟學家都認識到如果沒有政府的積極推動,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在經濟上取得進展; 政府干預過多也會導致政府低效率,政府做的過多或過少都有可能導致政府失敗。那么,面臨的問題不是政府是否應當干預的問題,而是應當如何干預的問題;市場與政府究竟應當如何去“分工”,政府應當如何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才能有益于社會福利增進的問題。幾乎所有的現代國家都從事收入再分配、宏觀經濟管理和市場規制的活動,但是這些功能的相對重要性在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歷史時期會有很大的差異。人類進入社會之前的生活狀態已無法再現, 也許是洛克形容的“完備的自由狀態” 人們享有完全的自由權利, 也許是一片“霍布斯叢林”人與人之間就像狼與狼一樣,充滿仇恨、恐懼、互不信任的氣氛,完全是一種戰爭狀態。然而,人類最終拋棄或者超越了這種狀態,不約而同選擇了社會生活。當然人們進入社會生活的過程可能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圖景:一種是自然規律支配下必然的進化過程,另一種是指人們有意識的選擇的過程。但無論人類怎樣進入社會生活,都證明了社會生活能夠滿足我們共同的價值追求——生存、基因延續、自由、安全、便利、秩序、和平等等,而凝結著這些共同的價值追求的社會公共利益正是社會生活的主要特征,更是社會存在與發展的基礎。總之,社會公共利益是一種歷史沉積下來的“大善”,因此,無論是提倡市場上的經濟自由還是借助政府的干預,都必須遵循保護好社會公共利益的原則,二者在此消彼長中動態的均衡于社會公共利益最大化。endprint
(一)公共利益是市場主體行使經濟自由的邊界。
一直流行到20世紀70年代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形成的、支持政府干預的共識是存在問題的,因為它解釋了市場失靈( 因公共物品、外部性、不完全競爭、有限信息、短視等等),忽視了政府失靈。在戰后的共識中,人們通常假定政府只關注最大化社會福利,而且認為政府擁有它們意欲實現這個目標的全面信息。作為對政府干預的理論和實踐的反應,很多經濟學領域放棄了這種認識。隨著資本主義黃金期的不斷展開,歐洲和北美的長期戰后繁榮結束了,造成這種結束的現實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耗盡導致的利潤壓縮,資本主義黃金期的過度積累,德國和日本等新工業化國家興起導致的國際競爭加劇,以及資本全球化使得國家宏觀經濟管理變得不再那么有效。
在這種背景下,政府失靈的概念出現了,公共選擇理論家分析了各種各樣類型的公共部門失敗。國有化政策為積極型國家的失敗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在一個又一個國家,國有企業被認為無法完成它們的社會和經濟目標,它們缺乏問責性,而且它們具有被政治家和工會俘獲的趨勢隨著大規模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速度的下降,分配沖突加劇②,有關建立在統合主義討價還價和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管理基礎之上的福利國家的共識開始破碎,隨之而產生的是對政府職能的理論共識的破滅。20世紀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新自由主義成為西方國家制定經濟政策的依據,并取得一定的成效。以哈耶克為代表的新經濟自由主義學派雖然堅持以經濟自由為主,但接受政府在一定范圍內對經濟的干預,承認經濟自由不是無限度的自由,這一限度就是公共利益,即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不能損害他人和集體的利益,否則便會出現"公共地悲劇"、"搭便車"、和外部性等問題,造成社會總福利的減少和不均衡,最終會阻礙社會發展,削弱社會的民主性。
(二)公共利益是政府干預的正當理由
政府對市場和個人經濟自由進行干預,原則上是違背了資本主義所提倡的自由民主原則的,但若是出于保護社會公共利益的目的而進行,則增加了它的正當性,也會獲得人們的許可。因此,西方國家一個常用的原則是,國家或公共部門在發展公益事業的過程中有對私人財產的最終征用權。理論上,這個權力可以維護公共利益。在使用過程中, 如果得法, 這個權利也可以相對公正地保障個人利益和權力, 有助于實行良好的城市規劃,一方面解決發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盡可能減低公民損失,有利于社會的和諧和長治久安。綜上所述,政府干預思想和經濟自由思想本身都沒有什么錯誤,都曾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做出過巨大的貢獻,或是極大的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或是力挽狂瀾征服毀滅性的大危機。關鍵在于在不同時期我們需要對二者進行不同比例的配合使用,是自由多一點還是干預多一點,要根據特定時期的經濟發展情況和社會形勢而定,但不管在哪一時期,不管二者采取何種配合比例,最終都要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最大化為結合點。在進一步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政府和市場關系的討論已經從學術層面上升到政策層面。對于我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大國來說,在理論上慎重理解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積極發揮國家職能在發展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改革開放前三十年,我國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雖然建立了完整的工業體系,但是政府對經濟管得過死、過嚴,經濟發展缺乏活力,各類生產要素資源未能得到優化配置;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逐步調整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逐漸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了基礎性作用,激發了各種市場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力,為我們國家經濟的發展釋放了巨大的活力,三十多年的改革發展成果已經證明這一切。但是,同樣不能忽視的是伴隨改革發展成果的取得、社會財富的涌流,出現了財富分配的明顯不均,收入、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產能嚴重過剩,環境污染、生態破壞嚴重,市場體系仍不健全,政府職能的缺位、錯位與越位等等的問題。這就不得不以實踐中存在的問題為導向,重新思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政府和市場關系,只有厘清兩者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關系,并加以準確定位,才能進一步指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
根據對政府和市場關系的理論和歷史梳理,我們可以得到下述重要認識:第一,良好的經濟體制不是在市場和政府之間做出惟一的選擇,實際的經濟體制必然是市場和政府的某種結合;第二,就靜態和動態效率標準而言,市場通常比政府做得好;第三,存在各種各樣政府能夠改善市場運行的途徑;第四,市場力量能夠在改善政府的運行上發揮有效作用并減少非市場失靈③。
三、結論
中國與西方國家有著不同的國情,人口龐大、民族眾多、基礎薄弱、地域廣闊但差距較大,等等。歷史告訴我們,沒有一個相對強勢的政府,不要說經濟發展,國家統一都很難保證。確實,在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中,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都表現得相對強勢,但是,中國近20年來一直保持10%以上的經濟增長速度、經濟總量從世界的第10位左右跨越到第2位,經濟話語權不斷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不斷提高,特別是成功抵御東南亞金融風暴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等事實表明,中國政府的作用是成功的、是好的。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必須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出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當代中國的最大國情、最大實際”,“推進任何方面的改革發展都要牢牢立足這個最大的實際”,這既是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依據,也是調整政府和市場關系的總依據。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實踐沒有完結,世界各國政府與市場關系的演進也沒有完結,對政府與市場關系規律的經濟學探索也沒有完結。每個國家的經濟資源稟賦、經濟發展歷史、經濟制度演變、民族文化習俗等等不盡相同,市場經濟發展的普遍規律在不同國家的不同發展階段也必然表現出各自的特殊性。合適的就是最好的,檢驗一國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是否合適的標準應當是,綜合國力是否不斷提高,人民生活是否不斷改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是否可持續發展。
[注釋]
① 魏風勁 . 政府與市場的共生和互動———金融海嘯對中國宏觀調控變革的啟示[J]. 吉首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2009( 7) : 111 - 115.
②GIANDOMENICO MAJONE. Regulating Europe[M]. Psychology Press, 1996:11-23.
③張旭.政府和市場關系中的管制主義.[F].經濟學家.2016.3
[參考文獻]
[1]魏風勁.政府與市場的共生和互動———金融海嘯對中國宏觀調控變革的啟示[J]. 吉首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2009( 7)
[2]GIANDOMENICO MAJONE. Regulating Europe[M]. Psychology Press, 1996:11-23.
[3]張旭.政府和市場關系中的管制主義.[F].經濟學家.2016.3
[4]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M]上海遠東出版社,2004 年版.
[5] [美]查爾斯·沃爾夫《市場或政府---權衡兩種不完善的選擇/蘭德公司的一項研究》,[M]中國發展出版社,1994 年版.
[6] [美]查爾斯·林德布洛姆《政治與市場:世界的政治-經濟制度》.[M].王逸舟譯,上海三聯書店, 1992 年版.
[7] 周明生.《政府與市場關系--指標為什么下降》.[J].中國改革,2003(2)20.
[8] 朱立言,孫健.《政府組織適度規模研究》.[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作者單位:中央民族大學,北京 100081)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