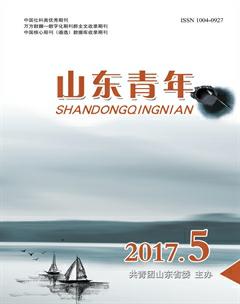環境犯罪非刑罰措施研究
張超
環境犯罪中適用非刑罰處罰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法律和社會效果,但是在立法和司法實踐中存在著法律地位、決定機關不明確和適用較少的問題,本文從非刑罰處罰措施的概念和意義出發,介紹國內外的立法和司法實踐,對環境犯罪非刑罰處罰措施的立法和司法適用提出建議,以期更好發揮其功能,保護環境。
一、問題的提出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隨之而來的也引發了環境污染的問題。特別是近幾年發生了大量的環境污染事件,可以說,目前我國的環境形勢比較嚴峻。除了通過民事、行政等手段對其進行懲處外,我認為刑法也應該發揮其特定的作用。我國刑法在1997年修訂的時候,在刑法分則第六章“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中增設了一節“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表明了對環境保護的重視,是我國環境保護在刑法上的一大進步。但是通過對刑法分則條文的觀察,可以發現對于環境犯罪的懲罰主要是通過規定刑罰的方式,刑罰大多數是在三年以下,對于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以五年到十年有期徒刑或者處以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另外在一部分條文中還規定了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可以說刑罰手段對于懲治犯罪和預防犯罪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在環境犯罪中我們也發現采取刑罰的處罰措施無法讓被破壞的環境得到恢復。近年來,在司法實踐中法院審理了一些環境犯罪的案件,在判決中運用了非刑罰處罰措施,非刑罰措施的適用對于環境的恢復以及對于受害人的補償有著積極的作用。所以有必要對環境犯罪非刑罰處罰措施的概念和意義以及適用進行探析,在此基礎上提出建議,以期對環境犯罪的預防起到一定作用。
二、環境犯罪非刑罰處罰措施的概念和意義
(一)概念
我國刑法第37條:“對于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可以免予刑事處罰,但是可以根據案件的不同情況,予以訓誡或者責令具結悔過、賠禮道歉、賠償損失,或者由主管部門予以行政處罰或者行政處分。”也就是說對于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行為人可以給予以上五種制裁措施,這被認為是刑法關于非刑罰處罰措施的規定。對于非刑罰處罰措施的定義,學者們有不同的表達方式。“所謂非刑罰處罰,是對應當承擔刑事責任或有人身危險性的犯罪人,以刑罰之外的刑事制裁措施來實現刑法防衛社會的目的。”[1]蔣蘭香教授認為“環境刑罰輔助措施又稱環境犯罪補充性處罰方法,是指對環境犯罪人所采取的刑罰之外的旨在恢復被犯罪行為破壞的環境,救濟被犯罪行為減損的自然資源的非刑罰處置措施,包括教育性處罰措施、民事性處罰措施和行政性處罰措施三類。”[2]從以上的表達可以看出,所謂的非刑罰處罰措施就是指除刑罰的主刑和附加刑以外的制裁措施。
(二)意義
1、完善了刑法關于環境犯罪的刑事責任方式,有利于預防環境犯罪。
從刑法的角度來說,環境犯罪侵犯的法益或者造成的后果關系到了人類的生存與發展,所以在懲處犯罪行為人時不得不考慮對生態環境的恢復。環境犯罪中行為人主要是為了追求經濟利益,其人身危險性較其它犯罪較小,過去單純的判處刑罰確實讓行為人受到了應有的處罰,但是被破壞的生態環境卻得不到恢復,并且大量的環境犯罪都是單位犯罪,對單位只能處以罰金刑,這對于其來說是無關痛癢的。我國刑法第37條確實規定了非刑罰的方法,但在很難適用于環境犯罪中,所以非刑罰的處罰方式能夠完善刑罰的缺陷。采用這樣一些有利于環境恢復的非刑罰處罰措施有利于環境生態的恢復,也對犯罪行為人及其身邊的人起到教育和警醒的作用,有利于懲治和預防環境犯罪。
2、有利于恢復受破環的生態環境。
環境犯罪與傳統的犯罪不同,單純的采用刑罰的方法還不能發揮補救被破壞的環境生態的效果,而非刑罰處罰措施可以適用于對被損害環境的恢復,最終達到對被侵害的法益的彌補。雷鑫教授認為,“非刑罰方式能以較小的司法成本彌補刑罰的不足,發揮其消除環境犯罪后果的持續危害和恢復環境權益的功效,是我國環境刑事責任發展的必然。”[3]大自然雖然有一定的自我調節的能力,但環境犯罪行為人為了追求經濟利益破壞了環境生態的平衡,造成環境的污染,在追究其刑事責任時可以考慮非刑罰處罰措施,注重對于生態環境的恢復。
3、體現了刑法的謙抑性。
刑法在所有部門法中是最為嚴厲的法,所以它是處理問題的最后手段。只有當民法、行政法等其它部門法不能提供有效的解決方式時,才由刑法來調整。環境污染是隨著社會和科技的發展而產生的,是發展的必然結果,所以對于很多行為不能一概認為使其犯罪化就可以得到解決,要同時兼顧社會發展的需要。“現代社會中雖然很多行為對生態環境具有極大的危險性,但是對這些具有危險性的行為不能一概持否定態度,很多行為是社會發展所必須的,是有益的,比如大型重化工業、核工業、轉基因等高端工程、航天業、高速交通工具等的發展,一旦失事就會給環境帶來重大破壞,但該危險是社會發展必須的危險,是發展的代價或成本。”另外,有些學者研究認為對于環境犯罪目前的處罰過輕,沒有達到懲罰和預防環境犯罪的目的,建議刑法加重對環境犯罪的處罰。筆者認為這種觀點沒有注意到環境犯罪產生的原因和特點。刑罰也不是萬能的,一味加重刑罰增加了司法成本,給國家司法資源帶來負擔。非刑罰處罰措施體現了刑法的謙抑性原則,在追究環境犯罪行為人的刑事責任時要考慮到環境犯罪的原因和特點,適用非刑罰處罰措施。
三、國內外立法和司法實踐
目前,我國的環境形勢可以說非常嚴峻,環境犯罪不斷發生,對生態環境和人民的生活都造成了重大的威脅和侵害。法院在對一些環境犯罪的判決中對被告人適用了非刑罰措施,促進了生態的恢復,實現了良好的社會效果。在前面我們分析過,環境犯罪不同于傳統犯罪,環境犯罪中犯罪人的主觀惡性小、人身危害性較小,犯罪主體主要為單位,在犯罪主體是自然人的犯罪中,犯罪人的職業主要是農民。環境犯罪以上的特點決定了刑罰的處罰方式。
環境問題目前已是一個世界性的熱點和難點問題,各國高度關注環境犯罪的懲治和預防問題。國外關于環境犯罪非刑罰處罰措施的刑法規定和司法實踐給了我國良好的啟示。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的《環境犯罪與懲治法》中就規定了關于環境犯罪的非刑罰處罰措施,“《環境犯罪與懲治法》在第四章專門規定了 ‘復原、賠償和損害的恢復,其目的是通過支付相關費用或者履行某種義務,恢復被環境犯罪破壞的環境法益。”[4]《俄羅斯聯邦刑法典》中也規定了關于環境犯罪的非刑罰處罰措施。如第254條毀壞土地罪規定:“處罰數額為過去最低報酬200至500倍或被判刑人2個月至5個月的工資或其他收入的罰金,或處3年以下剝奪擔任一定職務或從事某種活動的權利,或處兩年以下的勞動改造。”也就是說法院在裁判環境犯罪的案件時可以判令被告人恢復被破壞的生態環境。美國訴卡迪尼爾案中,被告同意接受1年有條件的緩刑,在緩刑期間,負責把由于該公司傾倒的4.5萬加侖磷酸而被毀壞的沼池恢復成原樣,對雇員進行環境法知識培訓。[5]通過以上我們可以發現國外對于環境犯罪規定了諸如“勞動改造”、“禁止擔任一定職務”等非刑罰措施來預防環境犯罪,為我國非刑罰處罰措施的規制和司法適用提供了借鑒。
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全國各地的法院已經開始探索適用對環境犯罪被告人采取非刑罰措施來恢復被破壞的環境,取得了良好的效果。2002年,湖南省臨武縣法院判決濫伐林木的犯罪人王雙英有期徒刑3年,緩刑4年,并且令其緩刑期內植樹3024株,成活率要求在95%以上。2008年12月15日,李華榮、劉士密等人在滬寧高速公路無錫市錫山區梅村段盜伐防護林中意楊樹19棵(10年樹齡)計3.9立方米。2009年6月18日,無錫市錫山區人民法院依法判處被告人李華榮有期徒刑1年6個月,緩刑2年,并處罰金人民幣2500元;判處被告人劉士密有期徒刑1年,緩刑1年6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2000元。同時,判決被告李華榮、劉士密共同補種意楊樹19棵(相同樹齡),并從植樹之日起管護1年6個月。補種樹木及管護期間,由無錫市錫山區農林局負責監督。[6]貴州省是我國自然資源非常豐富的省份之一,同時旅游業也是全省發展的支柱之一,環境保護任重而道遠。2007年11月20日,貴州省貴陽市中級人民法院環境保護審判庭和清鎮市人民法院環境保護法庭成立,在審理環境犯罪的案件中探索適用非刑罰處罰措施。清鎮市人民法院以被告人郎學友犯盜伐林木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并處罰金人民幣1000元;同時判處被告人郎學友賠償被害單位貴陽市烏當區水田鎮安多村民委員會經濟損失人民幣6453.50元,并于判決生效后90日內在案發地補種樹苗145株。判決生效后,清鎮市人民法院環境保護法庭于2008年3月12日將郎學友從監所提出,到案發地種樹。[7]以上兩個案例我們可以看出,法院在判決中首先對被告人適用緩刑,然后同時適用非刑罰處罰措施,使生態環境得到恢復,比起單純的判處刑罰,其對被告人的懲治和環境的預防達到了更好的效果。
四、非刑罰處罰措施立法及司法問題
(一)法律定位不明確
考察我國的立法現狀,對于環境污染的懲治和預防,我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大氣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礦產資源法》、《森林法》、《土地管理法》等法律中規定了大量民事的和行政的非刑罰處罰措施。如前所述,我國刑法第36條和第37條規定了非刑罰處罰方法,同時,刑法第64條規定“犯罪分子違法所得的一切財物,應當予以追繳或者責令退賠;對被害人的合法財產,應當及時返還;違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財物,應當予以沒收。沒收的財物和罰金,一律上繳國庫,不得挪用和自行處理”。總結以上的規范內容,有學者對其進行了分類:“(1)教育性的輔助措施,如賠禮道歉、公開悔過等;(2)民事性輔助措施,如恢復原狀、賠償損失等;(3)行政性輔助措施,如限期治理、勒令解散等;(4)沒收性的輔助措施。”[8]目前我國刑法對于環境犯罪適用非刑罰措施還沒有規定,只是在總則規定了非刑罰處罰措施,但是以上的非刑罰處罰措施難以發揮其恢復性功能,無法實現懲治和預防環境犯罪的作用。總結來說就是非刑罰處罰措施的法律地位或者說環境犯罪的非刑罰處罰措施的法律地位還沒有得到確定,這也導致了理論界對于非刑罰處罰措施這一概念的巨大爭議。非刑罰處罰措施符合我國當前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可以輔助刑罰措施的適用,從而更好地發揮刑法在懲治和預防環境犯罪中的作用,所以可以在刑法中明確其地位,從而促進其在司法實踐中的適用。
(二)決定適用的主體不明確
非刑罰處罰措施的性質雖然有爭議,但比較主流的觀點都認為其是刑事責任承擔方式的一種,那么又那個機關來決定其適用呢?理論界有觀點認為法院、檢察院和公安機關都可以,理由是《人民檢察院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規則》第255條規定“人民檢察院決定不起訴的案件,可以根據案件的不同情況,對被不起訴人予以訓誡或者責令具結悔過,賠禮道歉,賠償損失。對被不起訴人需要給予行政處罰、行政處分或者需要沒收其違法所得的,人民檢察院應當提出檢察意見,連同不起訴決定書一并移送有關主管機關處理。”《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268條規定,“在偵查過程中,發現犯罪嫌疑人不夠刑事處罰需要行政處理的,經縣級以上公安機關批準,對犯罪嫌疑人依法予以行政處理或者移交其他有關部門處理。”
產生上述爭議的原因就是立法不明確,所以應當在立法時做出相應的規定。
(三)非刑罰處罰措施適用少
雖然我國刑法明文規定了非刑罰處罰措施,同時在司法實踐中法院針對環境犯罪適用了一些諸如恢復環境的非刑罰處罰措施,并且達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由于在實踐中各地法官水平不一,不敢大膽適用非刑罰處罰措施,一般就直接適用刑罰措施,但是非刑罰處罰措施其實是對刑罰的補充,在環境犯罪中能夠使被破壞的環境得到彌補,然而在司法實踐中這種適用是非常少的。
五、建議
(一)明確法律地位。
在刑法立法中規定環境犯罪非刑罰處罰已經成為當今世界各國的立法趨勢。環境犯罪具有多樣化和復雜化的特點,而非刑法處罰措施可以有效的懲治和預防環境犯罪,所以有必要明確環境犯罪非刑罰處罰措施的法律地位,同時需要厘清環境犯罪非刑罰處罰措施的概念和適用對象、范圍等。
(二)明確決定主體。
本文認為決定適用的主體應該是人民法院。行為人在環境犯罪中的行為已經構成了犯罪,人民法院在審理環境犯罪案件過程中,對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并免予刑事處罰的犯罪人,并且法官認為被污染的環境有恢復的可能性的,可以單獨也可以復合對犯罪人決定適用非刑罰處罰措施。
(三)加大適用。
應加強對環境犯罪非刑罰處罰措施的適用。環境犯罪非刑罰處罰的適用在司法實踐中取得了很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前面已經提到了環境犯罪的復雜和多樣,同時行為人的主觀惡性也比較小,非刑罰處罰措施能夠更好的懲治和預防環境犯罪,但是也應該注意到環境犯罪對法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結合環境法的相關知識,所以應加強對法官的專業能力的培養。
[參考文獻]
[1]吳獻萍.環境犯罪非刑罰化的證成與價值[J].求索,2011,(10):172-173+213.
[2]蔣蘭香.環境刑罰輔助措施研究[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8,(03):55-64.
[3]雷鑫,鄭君.論環境刑事責任實現方式的發展趨勢[J].中南林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02):53-56.
[4]蔣蘭香.環境刑罰輔助措施研究[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8,(03):55-64.
[5]蔣蘭香.環境刑罰輔助措施研究[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8,(03):55-64.
[6]雷鑫,鄭君.論環境刑事責任實現方式的發展趨勢[J].中南林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02):53-56.
[7]舒子貴.環境犯罪適用非刑罰措施探析[J].貴州警官職業學院學報,2008,(03):29-32.
[8]蔣蘭香.環境刑罰輔助措施研究[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8,(03):55-64.
(作者單位:貴州大學法學院,貴州 貴陽 550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