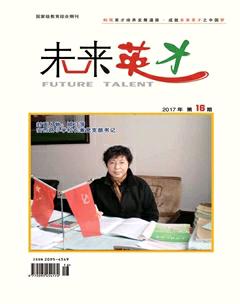普里什文《人參》淺談
宋碧君
摘要:普里什文是到目前為止,學界研究比較少的一個作家。他作品中融入的濃厚的自然生態觀和平和的氣質不太被這個追求新穎和刺激的社會喜聞樂見。但是正是這樣的返璞歸真,回歸心靈和自然才讓他的作品在浮躁的社會顯得難能可貴。本論文試圖分析他的代表作《人參》來一窺普里什文天人合一的生態觀,以及文化與民族相互影響和交融的世界觀。
關鍵詞:《人參》,自然生態觀,天人合一
在二十世紀的俄羅斯文學史中米哈伊爾·米卡伊洛維奇·普里什文占據著一個特殊的位置。普里什文與1873年2月4日出生于一個商人家庭,是俄羅斯著名的生態作家,哲學家。受到父親的影響,普里什文對大自然有著特別的感情,小小年紀的他就期待能去未至之境。在他的作品中,大自然,動物總是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他的代表作《人參》就是這樣一部充分展示其世界觀,生態觀的作品。
普里什文善于發現平凡人的智慧,善于描寫人和自然和諧共處的畫面。一代文豪肖洛霍夫曾推薦自己的朋友朗讀這部作品:“一定要讀一讀! 如此的明亮,睿智,老者的純粹,就想泉眼里的泉水。我前不久讀過,直到現在我的心都暖暖的。優美的語言,就像善良的人一樣讓人心靈歡快”。
盡管肖洛霍夫都曾經為這部作品迷醉,但是這部作品在當時的社會并沒有引起廣泛的注意。俄羅斯普里什文的研究者如托夫曾一針見血的指出各中原因:《人和自然的關系,那個時候,人們并沒有特別重視》。對于這個問題,高爾基進一步解釋到,普里什文的自然哲學是超前的,不能被當代人所理解,但是這些自然哲學遲早要被接受。
一、一部思想偉大且超前的作品的誕生
據普里什文的孫子回憶,普里什文《人參》的創作是受了阿爾謝尼耶夫的《在烏蘇里的密林》這部作品的影響。《當第一次讀到這部作品(《在烏蘇里的密林》)的德文版本的時候,他就立刻給高爾基打電話,說自己讀到了一本特別好的書,從書中了解了一個特別好的人(杰爾斯·烏沙爾)。》所以在《人參》的盧文身上中我們可以看到杰爾斯·烏沙爾的影子。
同時,作者融入了自己的在遠東的經歷。在那里他看到了有著雙梅花鹿般美極了的眼睛的女子。由于種種原因,他們并未相識。在1951年的日記里,普里什文如是寫到,—《女子的眼睛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而《人參》的其他部分大都是我想象出來》。作者的愛情經歷也在文中有所體現。青年時期的普里什文在巴黎遇見了他視為一生的的摯愛,卻因追尋自己價值而失去了她。從那以后,在不停止的尋找消逝的愛情的歷程中,在人和大自然的相互關系中,他汲取了許多新的創作靈感。《人參》的敘事主人公和美麗的花鹿錯過時,內心吶喊道:《獵人啊,獵人!你為什么當時沒有抓住她的角》。這里的“花鹿”,何止是“花鹿”,那是有著“花鹿”那樣美極了的女性,那是他曾經的幸福,他錯失的愛情![1- 2]
20世紀30年代,普里什文相繼寫成三本書《珍貴的野獸》,《梅花鹿》,《蔚藍的北極狐》。隨后,他將這三本書收編到一本書中,取名《金色的角》。最后在這三本書構思的基礎上,加上個人的生活體驗,普里什文創作了《人參》。
二、《人參》中所反映的普里什文的世界觀
1、普里什文的自然觀。盧文的形象是高爾基關于人于自然關系的理想代表。盧文長期生活在泰加林里,他尊重大自然,敬畏大自然,按照自然的規律辦事,和自然和諧相處。他從事著治病救人的偉大事業。他用一顆向善的心,睿智的語言贏得了所有人的尊重。
關于普里什文的作品,高爾基曾評價說:《在普里什文之前沒有人能這樣去描寫》。普里什文和其他的作家的最大區別在于,他的作品既有對人本的關懷,更有對自然的描繪,在他的作品中透著關于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及人類世界和自然世界的在本質上相似的哲學思考。大自然,跟人一樣,是地球不可分割的部分。在《人參》中大自然成為了一個動態的意象,他喚起主人公的哲思,治愈他的靈魂傷痛,讓他重返生活,重返快樂的創作。
普里什文試圖證明,人只有通過和自然的合作才可以獲得最大的收益。敘事主人公和盧文在“花鹿”的幫助下建立了歷史上第一個梅花鹿養殖園就是明證。
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趨同性也是本文的重要觀點,自然界的種種都會給人以啟迪。人參,它又被稱為生命之根。人參是擁有神奇療效的遠古藥材,傳說可以讓人煥發青春的光彩,健康永駐。老盧文深諳采參之道,他帶著敘事主人公去看他的生命之根。這棵人參很小,可是它卻跨越遠古時空,經歷過讓物種滅絕的大災難,存在到了現在。想到這個經過無數風雨的外表弱小的植物,人又有什么理由在暫時的困難面前屈服呢?所以當敘事主人公因為感情受挫,一蹶不振時,老盧文微笑著平靜地告訴他,他的生命之根是完整的,它還在成長。從這個意義上講,人參不再單是人參,它更是生命之源,是萬物的精神源泉,它哺育著人,給他們指明方向,幫他們找到自我。生命道路曲折蜿蜒,生命之根本就是忍耐和百折不撓。
而通向人參的路,則象征著通往成功,通往生命真知的路。道路漫漫且陡峭,標記很容易被風抹掉,被浪洗掉。盧文說,《在尋找生命之根時,靈魂一定要干凈,永遠不要回頭看向那已經揉碎和踏爛的地方。如果靈魂干凈,那么沒有什么障礙物可以破壞道路(破壞通往人參的道路)》,按照盧文的方法,許多年后,敘事主人公真的在漫無邊際的泰加林里找到了那棵盧文帶他看的人參。帶著一個純粹干凈的心靈,作者也終于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標,實現了自己的人生理想[3- 5]。
2、普里什文的社會文化觀。于人于人之間關系的關注,也是本篇小說的亮點。人與人之間,文化與文化之間是有沖突和差異的。盧文和小說的敘事主人公分別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社會形式的代表。他們每一個人都是人類文化的載體。敘事主人公——是用科學眼光看待自然的代表——他不能容忍盧文對自然的神秘現象神學的解釋。他依靠自己對自然認識的經驗,認識到人類的理智,知識的實質作用。盧文的迷信,他在自然力量面前的臣服——對于文明人類來說,已經是遙遠的過去。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