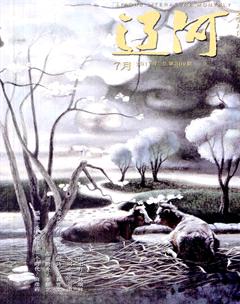山里山外
紅雪
剛進十月,山里就飄起了清雪,天灰蒙蒙、冷嗖嗖的。山上隆隆的放炮聲老是往表嫂的耳朵里灌。突然停了,表嫂預感到要發生什么事。真的發生了,表哥被山上滾下來的一塊石頭砸死了。噩耗傳來,表嫂沒說一句話,就瞪著眼睛瞅了三天房巴。
表嫂瘋了。
瘋了的表嫂就沿著這個十分鐘能打來回,撒泡尿能吡到頭的山城小街上來回瘋跑,嘴里不住地自言自語:“山里有啥好的?山外怎么了?”
小城的人們叫她瘋子。可以前表嫂卻是個美人。
美人總是招引男人的目光。
尤其是在那個憋死牛的河襠村。
河襠村不富裕,賊拉窮,二十幾棟土坯茅草房,像一片遺棄的荒冢,黑黢黢地趴在兩條拐把子河間的匯口處。自打清朝末年表哥的太爺的太爺闖關東在此落腳開荒種地,支起馬架子,升起第一縷炊煙,太爺的太爺就借助大自然畫就的形象,為落腳點起了個十分形象的大名——河襠村。到人民公社紅旗飄飄,百年風云飄逝,河襠村發面餅似的膨脹,最多時達到了一百戶,那是河襠村的兩條拐把子河出魚那陣兒,后來又萎縮到二十幾產,那是地壟溝刨食了幾輩人想過過城里人的生活,一戶接一戶往外搬的時候。可不管怎么折騰,河襠村依然是河襠村。人們追攆著太陽和月亮,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沒出現什么值得記上一筆的大事或人物,就連個秀才一類的讀書人也未曾出過。
表嫂也不例外,剛要上初中就被她爹大咧咧攆進地里去干農活,那年,表嫂才16歲。隊長說干不了整的,就干半拉子吧。表嫂要強,非干整的,累得小臉粉嘟嘟,腦門子上的汗珠子老往下滾。可還是跟不上趟……就有人幫她,是村里一個叫牤子的小伙子,健碩得像一頭小公牛,表嫂就忸怩地一笑,露出雪白糯米似的牙齒。說牤子哥你快歇著去吧。就貓腰一聳一聳拽鋤頭,一條黝黑的長辮子,在鴨梨似的屁股上掃來掃去。
一來二去,表嫂和牤子就有了眉目傳情,鄉野粗糲的風,拐把子河淙淙的流水聲,為這對初情萌動、兩小無猜的小情侶情感層層遞進,鋪展著原滋原味的交響樂,似有推波助瀾之意。可這天籟之音到了大咧咧耳里,就是鼓噪的蟲鳴,十分不悅耳。大咧咧不樂呵,說憑俺閨女那模樣,咋也得找個吃供應糧的,最次也得是個村干部家屬啥地。于是,表嫂就嗚嗚嚶嚶地趴在炕上哭了好幾個晚上,把眼圈哭得黢黑,眼睛抹得通紅。眼瞅著棒打鴛鴦散,忙子撲通跪在大咧咧跟前,祈求大咧咧高抬貴手成全他們這對有情人。大咧咧叼著一尺多長的大煙袋,吧嗒一口粘痰,砸在地上,濺起一圈灰,腦袋搖得像撥浪鼓。忙于求親不成,第二天就失蹤了,牤子父母尋兒不見,炕頭一個,炕梢一個,一個默默流淚,一個靜如樹墩,小土屋就荒墳一樣凄清了。
表嫂也惦記牤子,不知他去了哪里,抑或尋了短見,心里就罵他完犢子,不是男子漢。久等沒有忙于消息,就漸漸死了心,按照爹的旨意,18歲那年,跟了表哥。
表哥在大隊小學當民辦教師,個頭挺高,可五官長得不勻稱,咋看鼻子眼睛嘴都有些錯位。更要命的是表哥才念了三年書,寫自己的名字還費勁呢,卻讓他教五年級。表哥上課時不教課本,講閑話,講一雙繡花鞋,講程咬金三板斧、講狐貍精迷人……還哼哼王二姐坐北樓,好不自由。學生直笑。
每天早晨表哥穿上藍色的卡中山裝,的確良褲子,腰板拔溜直,雙手插在的確良褲兜里到課堂講閑話,招引了不少羨慕的眼光。村子里的人說看這做派,這小子還真像個先生哩。
那時,表哥他爹十大爺,是大隊支書。十大爺一字不識,可對土地親,侍弄莊稼十里八村叫得響。先當打頭的,又當生產隊長,后來就當上了支書。
有一次去公社開會回來,十大爺一大清早就把全村男女老少用大廣播喇叭喊到生產隊院子開會傳達精神。人到齊了,十大爺往中間一站,把油漬麻花的帽子一把擼下來,甩開八字步,氣勢洶洶在人群中轉了兩圈,可剛要開口,卻忘了該說啥。
他一拍腦袋說了句:“毛主席在北京說了,現在斗私批修——咱們呀,誰他媽了巴子也別休了,都下去干活去……尤其是一些老娘們,別老走東家串西家的,養的白胖白胖的,竟扯老婆舌。明個兒都去東大泡子挖魚池去,剩下的人由老疙瘩領著修梯田去!”
老疙瘩就是表哥。那時興養魚、修梯田,好好的土地,說挖就挖了。要在平地修出梯田,趕上向寡婦要孩子了,可社員們有招,愣是把鏡子一樣平展的土地,整出了波浪。十大爺在河襠村有威望,跟形勢跟得緊,一聲令下,沒有不聽他的。就這樣,河襠村修梯田,修出了名,十大爺也就成了紅人兒,公社、縣里老組織人來參觀,來參觀的人要吃飯,就一家一家輪莊吃派飯,吃得整個村子雞飛狗跳、羊跑豕突,十大爺的臉就起了皺褶,好像晚秋掛霜的核桃,
明里十大爺領著一伙一伙的人,東看看西看看,背地里卻罵:“媽了個巴子,來取什么經,就是他媽瞎折騰。”
表嫂被分到梯田組,累得夠嗆。表哥像個監工似的,指責這個,訓斥那個,唯獨不說表嫂。還時不時地幫表嫂挖幾鍬,老用眼睛往表嫂臉上掃。大伙就背地里說老疙瘩是不是對表嫂有意思了。
大咧咧可是真有意思了,坐在炕上捏起酒盅當著表嫂的面沒少夸表哥,說表哥人長得瓷實,有福相,爹又當官,真是打著燈籠難找,要是和這樣的人家交上親家,那可是咱們祖墳冒了青氣……表嫂低著頭光顧往嘴里扒拉飯,沒吱聲。大咧咧就罵,說小兔崽子你聽著沒有哇,啥意思你沒懂嗎?
正巧大隊原先的老師劉知青返城了,缺個空,表哥去頂崗。十大爺說,你他媽斗大字不識兩麻袋,可別糊弄人家這幫孩子,誤人子弟呀。
“糊弄啥呀,不就是1+1,2+3那點事嗎,公社李社長的兒子大雷、張民政助理的姑娘小丫,上學時還不如我呢,不都當上教師了嗎,人家還轉正了呢。”表哥晃了晃腦袋,上班去了。
當了老師的表哥,就有了更多的資本,向美人表嫂發起愛的攻勢。表哥知道,表嫂聽他爹大咧咧的,就隔三差五給大咧咧拎瓶酒、送瓶罐頭,背捆柴禾啥的。本來大咧咧就萌生要把表嫂許配給表哥之意,心里還害怕人家不干呢,這樣一來,大咧咧忽然轉被動為主動,自然喜上眉梢,喝著表哥送來的燒酒,也就別有一番滋味了。架不住大咧咧的軟硬兼施,轉年,表哥與表嫂就入了洞房。婚禮辦得挺熱鬧,也氣派,三輛四駕大馬車,從村西表嫂家拉上表嫂和娘家親,在村邊繞了一周,到了村西表哥家,十面大鼓、十副銅鑼,擂得山響,震得小村都好像晃動了,吹嗩吶的鼓足腮幫子,吱吱哇哇,幾掛炮仗,又配合著嗩吶噼噼啪啪響得豪放。endprint
升格為村領導家屬的大咧咧,喜興得走路就有了悠哉的曲線,咂摸著表哥給送來的小燒,一張黑魃魃的臉,就有了色彩。大咧咧和老伴說,我到墳地祭拜了祖宗,說咱們這一支兒出頭的日子到了,這人呀,說不準啥時候就發燒,好賴咱們也是皇親國戚了不是。
屯子人說,真是一朵鮮花插在牛糞排子上了。
可表嫂挺愛表哥。尤其是晚上,表哥折騰起來,美得表嫂第二天早晨起來頭不梳臉沒洗,就哼起小曲,一整天精神吭奮。
沒到半年,表嫂就像年豬一樣,發育起來,原先花骨朵似的胸部,兀自聳起兩座小山,顫顫悠悠,臀部也放肆地奢侈。
接著就是表嫂以一年一個的速度制造后代,直到小五滿月那年秋后,十大爺被民兵連長換下了位置。生產隊也在分田分地真忙中解散了。表嫂原先那種優越的貴族生活戛然畫上了句號,不得不對生兒育女來個緊急剎車,跟十大爺到自家的責任田里侍弄莊稼。
十大爺正日復一日地衰老,凸凹的臉宛如一穗瞎玉米,頭發像拐把子河上落上的雪,被風一吹,十分潦草,他嘴里常叨叨咕咕:這世道咋說變就變了呢。
縣里又下了一批代課教師轉公辦指標,本來有表哥,可一公布,沒有。原來,新上來的村支書被十大爺處分過。這小子好色,把村收發室的黃花閨女給干大了肚子。姑娘的家人不干了,說死說活讓民兵連長娶了那姑娘。可民兵連長有妻兒老小,娶不了,姑娘就投了河。投了河的姑娘父母鬧了幾天,就接受了民兵連長三麻袋苞米和一百塊錢的補償,不言語了。村里人說,得罪不起民兵連長,他身上老背著槍,一旦得罪,日后報復,用槍可咋整。村里人還說,其實人們不敢得罪民兵連長,是因為他是李鄉長的小舅子,出事后,李鄉長找十大爺談話,說:“這小子真操蛋,干人家沒開苞的干啥?老十呀,誰讓我推上這么個親戚,你,你看著辦吧。”
十大爺回家就喝悶酒。第二天,十大爺就宣布撤銷那小子民兵連長職務,回屯子種地去。可如今接替十大爺的卻是他,而他姐夫又榮升為副縣長了。
現在的村支書背地里罵十大爺:“你個老燈,當初還江北胡子不開面,咋樣?滾蛋了吧。”又對表哥說你別當什么教師了,還是去山里采伐去吧。第二天,表哥就扛個行李卷,和村里的幾個棒勞力上黑龍山倒套子去了。
表嫂不知道黑山有多遠,也不知道表哥啥時能回家。可他覺得日子被一大片一大片濃云,壓著,喘不過氣,
傍晚,表嫂正在院里喂雞,正趕上村支書打門口過。
“大嫂,喂雞呢?”眼睛往表嫂的胸脯里摳,臉上堆滿壞笑,腿卻不往前挪。
“嗯吶。你大哥走一個多月了,把我忙的連放屁的工夫都沒啦。”表嫂扭著屁股和村支書閑嘮。一來二去,村支書就跟表嫂整地粘粘糊糊。
屯子人對表嫂直撇嘴。
沒過仨月,表哥被村支書從黑龍山調回來到村辦公室打更。活兒倒是清閑了,可表哥卻整天高興不起來,坐在那一根接一根地抽紙筒子卷煙。屯里人都背地里指指點點,說表哥是借了自己老娘們的光了。
十大爺也一天天陰沉著臉。不用好眼瞅表嫂。背地里大罵表嫂的臉,讓黑瞎子舔了,給祖宗丟人現眼了。接著就病倒在炕上,整天說胡話,說這河襠村是咱們家老祖宗逃荒建起來的,從一戶到成了大屯子,咱們本本分分,守著土地過日子,門風正,可現在丟人呀……說我們那時咱當村干部都得干在前頭,現在的干部喝酒得先喝到前頭,還禍害人家老娘們……不應該呀!一口氣沒上來,十大爺走了。
屯子人就怨表嫂,說十大爺是讓她給氣死的。
閑話像深冬的大雪片子似的,壓得表哥家的小土房一下子矮了半截。
表嫂決定往九兒那搬,
九兒是表嫂的九妹妹,找了個林業工人,吃供應糧、穿勞保服、掙工資、做飯燒大木頭、凈吃大米白面。大咧咧也說,還是他的九閨女好,九女婿也好,城里的生活好呀。說時,眼睛翻了翻坐在旁邊的悶頭抽煙的表哥,撇了撇嘴。
說搬就真的搬到了山城。搬家那天,表嫂掉了眼淚,表哥也哭了。表嫂說故土難離,可這塊土地除了受窮,還是受窮,她再也不想回來了。
“哭啥?咱這是進城了,奔好日子去,應該高興!”表嫂損達表哥。九兒幫著表哥表嫂借了錢,買了兩間木刻楞,在山城安頓下來,表哥就上南山打石頭去了。這回表嫂也頓頓吃上大米白面了,心里掠過一絲欣喜,不管咋說,雖然城里人總管他們叫盲流,看不起他們,可畢竟進了城。
此時,從四面八方涌進山城討生活的鄉下人,泥石流一樣,完全超出了山城的承載力,弄得山城措手不及,吃、喝、拉、撒,都成了問題,就像突然來了一場冰雹,劈頭蓋臉把山城拍得鼻青臉腫。
進城的喜悅還沒從表嫂的臉上散盡,愁事就來了,五個孩子上學得有戶口,沒有就得托人花大價錢買。其實,學校已經滿員,教室再也裝不下這些外來打工謀生家庭的孩子了。于是,一場清理盲流的游擊戰,驅趕牲口一樣,在山城隔三差五上演一次,弄得表嫂整天提心吊膽,嘴角的火泡此起彼伏。表嫂決定去找九兒的老公公一李大胖子幫著落戶口。
李大胖子在山城謀得一份民政局長的官兒,表嫂是見過幾次的。見時,就覺出這個老東西的一雙藏在花鏡后的眼睛,老是不安分地越過鏡片,往她胸上撲。可畢竟是長輩,表嫂也就沒往壞處想。只見坐在辦工桌后面的李大胖子,邊用牙簽掏著牙縫里的垃圾邊說,她大姐這事不好辦吶……不過在山城,我李大胖子在城西一跺腳,城東都得晃悠,就沒有辦不成的事……誰讓咱們是親戚呢。說著就起身端一只空茶杯,眼睛發直說她大姐你喝水呀就靠過來。表嫂就慌里慌張往后退。等那雙大手還要得寸進尺時,表嫂終于使足勁把九兒的老公公推到了一邊,跑出了門外。
走在回家的路上,表嫂越想心越發緊,兩行淚不知啥時已滑出了眼角,淌了滿臉,弄得街上的行人回頭回腦地看。
學校逼得急,說再不拿來戶口本,就不讓孩子進校門了。清盲流的說,再辦不下來戶口,就不能在山城呆了,哪來的回哪去。
只好又去找李大胖子。endprint
表嫂說等辦成事我好好慰勞慰勞你,請你喝燒酒。李大胖子說喝那玩意啥用,辣的嚎的。說著,用手毫無顧忌地拍了一下表嫂肥碩的屁股。表嫂罵一句你個老燈泡子,燈油都要干了還挺邪性的,扔下表哥打石頭掙的兩干元錢,奪門而逃。
日子一天天過去了,左等右等也不見李大胖子的信。表哥已顯出有些急躁,他說有好幾產后搬來的都落上了戶口,這李大胖子錢也拿了,還不辦事,是不是我們還差點啥沒做到呀。
正說著,卻見九兒急三火四地來了,進門就像報廟似地嚎開了,說出事了,表嫂就急著追問說出啥事了,九兒說她公公搞破鞋讓人給逮住了。
表嫂一聽,心就咯噔一下,心想完了、完了,戶口的事泡湯了。心里這么想,嘴就罵出了聲“我早就看這老東西不是個正景物兒,老神神道道的。”
沒辦下戶口,就等于還是盲流,沒扎根,孩子上不了學,還是被清理對象。表哥就和表嫂商量,能否讓孩子回山外老家上學,可一提出就被表嫂否決了,表嫂說,咱們從地壟溝出來,屯里人都用艷羨的眼光看咱,認為咱們掉進了福堆兒,咋還有臉回去?絕對不能回去讓那些屯子人笑話。表哥再沒言語。
山城的夜有些浮躁了,山風呼呼地刮,好像大樹在哭,夾雜著街頭巷尾剛剛興起的歌舞廳飄出的“小城故事多,充滿喜和樂0J不是我不明白,這世界變化快”此起彼伏的輕柔及激越。鵝黃的路燈下,是一家挨一家的洗頭房、按摩屋,一群穿著暴露的女子,強拉硬拽從山上下來休班的伐木、采石工人,還有打著酒嗝的南方來山城倒騰木材的大大小小的老板。
表哥身子骨日漸瘦下去,十八磅大錘一掄就是一天,可掄來掄去,等大車小輛把石頭拉走時,表哥的心里突然生出一種空落落的感覺。想起了河襠村,想起那些模糊的、清晰的往事。和他一起上山打石頭的三個兒子,造的小臉灰突突的,一直和他鬧著別扭。離開校園的三個兒子不想來,想到外地闖闖,不行就回老家河襠村去種地,表嫂沒答應,逼著他們和表哥上山打石頭。表哥看一眼兒子們,還都稚氣未脫,尤其是小三,細胳膊細腿,明顯營養不良,穿著他的那件標志性的舊中山裝,空曠寬大,身體顯得異常瘦小。他的眼淚一下子就涌出來,“這得啥時是個頭呀?我對不起兒子們呀!”
山里回蕩著放炮的聲音,好像大雨來臨前的悶雷。環繞山城的南山、北山、東山、西山,都各有其主,被人承包了,不僅承包采伐,還承包采石,以及采摘山貨,就像占山為王的山大王,外人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大批的山外人被雇傭來,有的采伐,割灌機尖利的喊叫,剃著大山美麗的秀發;有的釆石,戰役一樣的炮聲,張著怪獸一樣的大嘴,一口一口地吞噬著大山。山頭山腳,像被鬼剃頭,道道傷口,猙獰而嶙峋。山在一圈一圈變瘦,崩下的石頭,被綠皮火車像運送原木一樣運到山外,用來鋪路、筑橋、蓋樓,有的成了制造水泥的原料。包工頭一般是不露面的,他手下幾個兇神惡煞似的家伙,在山腳下帳篷里與帶來的女人,聽著嗨曲,喝著啤酒,打情罵俏。一有風吹草動,就對像表哥一樣的一百多名打石頭的人,動以拳腳。僅僅一年時間,山就被消去了一角。正是五月,山上的達子香競相開放,多美的大山呀。可這些美,卻被轟隆隆的炮聲驚擾、追攆,直至無路可逃,成為大山頂上的一滴滴血。
表哥無心欣賞達子香的美,也無心可憐被摧毀的美。他關心的是工錢。包工頭不僅一次克扣工錢,有幾次還賴賬,玩失蹤。要不就指使山腳下那幾個剃著小平頭、胳膊上紋著青龍白虎的壯漢,毆打恐嚇討薪的工友,“你們這幫臭盲流子,都老實點!”他就眼睜睜看到這些人把一個工友打的鼻口竄血,最后還得跪地求饒……更讓他心痛的是,有天傍晚,他走在山城街頭,聽到吆喝賣雅格達聲,很像二閨女,走近了,真是,他的腿就有些軟,感到對不起閨女,畢竟她才十三歲。他沒精打采地躲在朦朧路燈暗影里,漫無目的往前走,忽然被幾個打扮妖艷的女孩子抓豬一樣拽住,嗲聲嗲氣,一口一口地叫他大哥,說進來玩一會兒吧,他就感到惶恐,一步步后退。就在他掙脫的剎那,他發現按摩房門口站著大閨女……大閨女穿個幾乎露屁股的裙子……他不敢看了,做賊了一樣逃走,他回家和表嫂說,表嫂沒有言語,“那些按摩房不就是窯子嗎?咱們家的孩子,窮死也不能去那地方!”表哥嘟囔著走了。
山上崩下的石頭,都被拉光了,到了開工錢的日子,表哥坐在一處高崗悶頭向遠方眺望。此時山外到了播種大田的季節,綿延的黑土地上,早已是人喊馬嘶,布谷鳥在田里飛,布谷、布谷地叫著,黑土殷殷,蒸騰藍色的霧靄,散發著蒸蒸向上的希望。一會兒包工頭就來給開工錢,這可是一年的血汗呀。他想明白了,開了錢,就把幾個孩子送回山外去上學,不管老伴咋反對,這回他要做一回主,年輕人沒有文化,就沒有前途,不能一代不如一代。其實,老伴要面子,是一種虛榮,怕回老家被屯里人笑話,有啥笑話的,人呀,三窮三富過到老,哪塊適應就在哪過,就跟羊群一樣,哪有草哪有水,就遷徙到哪,不行了,就回頭唄,河襠村雖窮,可畢竟是家鄉,水親、土親,人也親……想著想著,不覺日頭卡山了。
包工頭沒來。
“別等了,包工頭跑了……”不知誰喊了一聲。
“跑了?真的跑了?”表哥蒙了,這可是大半年的血汗錢呀!工友們亂作一團,有的罵,有的哭,有的要去報警,有的說干脆扯塊布條,到政府門前討說法……表哥忽地感到頭皮發麻、渾身的血液不流動了似的,幾次想站起來,卻沒成功,張了幾次嘴也沒發出一點聲兒,卻有一股黏糊糊的、腥的哄的東西頂到嗓子眼,一張嘴,一道血紅的液體射了出去。
“我操你八輩祖宗,這包工頭可真不是人揍的!”
表哥一陣狼嚎似的罵聲,引來工友圍上來看熱鬧。有人說這人好像精神有毛病……隨即躲瘟疫似地散去了。
臥床的表哥一陣明白一陣糊涂,腦海里又回閃著河襠村……那綠油油的莊稼,那書聲瑯瑯的教室、那雞鳴犬吠牛哞羊咩……是多么美妙的景象呀。而這里除了錢,還是錢……要過年了,各家各戶輪流殺年豬的場面,是那么親切,還有寫對聯、刻掛錢、蒸豆包、糊燈籠、打出溜滑、發紙、供老祖宗、走親戚……從電視上看到,河襠村重新進行了規劃,新修了路,修了小廣場,村里人吃完晚飯,都到小廣場扭秧歌,唱二人轉,老熱鬧了。而今這些,距離他是那么遙遠,都成了飄散的煙云。表哥的夢,仍在河襠村轉著,忽然有人喊——
“城里人!有錢了!”
“城里人!有錢了!”
是誰喊的?大雷?小丫?還是……表哥想看清楚,可眼睛怎么也睜不開,卻有兩行淚水撲簌而落。
“唉,我可能回不去老家了!”表哥輕嘆了一聲。
“不能躺著了,只要活著就得干活。”醒過來的表哥擦了擦眼睛,恢復了兩天,側歪著身子,又到北山打石頭去了。
借九兒的錢,九兒幾次來討要,黑著臉,說家里要買電腦,還要花錢送禮把她老公公給弄出來,如再給不上就賣房子吧。
氣得表嫂直哭。說現在我們就眼珠子沖前了,我家的情況九兒你不是不知道。背地里表嫂就叨咕說現在的親姐們也不行了,原先九兒在屯子當姑娘時老長到我們家,吃我的用我的穿我的拿我的,可現在土包子開花就忘本了……姐倆從此就掰了。
表嫂的神情日顯麻木了,好像秋后的茄子,沒了一點精神頭。
姐倆形如陌路的第三天,表哥就出事了。
打擊最大的當然是表嫂。
山城開始全面封山育林,就連采石也限制了,封了南山、北山和西山,只有東山還偶爾傳出放炮聲。虛胖起來的山城,閑起來的人們,開始流水似的往山外涌,山城在一夜間高潮泄了,不少臨街的歌廳、按摩房、酒樓,也大多鐵鎖把門。
山城又恢復了它的寧靜。
因生活作風問題被摟進去的李大胖子,還交代炸山采石的老板是他。
表嫂還是滿街瘋跑,披散的花白頭發,凌亂,干枯,離遠一瞅,像個紙糊的風箏在飄。她嘴里不停地叨咕著,“孩子都到山外去了,我不走,我要陪著我的老頭……陪著我的老頭……陪著我的老頭……”
以前還有人圍觀,幾個頑皮的孩子跟在表嫂身后嬉戲,打鬧,可現在只有表嫂形單影只,自說自話,好像山城壓根就沒有表嫂這個人一樣。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