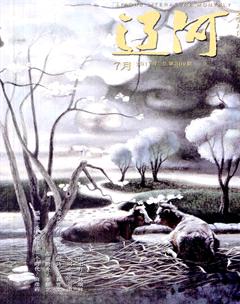車間時光
李新立
時光的機器不知疲倦地運轉,一些事物隨之消失,但似乎仍然停靠在記憶的入口。驀然回首,許多舊事雨點般灑落。
1995年初春,萬物正在復蘇。上午八時,陽光充足,心情沒有覺得不好,我們七八個男工,先去人事部門報到,然后由一位不認識的秘書領著,去了生產調度室。從文件上知道,我們分到新的崗位上班,這多少有些新鮮和興奮。生產調度室里,六七張桌子前都坐了穿著工作服的師傅,據說他們是各車間的主任。按理,主任們就是我的上級,生性膽怯的我,不由得有些莫名其妙的緊張。
我們經過主任們再次分配,就有了自己的歸屬。我的車間主任,年齡稍大,方臉,頭發灰白,說話聲音低沉。他打量下我,說:“你這身板,恐怕耐活不了幾天,那崗位連臟帶苦,你得有個思想準備。”他在前面走著,我像頭瘦弱的小牛,快步跟著。又到了庫房保管室,主任簡單地填寫了份領料單,保管便交給我一把大鐵锨、一雙手套、一頂防塵帽和一只防塵口罩。主任仍然在前面走著,我扛著鐵锨,把防塵帽和口罩提在手中,一路晃蕩著來到了生產車間。車間是高大的窯樓,機械聲填滿耳朵,主任朝上喊了幾聲,便有粉塵落入他的眼睛。正好,過來一位瘦長者,主任說他是我的班長,今后就歸他管了。班長又把我領到窯下,指著鏈運輸送帶,強調了下崗位的重要性和操作要點,吩咐了幾句上下班時間,隨即轉身上了窯樓。一九九六年春暖乍寒的一天,我所在的小廠被該公司兼并,初次體味到了失業的懼怕,還算好,約莫半個多小時里,轉來倒去,跑了不少路,但很快認識了自己的上級,進入了新崗位,內心多少有些安慰,甚至幾許溫暖。
宿舍在西邊綜合樓的二樓上。下班時,有人提醒我去總務要一把房門鑰匙,便找了過去。總務笑嘻嘻地說:“新來的?”說著話,從一堆鑰匙中找了把黃色的,心里懷疑它是否能打開房門時,發現上面貼著一片膠布,趕緊捏在手中走了。從表皮的磨損程度看,使用過它的人已經不少。宿舍的樓道里,污水是新灑出的,泛起的灰白色泡沫正在破碎,洋溢著洗衣粉與香皂的味道。順墻壁立著的鐵锨上,掛著汗漬未干的工作服和落有灰塵的防塵帽。打開右手第一間房門,高低床幾乎與人撞個滿懷。這是四人住宿,三張床位上已經躺著人,那個上面空著的床就是我的了。宿舍內一張小桌,一件衣柜,剩余的空間不多。毛巾搭在床頭上,臉盆和腳盆塞在床下。地面上很濕,洗過一般。我差不多明白,上下班的同事都懶得去公共澡堂,喜歡在狹小的空間里擦拭身體上的灰塵和汗漬。正是春夏交替,窗戶沒有全部關閉,只拉了窗簾,但自窗口吹進來的清風,仍然對室內潮濕發霉的氣味似乎無可奈何。他們三個,扯著呼嚕,我往床上扔東西時,竟然沒有被驚醒。
這意味著,新的生活開始了。
窯樓高過三十米,如果加上伸向半空的煙囪,估計不止四十米,抬頭仰望,這個碩大的鋼鐵與水泥的結合體,似乎懸浮在頭頂之上。當然,我很少看它,剛進入生產區域時,已經有過一次經驗:上空彌漫著肉眼難以看到的顆粒,趁抬頭的機會,這細小的家伙就會奔入眼角,那種灼熱、酸癢,實在叫人難耐。一條約五十厘米寬的鏈式輸送帶,以三十度的傾斜度,插到窯下。我們一組四人,主要轉運從窯樓卸出來的料塊。我們頭戴防塵帽,嘴堵防塵罩,除了眼睛,一張臉基本全被隱藏。那些塊狀的結晶體,從干度以上的高溫燃爐內跑了出來,還帶著炙人的熱氣。它們受咖嗎射線的的指揮,排卸得極有規律,每隔一小會,卸料器“昂——”地叫一聲,從溜糟上“嘩——”地流下一堆料塊,“昂——”地叫一聲,“嘩——”地流下一堆料塊。那個鏈板輸送機,好像一個人,始終處于緊張狀態,保持不卑不亢的速度,將料塊運上來,正好溜到我們放好的架子車上。等架子車裝滿了,挪到一邊去,趕緊換上另一輛,然后推著裝了料塊的架子車,“丟丟丟”地一陣小跑,轉倒在附近的堆場上。無處不去的風,此時顯得十分廉價,隨時為料塊們降溫。
和我同在一個小組的兩位同事,四十歲左右,都姓韓,是從一個分廠抽調來的,我去時,他們已經在崗兩月之久。顯然,二位同事十分熟悉這個崗位的工作。或許覺得是體力勞動,技術含量太低的緣故,他們從未給我講過操作要領,倒是我眼看著他們的勞動步驟,知道怎樣使用架子車和鐵锨才能更為輕松一些。共事半月之后,到了發放工資的日子,同事們都好像去了主任那兒簽名領錢,我心想時間太短可能沒有,或者累積到下月,便沒有去。幾天后,一同兼并上來,并被分配到另一小組的兄弟問我領到了多少工資,我反問他:“有嗎?”牠說雖然不多,但還是有的。我好面子,怕被笑話,不敢去問主任,就問我的這兩位同事:“不知道我這月有工資沒有。”兩位都沒有吱聲,就沒有再問。心想,如果有,饃饃不吃還在籠子里放著,不急。
又是幾天后,倒過班回宿舍的路上,碰見車間主任,擦身而過時,他突然回頭喊住我,說:“見你不來領工資,就捎給你小組的小韓了。”我實在張不開口向韓師傅索要幾百元錢,也不明白他倆為啥不把我的工資交給我。我的宿舍下鋪的兄弟,也是和我一起被兼并過來的,知道這事后,罵我沒有出息,使我十分慚愧,半月后,我那兩位同事提著個黑塑料袋,強行塞到了我懷里,我看看,是五十元一條的煙,外加我的工資。他倆說,實在不好意思,代領工資后給忘記了。看他倆一臉歉疚和不安,我明白是我下鋪的兄弟向他們開了口,我頓時不好意思了起來。正好口袋里沒有香煙了,就收了下來,說:“辛苦兩位哥了。”將煙錢還給了他們。此后,我的這兩位同事還告訴我一個偷懶的秘密:大夜班是最容易疲倦的時間段,可以去窯樓的操作間,趁師傅們不注意,將咖嗎射線控制儀調一下,可延長窯下卸料間緩時間,減少卸料次數。這個辦法我從未使用過,也不知真假。而他倆,不久就返回了原企業,不久,這家企業被解散。
勞累,使大家像沒有發生什么事一樣。一切按部就班進行著。
這種機械且有規律的勞動,使人的大腦處于凝滯狀態,不容多想,就從春天進入了夏天。
春天的沙塵天氣,在窯下崗位,最能看見它的威力。風像一群亂竄的瘋子,進入高大的車間與車間、設施與設施間,找不到順暢的出路時,四處盲目沖撞。這時候,勞動防護用品顯示出了它們的脆弱,眼睛和脖子是最容易遭受侵犯的地方,砂土、灰塵常常耗費許多精力,才能清洗干凈。而夏天,盡管炎熱的天氣加上窯下料塊的溫度,讓人產生總想躲避到蔭涼處的欲望,但少了沙塵的侵襲,應當說是好多了,如果有一場雷雨,那更是上天最好的賜予。晚秋時節,上夜班是苦差事,尤其是上大夜班,要從深夜十二時上到第二天早晨八時,瞌睡不說,還會受到冬天般寒風的侵擾,特別是在凌晨時分。這時,我會違犯紀律,偷偷睡一會兒。那些倒在堆場上的物料,雖然硌人,但很是溫暖,躺在上面,沒有多想,不講究睡姿,就很快沉沉入睡,把隆隆的機械聲甩到世界之外,即便是細細的夜風在身上取暖,也不會醒來。身體升騰而起,一種快意從神經中抽出,但這不是做夢,不用睜眼就會知道,另一車間駕馭裝載機的師傅,轉載堆場上的物料時,把那只大鏟伸在了我的身下,故意將我輕輕掂起。我一點不討厭這樣的玩笑。endprint
不知是不喜歡還是不敢妄動,我很少隨意脫崗竄崗,通常往返于家、宿舍、崗位之間。當然,也有例外,夜班寂寞難耐,偶爾遇到窯面操作不正常時,窯下的鏈運機一般會停下來。抽身爬上窯樓,聽師傅們說東道西。深夜的恐懼,來源于人們喜歡在恐懼時說鬼事。師傅們說,廠區的西北邊,原來有一排宿舍,修建這些房子時,下面挖出來的不少白骨和“麻錢”,想必是個很大的墳地,但不知道是哪朝哪代的,從陪葬品看,可能是平民的墳地了。師傅們還說,廠里有一座房子,人住在里面,半夜時分,總感覺床在動彈。我不以為然,偏偏有人信誓旦旦地說:“對對對,是是是,我在那房子里住過的。”此后,不管是白天還是黑夜,經過那間宿舍時,不禁頭皮發麻,還說,那座舊窯樓,八十年代初發生過噴窯事故,火光彌漫了整個窯面,人無處可躲,一個職工從窯上掉了下去,沒有搶救過來。我不知道什么叫噴窯,又不敢多問,一直把這事當做迷,而在窯下作業時,又不由自主地想,他是不是落在了我腳下的這個位置?瞬間,一具血肉模糊的尸體,仿佛橫陳在眼前。
我多次在班后爬上高高的窯樓,眺望遠處。
新疆至上海的公路是國內最長的國道干線。路邊有許多縣城、村落,也有許多工廠,包括冒煙的工廠。東北邊有座叫“烽臺”的山(我原以為山上至少有一處烽火臺,但沒有,與古代的烽火臺不沾親帶故),山上有三棵松樹,據說是宋時的,這山就與周邊的山與眾不同了起來。與眾不同的還有,山上有座三將軍祠。祠不大,不過是間簡陋的小屋,陳列著三個牌位。很明顯,祠的規模與三位將軍的身份極為不符,后來知道,原來的祠毀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我便想,這三棵松樹,一棵代表劉銪,一棵代表吳蚧,另一棵便是吳璘了,山叫“烽臺”,也有了稍合理的道理。早晨太陽剛升起的時候,山上包裹著一層淡藍色的煙霧,這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我站著的這座窯樓產生的。也好,有了這“霧”,山在霞光中,有了些神秘,我曾經打定主意要和古人完成一次對話,但一直沒有深入下去過。我的這個行為多少有些與眾不同,總有人走出來,說:“你在做啥呢?”我說:“我在看山呢。”他也朝山看上一眼:“山有啥好看的呢,不如緩著去。”我便歇息去了。
崗位是枯燥乏味的。時間長了,內心深處對日復一日的工作產生了厭煩,甚至有一種莫名的抵觸。有時,盼望著設施不太正常,只有這樣,我們才有閑下來的機會。這樣機會還是有的,盡管時間只有兩三個小時。但車間有要求,不能回到宿舍去。曾記得另一車間,一員工趁這樣的間隙回到了宿舍,開機后不見他上崗,派人去找,宿舍門關著,一股橡膠味從門縫里透了出來,趕緊撞開房門,發現他已經死亡。原因就那么簡單,他偷偷用電爐子燒水喝茶時,不小心觸電,經驗教訓一再告訴我,紀律有它的道理,那只劍,就懸在不聽話的人頭頂之上。那么,我可以在廠區走走看看。六十畝大的生產區,到處充滿陌生的誘惑。朝西,幾百米,到了三車間。三車間四層高,不敢進去,站在車間門口朝里張望,一樓偌大的空間里,好像只擺了一件鋼家伙,它緩慢地轉動著,灑到身體上的水,很快蒸發,熱霧升起,不多停留,很快散盡。后來知道它叫球磨機,不去車間還真不知道它吼聲均勻、高亢。再朝西,一排平房,干凈漂亮,不像其它車間灰頭土臉。透過玻璃窗戶,看到三五位穿著白色長褂的女工晃動,持著檢驗器皿的樣子煞是好看。想進去,見門口寫著“非工作人員勿入”的字樣,立刻停下了腳步。
很少與車間同事交流閑談,也不太和本組同事說話,我們之間只是勞動的默契和機械,一個動作就會明白意思。只是按時到崗,準時回家。若實在勞累,匆匆洗一把,上床休息,本想瞇一會兒,卻酣然大睡。有時,突然就有說話的沖動。比如,白天人多,往往將來來去去的同事、領導忽略。晚上則大不一樣,人少,路燈亮起來,氣氛顯得孤單枯燥。如果想說話,無非是打發冷清,或者清除睡意。守著鏈運的地方,東西貫通,除了窯下出來的熱浪,就是由西刮向東邊的風。風竄了進來,被東邊的墻壁一擋,又折了回來,經常其中包裹著灰塵,細塵直奔衣領,顆粒稍大的,甩打在臉頰上。每遇這種情形,我會選擇堆場躲避,一般情況下,很少有人過問。這時,會從幽暗處閃出一個人,直奔過來。燈光下,看清他手里提了一根鐵棍,腋下夾著本子,他將鐵棍用力插到料堆中去,看看鐵棍上的刻度,記在本子上,馬上轉身離去。有次,我從料堆上翻了起來,問:“你這是做啥?”他說,在測算小時產量,每天抽樣四五次。他看不清我的臉,我戴了防塵帽和防塵口罩,熟識的人只能從聲音上分辨。此后好多次,我總會問他:“是多少?”他會告訴我一個大約數。還問過他年齡和學歷,二十五六歲,某專業院校畢業。便心中生出些許羨慕和感慨。兩月過后,抽樣的人換了一個胖得可愛的老頭,他看著我,好像熟人似的,呵呵地笑著,讓人想起胖佛陀。肯定是我開口問了,他告訴我,上次的那位調走了。后來,調走的那位成了我的主管。
從來沒有想過,希望有一天我也能被調走。
有次,趁鏈運緩慢轉動的間隙,去離我最近的庫底轉料崗位去,發現這里有只暖水瓶,心里一陣暗喜。由于崗位燥熱,補充水份似乎成了我們的勞動習慣,我帶到崗位的一杯水遠遠不夠身體所需,一直想把水壺拿過來,一是覺得麻煩,二是擔心被打碎。附近有水壺,實在叫人高興,便折身回去取了水杯。我還在倒水時,從角落處閃出一人,女的,包裹著工作服,看不清模樣。她允許我倒水,還簡短地聊了幾句。就知道她的丈夫也在公司內,禿頂,微胖,可惜我當時不曾見過他(認識他不幾年,他就因病去世了)。她說,她見過我,前天培訓時我坐她前面。第二天培訓時,有人喊我的名字,從聲音里知道是她,仔細打量,她的頭發稀少,臉膛上有酸堿腐蝕過的痕跡,算不上漂亮,但覺得她端莊善良。她說,老師講的速度太快,她跟不上作筆記,希望課后把我的筆記借她。第二天還我筆記時,她說我的字寫得真好,肯定有文化,不會在車間干長久的,總會有一天被調走。
業務培訓是新員工的必修課,而這次屬于綜合培訓學習。西邊綜合樓的一間大會議室里,鐵架子支了一張涂黑了的木板。化驗室的技術員,一連講了七天,我在本子上也認真記了二十多頁。我本來化學學得不好,那些符號和元素記得歪歪扭扭,至今沒有弄清三氧化二鐵、氧化鈣、三率值、飽和比。幾個月后,說是要進行考試,考試內容都是我記在本子上的東西,大多數人筆記做得馬虎,所以我占了不少便宜。考試現場并不像高考那樣嚴格,既便是放開抄,也有很多人找不到答案。因此,我的一份卷子成了傳抄的范本。傳至我手里時,已經面目全非,只好重抄了一份。
而重抄的這一份,可能是令同事們羨慕的一份答卷。國慶過后,我從車間調離。
時間搖晃間,數年過去。2012年春風浩蕩時,我再次走到窯樓之下。此時,聽不見機器轟鳴,沒有灰塵漂浮,四周安靜得冰冷。抬頭仰望,天空明凈,日光刺眼。這是我最后一次徘徊于曾經勞動過的車間,誰都知道,我試圖依賴一生的公司,已經從企業名錄中被抹掉。
是的,我再次想起曾經奮斗過的同事們,恍惚看見那些崗位上晃動的身影。我——念叨著他們的姓名,卻不知道他們奔波在何方。這時,一切是那么的讓我眷戀,那么的讓我溫暖,而又那么的讓我心酸。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