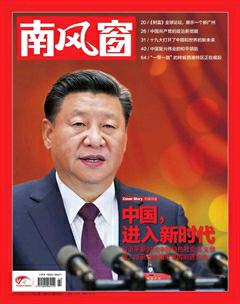不依靠工業(yè)化能否持續(xù)增長(zhǎng)?
丹尼·羅德里克
盡管全球各地的商品價(jià)格依然偏低,但世界上許多以此為生的最貧窮經(jīng)濟(jì)體卻都表現(xiàn)良好。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自2015年以來急劇減緩,但這只反映了當(dāng)?shù)?個(gè)最大型經(jīng)濟(jì)體—尼日利亞、安哥拉和南非的具體問題。埃塞俄比亞、科特迪瓦、坦桑尼亞、塞內(nèi)加爾、布基納法索和盧旺達(dá),預(yù)計(jì)今年將實(shí)現(xiàn)6%以上的增長(zhǎng)。而在亞洲,印度、緬甸、孟加拉、老撾、柬埔寨和越南也是如此。
這是個(gè)好消息,但有時(shí)也令人費(fèi)解。那些無需依賴高價(jià)自然資源而實(shí)現(xiàn)持續(xù)快速增長(zhǎng)的發(fā)展中經(jīng)濟(jì)體—跟大部分這些國(guó)家十多年來的發(fā)展模式相反—通常都是通過出口導(dǎo)向型工業(yè)化來實(shí)現(xiàn)的。而這些低收入的非洲國(guó)家并沒有實(shí)現(xiàn)多少工業(yè)化。撒哈拉以南低收入國(guó)家的制造業(yè)份額增長(zhǎng),大體上停滯不前,甚至在某些情況下有所下降。盡管“印度制造”已經(jīng)成了總理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的口頭禪之一,但這個(gè)國(guó)家卻沒有展現(xiàn)出什么快速工業(yè)化的跡象。
制造業(yè)之所以能成為低收入國(guó)家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強(qiáng)大助推力,原因有三:首先,從國(guó)外吸收技術(shù)并產(chǎn)生高效率的生產(chǎn)力相對(duì)容易。第二,制造業(yè)的工作并不需要太多的技能:農(nóng)民可以在工廠里變成生產(chǎn)工人,也無需多少額外培訓(xùn)投資。第三,制造業(yè)需求并不受國(guó)內(nèi)低收入水平的限制,通過出口,生產(chǎn)基本上可以無限增長(zhǎng)。
但情況一直在變化。現(xiàn)在有足夠的證據(jù)表明,近幾十年來制造業(yè)的技能密集程度日益提高。隨著全球化的推進(jìn),新進(jìn)入者非常難以打入世界制造業(yè)市場(chǎng)并復(fù)制以往那些亞洲制造業(yè)大國(guó)的經(jīng)驗(yàn)。除少數(shù)出口國(guó)之外,發(fā)展中經(jīng)濟(jì)體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提前的“去工業(yè)化”狀況。似乎這股助推力量和機(jī)會(huì),已經(jīng)從落后的國(guó)家身邊溜走了。
那么,我們究竟應(yīng)該如何看待某些世界上最貧窮國(guó)家新近的繁榮狀況?這些國(guó)家是否又發(fā)現(xiàn)了一套新的增長(zhǎng)模式?
在最近的研究中,美國(guó)國(guó)際食品政策研究所的刁新申、塔夫茨大學(xué)的瑪格麗特·麥克米蘭(Margaret McMillan)和筆者,共同研究了這批新的高增長(zhǎng)國(guó)家的增長(zhǎng)模式。我們的重點(diǎn)是這些國(guó)家所經(jīng)歷的結(jié)構(gòu)變化,并記錄了一些矛盾性的發(fā)現(xiàn)。
首先,盡管缺乏工業(yè)化,但埃塞俄比亞、馬拉維、塞內(nèi)加爾和坦桑尼亞等低收入國(guó)家近年的經(jīng)驗(yàn)表明,增長(zhǎng)促進(jìn)型的結(jié)構(gòu)性改革作用顯著。勞動(dòng)力從低生產(chǎn)率的農(nóng)業(yè)活動(dòng)轉(zhuǎn)移到了其他高生產(chǎn)率活動(dòng),不過,這些高生產(chǎn)率活動(dòng)主要是服務(wù)業(yè)而非制造業(yè)。
其次,這些國(guó)家的快速結(jié)構(gòu)性變化,大多都是以非農(nóng)部門勞動(dòng)生產(chǎn)率的負(fù)增長(zhǎng)為代價(jià)的。換句話說,盡管吸收新工作的服務(wù)業(yè)在初期產(chǎn)生了較高的生產(chǎn)率,但其邊際效應(yīng)也隨著行業(yè)擴(kuò)張而遞減。這一模式與經(jīng)典的東亞增長(zhǎng)經(jīng)驗(yàn)(如韓國(guó)和中國(guó))形成了鮮明對(duì)比,后者的結(jié)構(gòu)性變化和非農(nóng)業(yè)勞動(dòng)生產(chǎn)率的增長(zhǎng),都對(duì)總體增長(zhǎng)產(chǎn)生了巨大貢獻(xiàn)。
兩者之間的區(qū)別似乎是因?yàn)椋鼇磉@段高增長(zhǎng)時(shí)期的城市化和現(xiàn)代部門的擴(kuò)張,是由國(guó)內(nèi)需求驅(qū)動(dòng)而非以出口為導(dǎo)向的工業(yè)化。尤其非洲模式,顯然是由國(guó)外僑匯或者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率提升所產(chǎn)生的正面總需求的沖擊支撐起來的。
以埃塞俄比亞為例,灌溉、運(yùn)輸和電力方面的公共投資,顯著提高了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力和收入,并因此催生了促進(jìn)增長(zhǎng)的結(jié)構(gòu)性變化—因?yàn)樾枨髸?huì)外溢到非農(nóng)業(yè)部門。而非農(nóng)部門勞動(dòng)生產(chǎn)率的下降,則是作為上述情況的副產(chǎn)品而出現(xiàn),因?yàn)橘Y本回報(bào)率下降,生產(chǎn)效率較低的企業(yè)則收縮經(jīng)營(yíng)。
說這些,可不是要淡化農(nóng)業(yè)這個(gè)典型傳統(tǒng)部門實(shí)現(xiàn)快速生產(chǎn)率增長(zhǎng)的重要意義。我們的研究表明,農(nóng)業(yè)在非洲所扮演的關(guān)鍵作用不僅在其本身,還在于其作為增長(zhǎng)結(jié)構(gòu)變化的推動(dòng)力。對(duì)非傳統(tǒng)農(nóng)產(chǎn)品的多樣化嘗試,以及新生產(chǎn)技術(shù)的采用,都可以將農(nóng)業(yè)轉(zhuǎn)變?yōu)橐豁?xiàng)準(zhǔn)現(xiàn)代活動(dòng)。
但這個(gè)過程對(duì)整個(gè)國(guó)家經(jīng)濟(jì)的推動(dòng)程度有限。部分原因是農(nóng)產(chǎn)品需求的收入彈性較低,同時(shí)勞動(dòng)力從農(nóng)業(yè)部門流出也是發(fā)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結(jié)果。這些被釋放的勞動(dòng)力必須被現(xiàn)代活動(dòng)吸收。如果這些現(xiàn)代部門的生產(chǎn)力不增長(zhǎng),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就最終將陷入停滯。如果現(xiàn)代部門自身沒有經(jīng)歷過生產(chǎn)力的快速增長(zhǎng),那么目前這種結(jié)構(gòu)變化部分可以做出的貢獻(xiàn)就必然會(huì)出現(xiàn)自限性。
如果人力資本和治理水平能不斷提升,低收入非洲國(guó)家就可以在未來維持溫和的生產(chǎn)率增速,與富裕國(guó)家收入水平逐漸趨同似乎也可以實(shí)現(xiàn)。但有證據(jù)表明,最近這種由快速結(jié)構(gòu)性變化所帶來的增長(zhǎng)是一個(gè)例外,也可能無法長(zhǎng)久持續(xù)。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