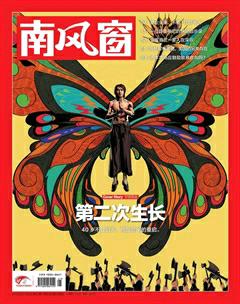安倍的政治豪賭會將日本帶向何方
王家曦
9月28日,日本眾議院第194屆臨時國會在召開伊始,就被首相安倍晉三宣布解散,朝野各黨進入事實上的選戰狀態。10月22日的眾議院選舉,將是日本自2014年12月以來再次舉行大選,也是5年來安倍晉三第三次迎戰大選。日本在野黨以“沒有大義的解散”為由批評政府。日本選民對安倍首相過于頻繁地提前大選也感到困惑,開始討論是否應當像英國那樣,用需要下議院2/3以上議員同意的條款來限制首相任意解散下議院的權力。
在本屆眾議院解散時,執政的自民、公明兩黨合計擁有322個議席,而安倍在10月選戰中給自己劃定了“自民·公明執政聯盟獲得465個議席中的過半數(233席)”的勝負分界線,表示如果達不到這一目標,自己將辭職。考慮到在野黨以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成立的“希望之黨”為中心聯合“圍剿”安倍的走向,以及英國、德國的執政黨在今年大選中均遭遇議席明顯縮水的意外,對安倍和自民黨來說,這次提前大選無疑是一場政治豪賭。
安倍“背水一戰”
此次提前大選,發生在安倍和自民黨遭遇連續的丑聞轟炸、支持率跌落谷底又緩慢回升的多事之秋,注定將是充滿不確定性的一戰。最新民調顯示,民進黨與“希望之黨”的民意支持率加起來,與自民黨旗鼓相當。
即使對安倍這樣精于算計的老成政客而言,2016年歲末至2017年伊始的日子也是十分難熬的。森友·加計學園丑聞、閣僚議員失言、東京都議會選舉慘敗等連串事件的集中爆發,在短期內給安倍和自民黨的執政聲譽以沉重打擊。據朝日電視臺的跟蹤式電話調查,截止到2017年6月,安倍內閣的支持率從55.3%的云端,跌落到29.2%的谷底;不支持率則從34.3%一路飆升至54.5%。
正當安倍為此一籌莫展之時,內外環境陡然間出現了有利于安倍和自民黨的變化。
首先是朝鮮核導威脅升級,給安倍一直主打、民意反彈激烈的新安保政策提供了合理性支撐。面對朝鮮中遠程導彈今年8月以來“兩次越頂”的直接威脅,日本國內對安倍內閣和自民黨的政策都有“回溫”的傾向。
其次,與自民黨穩定的“安倍司令塔”體制相比,日本國會幾個主要的在野黨貌合神離,各有內部隱憂。第一大在野黨民進黨,其華裔黨首蓮舫因為“改造民進黨不力”辭任后,保守的前外相前原誠司倉促當選新黨首。不久,前原誠司內定的干事長山尾志櫻里因出軌丑聞被迫辭職,使得前原的人事安排剛剛開局即面臨整體破局的壓力。
9月28日上午,前原召開記者會宣布,民進黨將與小池百合子3天前宣布建立的“希望之黨”合并。雖然完成了形式上的“在野大聯盟”,但鑒于目前瀕臨崩潰的黨務和小池百合子的政治勢力正隆,這一合并意味著民進黨已經失去了獨立性。前原自己承認:“導致一強多弱局面的責任在于民進黨。(民進黨)在創造大潮的過程中失去名字,是歷史的必然。”
至于代表傳統進步力量的日本共產黨、社民黨,在本屆眾議院中的席位不足10%,早已陷入邊緣化的境地。另據日經調查公司9月22-24日開展的電話調查,安倍內閣的支持率為50%,比8月下旬提高4個百分點。在這樣的民意預期下,安倍打響了選戰的“發令槍”,在逆風中發起一局政治豪賭。
安倍二次執政以來,心心念念的兩個方略是增稅和修憲。這兩個政策都因為涉及民眾的切身利益,而遭到持續的強烈反對。也正因如此,安倍稱這一次解散眾議院是“國難突破解散”,宣稱要將2019年消費稅增稅部分(稅率從8%增為10%)的用途,從償還國債變更為一半用于免費的托兒所和幼兒園,以鼓勵女性多生孩子,解決日本少子化的“國難”。
這一招其實是向小池百合子學的,因為后者在東京都的主要政績之一,就是減少女性生子的后顧之憂。當然,如果被視為東施效顰,民意壓力難擋,安倍也做好了與國會中自民黨團切割、引咎辭職的準備。
自民黨應能維持最大黨
目前來看,自民黨維持最大黨的局面不會發生根本變化。自1955年自由黨、民主黨和社會黨右翼合并成立自民黨以來,共有6位首相在執政時不屬于自民黨,其中真正與自民黨沒有瓜葛,不依賴自民黨或自民黨前要人支持而能執政的,只有一個,就是民主黨“末任首相”野田佳彥。
自民黨只在2009年至2012年民主黨執政期間屈居第二大黨,即便在1993年夏到1996年初的非自民黨人(細川護熙、羽田孜、村山富市)擔任首相時期,自民黨也還是最大黨,只不過面臨一些政黨的聯合壓制或掣肘。與之相對的是,其他政黨不斷重復著合流、分裂的戲碼,可謂是“你方唱罷我登場”。
2016年,為了整合在野黨力量以應對即將到來的選戰,第一大在野黨民主黨與從“日本維新會”改組而來的“維新黨”合流,組成了“民進黨”。時任自民黨干事長谷垣禎一當即表態稱,兩黨為選戰而倉促合流,缺少理念整合和利益協調,很難取得實質性成果,嗤之為“政治野合”。
一如谷垣所預料的那樣,民進黨在整合之后不僅未能在選戰中有所建樹,重新舉行的黨首選舉也充斥著各種權斗和口水。在“中間派”岡田克也支持下擔任黨首的蓮舫,作為東京都出身的國會參議員,因為民進黨在今年7月的東京都議會選舉中慘敗而引咎辭職。民進黨不得已再次倉促組織黨首選舉,曾任原民主黨黨首的前原誠司,于9月1日高票戰勝前首相菅直人時期的官房長官枝野幸男,擔任民進黨黨首。這次為了應對提前大選,前原誠司又提出并入“希望之黨”,但小池百合子表示不會“照單全收”。有人替民進黨抱不平說:“小池想要得到的,說到底就是民進黨的組織和錢。”

目前“希望之黨”在全國單獨提名的100名國會眾議員候選人,即便全部當選,也只不過在眾議院465個議席中占比21.5%,需要聯合多個在野黨組建大聯盟才有可能執政。而小池百合子日前已經聲明,自己雖然擔綱組黨,但目前沒有辭去東京都知事、重新競選眾議員的打算;最近她又和三個地方都知事會面,展現出向地方合作傾斜的策略。換句話說,她還沒有做好問鼎首相寶座的準備。
實際上,安倍在9月28日已對外表態稱:“貌合神離的政黨中孕育出的不是‘希望,而是‘混亂。”在野黨的聯合聲勢雖浩大,但成分復雜,包括自由派的社民黨、左翼的日本勞聯和保守派的小池勢力,還包括小澤一郎(現任自由黨聯合黨首)和前首相小泉的勢力(小池的“脫核電”政策就是與小泉商定的)。這些政治勢力目前也只有反對安倍政權這一個共同點,彼此之間的綱領、利益還存在許多無法融合甚至相互矛盾之處。
以往選戰的經驗表明,在倉促進行的選戰中,這些矛盾會隨著一些細節性的問題逐漸爆發,削弱在野黨聯盟的實質性意義(就如大阪府的橋下徹與東京都的石原慎太郎的“野合”,離“問鼎國政”相距遙遠)。而自民黨現階段仍尊安倍為“共主”,在內部團結和利益一致的層面上,較之在野黨聯盟有一定優勢;只要能充分發揮優勢,積極動員各級組織和自民黨的支持者,在選戰中對抗左支右絀的在野黨聯盟,自民黨仍然有較大贏面。
自民黨樹大根深,精于選戰,其與公明黨的執政聯盟堪稱國會中的“連橫”,這次與小池百合子等地方實力派所領軍的泛在野勢力“合縱”之間的對決,不論輸贏幾何必然精彩紛呈,我們不妨拭目以待。
日本將被帶向何方?
二次就職以來,安倍終結了日本“十年九相”的首相走馬燈,創立了國家安全保障委員會,推動出臺了新安保法,改變了新世紀以來日本政治的混亂狀況。變與不變往往互相依存,此次安倍提前大選增加了新首相人選的變數,但日本的內政外交應可維持兩方面的“不變”:
對內,新一屆國會的政策方針和權力結構不會發生根本變化。安倍內閣此前推動的、以量化寬松為主的“安倍經濟學”對日本經濟產生了一定的提振效果,未來以此為基礎形成的一系列經濟政策,在新一屆國會中仍有較大可能得到完整執行。
與安倍相比,曾做過防衛大臣的小池百合子同樣有深厚的保守派底色,甚至直到數月前她還隸屬于自民黨(因一年前擅自參選東京都知事,小池背了個相當于“留黨察看”的處分)。如果像外界所預料的那樣,小池勢力強勢入主國會,民進黨等之前反對修憲的在野勢力將被實質性削弱,這等于為安倍和自民黨推動修憲減小了阻力。
有專家指出,從“希望之黨”主要發起人陣容看,可以說它比自民黨更保守、更右傾、更具排外色彩。所以,9月28日晚安倍首次參加中國駐日本大使館舉行的中國國慶招待會(亦適逢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被認為有替大選拉票考量,卻也說明中日兩國正在努力改善關系,不希望再生波折。
另一方面,安倍打造了一個以首相為中心的“首相-執政黨”新權力架構。區別于以往“強國會,弱首相;強政黨,弱政客”的制衡性權力架構,新權力架構下,首相在行政權、人事權之外掌握了新的制度化權力,首相不再是個體的人,而成為整個權力機構的中樞組成部分,為后續的繼任者實現權力意圖創造了條件。由于日本的首相往往出自議會中的第一大黨,因此無論議會中的黨派權力分布發生何種變化,由安倍重新確認過的、國會與首相的權力分配也不會發生根本性的改變。
對外,美日同盟的性質不會發生根本變化。戰后70余年來,美日同盟始終是美日兩國關系發展中唯一不變的主軸和結構性“常量”。即使是在日本國內左翼反戰運動聲勢最為浩大的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美日關系仍然圍繞著安保條約的更新而穩步推進。此后的幾十年中,無論是日本的戰后和平主義、議會斗爭、群眾運動還是謀求防衛自主化,即使日本和美國在局部利益上發生沖突和矛盾,也沒有對美日同盟構成實質性的影響。
特朗普執政以前,美國就多次表示希望日本增加軍費、積極參與美國主導的地區安全事務,日本政府都因國內法律和民意限制,而采取了保留態度。特朗普上任之后強調“美國優先”,與安倍的“安全自主”既定方針一拍即合。特朗普將于11月初對日本進行任內的首次訪問,這次訪日很可能提出其具體的亞太政策構想,所以安倍首相選擇在10月下旬結束選舉工作,以便向特朗普總統展示自身政權的穩定性。
其實,就算大選后自民黨、公明黨執政聯盟在眾院議席未能過半,導致安倍“愿賭服輸”辭職下臺,其繼任者也不會動搖日美同盟。因為在捍衛美國主導、日本獲益的亞太政治經濟秩序方面,日美的戰略目標和戰略利益從宏觀層面趨于一致。而無論是前防相小池百合子還是前外相前原誠司,都是主張美日親善的外交保守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