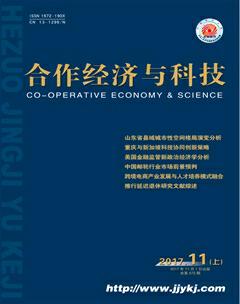馬克思交往理論在當代中國語境中的理性審視
李聯華
[提要]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交往已成為當代人類生存與發展的普遍方式,交往理論研究愈來愈成為哲學理論界關注的焦點。本文立足于馬克思主義基本立場,比較和分析馬克思和哈貝馬斯關于交往理論的相同與不同之處,指出在當代中國語境中,我們應重新審視傳統的對馬克思交往理論二元理解的方法,還原馬克思交往理論曾被遮蔽的現代意蘊。
關鍵詞:馬克思交往理論;當代中國語境;理性審視
中圖分類號:C91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7年7月18日
當代中國主流哲學思維范式的轉換、馬克思交往理論的重新界定,以及當代中國社會改革與實踐中出現的普遍交往問題構成了“當代中國語境”的三維結構。思維范式的轉換說明當代中國和知識界精英在理論思維層次已經有了一個與現代西方哲學中的交往理論特別是哈貝馬斯交往行動理論對話的平臺。馬克思主義是我黨的指導思想,馬克思交往理論的科學定位不僅是理論思維與思維范式轉換的需要,而且對當代中國社會具有重新啟蒙的指導意義。而當代中國社會出現的普遍交往問題的思考與解決理應是本文立意的出發點和歸宿點。因此,“當代中國語境”的三維結構昭示了對交往行動理論的理性審視和對當代中國社會出現的普遍交往問題的深深憂慮,同時也蘊含了解決這些交往問題的理論與實際的祈盼。
隨著全球化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以及人對外部自然的改造不斷理性化、合理化,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方式卻不斷遭到扭曲,導致人際交往不合理,非理性的程度日益加劇。人的現實交往困境使交往成為具有鮮明時代特征的哲學課題。進入21世紀后,人類始終處于自相矛盾的窘境:一方面是科學技術、物質財富和人的本質力量的不斷增長;另一方面則是人的許多創造物作為異已的力量對人的統治不斷加劇。因而,在交往實踐中,只要交往雙方或各方不能以自由、平等、自然、全面發展的主體而存在,主體—主體的關系就會在某種意義上降格為主體—客體關系或物與物的關系。從而使交往走向異化。這不是晚期資本主義社會所獨有的,而是迅速走向現代化的中國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加速度的方式出現的交往民化問題。實質上,這是現代社會和現代人所面臨的生存問題。揚棄交往異化的根本途徑是消除物對人的統治。而要消除物對人的統治,卻是一方面要通過大力發展科學技術極大地豐富物,另一方面要在人與人之間完善主體—主體關系,清退系統對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并且使二者處于均態勢,實現總體人的自由、人的本質的實現和人的全面發展。也就是現在當代中國語境中,哈貝馬斯和馬克思的交往理論具有極大交融的可能性。一個結語式的道路是:以哲學思維范式轉換為契機,以哈貝馬斯的交往行動理論為借鑒,實現馬克思主義交往理論在當代中國的理論創新與實踐取向,并且以馬克思主義交往理論為指導,解決當代中國社會出現的普遍交往問題。這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有可能的。
對于馬克思交往理論的重新界定目前國內學界意見并不一致。筆者認為,馬克思交往理論定位在交往實踐觀,是較為恰當的。概括起來,交往實踐觀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內容:
交往是人的社會性的存在方式,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活動是社會實踐總體的有機組成部分。社會交往(包括物質交往和精神交往)影響著人類的生產活動。文化中凝結的人的社會特性,正是從交往活動的媒介作用中形成和發展的;物質交往使單個人勞動成為社會勞動的一部分,使個人的精神和天賦的特性同時采取一種社會特性的形態。而且,交往又使個人能以特殊活動為媒介而享受人類總體活動的一般成果。所以,交往是個人創造與發展社會文化以及社會文化塑造與發展個人的基本形式之一;交往創造了一種人類積累、交換、傳遞、繼承和發展自己文化的特殊的社會進化機制;人們以文化的、觀念的方式把握外部世界,是通過精神交往來實現的。精神交往手段——語言符號,既是交往實踐的產物,又是人類文化的重要象征,它本身是和交往實踐具有根本上的同構性。
因此,馬克思交往理論可以定位在有別于傳統實踐觀的交往實踐觀上。傳統意義上的實踐觀是由“主體—客體”的要求構成的,這種兩極框架或模式存在明顯的缺陷:它撇開了實踐主體與主體之間的物質交往關系或社會聯系,使實踐中的主體、結構和關系單一化,并將實踐活動自覺不自覺地視為沒有“主體—主體”關系介入的片面的“主體—客體”相互作用過程。針對這些缺陷,必須突破對馬克思主義實踐觀的狹義理解。事實上,交往實踐是諸主體間通過改造相互聯系的中介客體而結成社會關系的物質活動。從其結構來說,交往實踐觀超越或揚棄了“主體—客體”模式。它將交往納入實踐,將“主體—客體”與“主體—主體”統一于實踐,構成了“主體—客體—主體”的相關性模式;從而深化對傳統實踐觀在內容和結構上變革,克服以往哲學在實踐觀上的主客二元對立。這樣,馬克思交往理論得到了全新界定,獲得了當代的意義并與哈貝馬斯的交往行動理論在主體間方面有了內在關聯。
第一,馬克思論述交往與物質生產之間的關系,認為人類的生產是以個人彼此之間的交往為前提的,交往形式是由生產決定的。通過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人們以一定的方式結合起來共同勞作并相互交換其活動,而交往本身亦成為人的需要和能力的源泉,促成生產者在社會分工基礎上的合作,各生產者之間內在結合力的形成和增強正是在交往活動中形成的。因此,交往和生產一起構成了社會實踐活動中互為前提、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
第二,馬克思探討交往形態歷史演進與人的全面發展的關系。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劃分了人類交往發展的歷史形態。即以人的信賴關系或個人之間的統治服從關系為基礎的最初交往形態;建立在交換價值基礎上的一切勞動產品、能力和活動和私人交換,也就是“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第三階段是“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
第三,馬克思闡述社會分工的演進與交往方式、交往關系的變化是相輔相成的。分工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標志,這一方面使人們彼此分離局限于某一行業或領域,另一方面又使他們之間的相互聯系、相互交往更加迫切和必要。隨著分工的發展,交往形式不斷變化,交往范圍也不斷擴大。特別是大工業的出現,使分工更加專業化、細微化,這既導致人的現實生存狀況的嚴重變化,又使人的交往形式更加多樣化、交往關系更加復雜化。隨著廣袤的世界市場的建立,使普遍性的世界交往迅速發展起來,進而促進人類社會演進和社會結構的變革。
第四,馬克思區分物質交往和精神交往,認為精神交往是從物質交往中分化出來的。物質交往決定精神交往。而且,馬克思還肯定了語言在交往活動中的媒介作用,認為語言行為作為一種重要的交往行為,乃是由實踐的需要,尤其是由物質生產的需要決定的。雖然馬克思未能像哈貝馬斯那樣對語言的作用進行分析哲學式的闡述,但是我們可以說,馬克思、恩格斯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德意志意識形態》等著作以交往問題的重要論述,都是對哈貝馬斯交往行動理論產生重大影響的思想資源。
總之,交往實踐觀認為,“交往”是理解馬克思關于生產勞動、人的本質與發展、社會結構及其演進等一系列基本理論的關鍵性范疇,它在唯物史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建基作用。可以這樣說,唯物史觀從物質生產活動與物質交往活動及其關系中,牽引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范疇,豚其辯證關系原理,又從精神生產活動與精神交往活動中,牽引出社會政治上層建筑與思想上層建筑范疇,并通過精神生產、精神交往與物質生產、物質交往的內在聯系,科學地揭示了上層建筑與社會經濟基礎之間的辯證關系。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筑決定作用不是直接現實的,而是通過一系列中間環節實現的,其中包括交往和交往關系作用。但是,在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教科書中,由于缺少交往和交往環節,所以不能科學地說明人們社會關系(包括生產關系)形成的內在機制,也導致了對社會結構的形成及其相互之間內在聯系的一種過于簡單的理解和闡釋。這也是哈貝馬斯批判歷史唯物主義的勞動實踐理論缺少“交往”維度的緣由之一。因此,馬克思交往理論在當代中國語境中的理性審視,可以彌補唯物史觀傳統意義上的交往緯度的缺失。
主要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人民出版社,1979(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