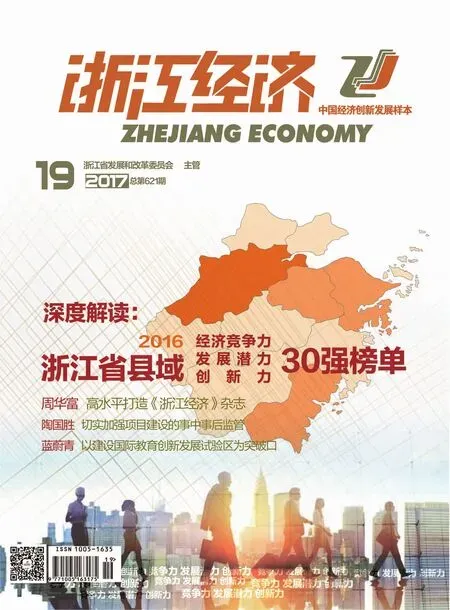浙江金融改革發(fā)展必須聚焦五大問(wèn)題
□李金珊 沈楠
浙江金融改革發(fā)展必須聚焦五大問(wèn)題
□李金珊 沈楠
金融活,經(jīng)濟(jì)活;金融穩(wěn),經(jīng)濟(jì)穩(wěn)。從浙江經(jīng)濟(jì)及金融改革發(fā)展大局看,必須著力解決好當(dāng)前金融發(fā)展中的突出問(wèn)題,消除風(fēng)險(xiǎn)隱患,促進(jìn)經(jīng)濟(jì)和金融良性循環(huán)、健康發(fā)展
近年來(lái),浙江積極推進(jìn)金融改革發(fā)展,取得了許多突破性進(jìn)展。但在金融運(yùn)行中也存在不少問(wèn)題,突出表現(xiàn)為浙江金融業(yè)增加值在全國(guó)占比從2010年的8.9%下降到2016年的4.9%,同期江蘇從8.2%提高到9.8%。我們分析,浙江金融業(yè)增長(zhǎng)速度的持續(xù)下滑,主要被較高的杠桿率、不良率以及非法集資、政府債務(wù)、金融空轉(zhuǎn)等問(wèn)題拖累。中央金融工作會(huì)議強(qiáng)調(diào),維護(hù)金融安全是關(guān)系我國(guó)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發(fā)展全局的一件帶有戰(zhàn)略性、根本性的大事。金融活,經(jīng)濟(jì)活;金融穩(wěn),經(jīng)濟(jì)穩(wěn)。從浙江經(jīng)濟(jì)及金融改革發(fā)展大局看,必須著力解決好當(dāng)前金融發(fā)展中的五個(gè)突出問(wèn)題,消除風(fēng)險(xiǎn)隱患,促進(jìn)經(jīng)濟(jì)和金融良性循環(huán)、健康發(fā)展。
控制好杠桿率
去杠桿是供給側(cè)結(jié)構(gòu)性改革的一個(gè)重要任務(wù)。對(duì)于實(shí)體經(jīng)濟(jì)的杠桿率,一般采用“債務(wù)余額/GDP”這一公式或指標(biāo)進(jìn)行衡量。如居民部門(mén)杠桿率為居民部門(mén)貸款余額/GDP,政府部門(mén)杠桿率為(國(guó)債+政府支持機(jī)構(gòu)債+地方政府負(fù)有償還責(zé)任的債務(wù)+地方政府或有債務(wù))/GDP,非金融企業(yè)部門(mén)杠桿率為(銀行信貸+企業(yè)債券+信托貸款+委托貸款+未貼現(xiàn)銀行承兌匯票-城投企業(yè)債務(wù)余額)/GDP。對(duì)于區(qū)域經(jīng)濟(jì)而言,最簡(jiǎn)便的杠桿率計(jì)算公式是“各項(xiàng)貸款余額/GDP”。
按照這一公式,我們發(fā)現(xiàn),2016年浙江杠桿率為175.98%,高于全國(guó)平均水平,也高于GDP3萬(wàn)元以上的各省份(參見(jiàn)表1)。

表1 2016年部分省份杠桿率
浙江經(jīng)濟(jì)高杠桿的形成主要在2000年至2005年期間。當(dāng)時(shí)浙江銀行業(yè)利潤(rùn)高且風(fēng)險(xiǎn)低,四大行和12家股份制銀行涌入浙江開(kāi)設(shè)分支機(jī)構(gòu),信貸投放力度空前,導(dǎo)致浙江經(jīng)濟(jì)杠桿率從1995年的60%,提高到2000年的90%、2005年的130%,同期全國(guó)為70%、110%和114%。
高杠桿必然包含高風(fēng)險(xiǎn),但控制好區(qū)域經(jīng)濟(jì)杠桿率卻是一個(gè)政策難題。假設(shè)未來(lái)五年全國(guó)各項(xiàng)貸款余額與GDP的比率穩(wěn)定在150%左右,假設(shè)未來(lái)五年浙江GDP年均增長(zhǎng)7%、五年后達(dá)到7萬(wàn)億元左右,假設(shè)浙江的杠桿率五年后也要控制在150%左右,則未來(lái)五年浙江貸款余額的年均增長(zhǎng)率只能在4%左右。這意味著浙江未來(lái)五年要過(guò)緊日子,同時(shí)貸款余額年均增長(zhǎng)4%也難以支撐經(jīng)濟(jì)年均增長(zhǎng)7%。
為此,我們建議:第一,長(zhǎng)期保持貸款余額增長(zhǎng)略低于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的態(tài)勢(shì),以10年乃至更長(zhǎng)的時(shí)間來(lái)調(diào)整好杠桿率。第二,積極支持有條件的企業(yè)在境內(nèi)外上市,大力發(fā)展直接融資,加快改變對(duì)間接融資的過(guò)多依賴(lài)。第三,積極培育發(fā)展地方資本市場(chǎng),力爭(zhēng)五年后在省產(chǎn)權(quán)交易中心掛牌的科技型中小企業(yè)達(dá)到3000家以上。
化解好不良貸款
根據(jù)《中國(guó)金融穩(wěn)定報(bào)告(2017)》,2016年末全國(guó)銀行業(yè)金融機(jī)構(gòu)不良貸款余額2.19萬(wàn)億元,不良貸款率為1.91%;關(guān)注類(lèi)貸款余額5.28萬(wàn)億元,關(guān)注類(lèi)貸款率為4.6%;逾期貸款3.24萬(wàn)億元,在貸款余額中占比2.87%;實(shí)現(xiàn)凈利潤(rùn)2.07萬(wàn)億元,資產(chǎn)利潤(rùn)率0.96%,資本利潤(rùn)率12.61%。如果將2.19萬(wàn)億元不良貸款以三折打包出售(新浪財(cái)經(jīng),2016),估計(jì)全國(guó)銀行業(yè)金融機(jī)構(gòu)凈利潤(rùn)不超過(guò)6000億元,資產(chǎn)利潤(rùn)率不超過(guò)0.3%,資本利潤(rùn)率不超過(guò)4%。
浙江的情況更為嚴(yán)重。根據(jù)浙江銀監(jiān)局的統(tǒng)計(jì),2016年末,全省銀行業(yè)金融機(jī)構(gòu)本外幣不良貸款余額1777億元,不良貸款率2.17%;實(shí)現(xiàn)利潤(rùn)699億元。如果將不良貸款也以三折打包出售,浙江銀行業(yè)金融機(jī)構(gòu)的利潤(rùn)為負(fù)500億元。
事實(shí)上,浙江的不良貸款問(wèn)題已經(jīng)持續(xù)了五六年。2011年,浙江不良貸款余額387億元、不良率0.91%,2012年增至970億元和1.68%,2013年再增至1035億元和1.84%,2014年至1397億元和1.96%,2015年為1808億元和2.37%,2016年“雙降”至1777億元和2.17%,不良貸款總量多年居全國(guó)第一。期間,浙江銀行業(yè)累計(jì)處置不良貸款超過(guò)7000億元,其中核銷(xiāo)超過(guò)3500億元;相應(yīng)地,銀行業(yè)利潤(rùn)從2011年的1383億元下降至2012年的1198億元、2013年的1144億元、2014年的875億元、2015年的585億元和2016年的699億元,五年利潤(rùn)損失超過(guò)2400億元,加上核銷(xiāo)損失,浙江各銀行損失合計(jì)大致在6000億元左右。實(shí)際損失還會(huì)更多。截止到2017年6月末,浙江除1712億元不良貸款外,還有3250億元關(guān)注類(lèi)貸款、2587億元逾期貸款。
大量的不良貸款、關(guān)注類(lèi)貸款、逾期貸款,源于銀行多年的粗放經(jīng)營(yíng)和企業(yè)的高負(fù)債。但對(duì)浙江影響最大的是擔(dān)保鏈。擔(dān)保鏈本質(zhì)上是“要死一起死”的融資機(jī)制。假設(shè)1家企業(yè)的貸款平均有5家企業(yè)為其擔(dān)保,這5家企業(yè)的貸款各自又有5家企業(yè)為其擔(dān)保,到第三圈擔(dān)保鏈企業(yè)已經(jīng)是5的3次方。錯(cuò)綜復(fù)雜的擔(dān)保鏈剪不斷、理還亂。2008年貸款80多億元的紹興華聯(lián)三鑫石化資金鏈斷裂時(shí),曾使數(shù)百家紹興企業(yè)陷入擔(dān)保鏈危機(jī)。1712億元不良貸款若處置不當(dāng),可能拖累整個(gè)浙江。
巨額不良貸款是浙江經(jīng)濟(jì)機(jī)體中的毒瘤,必須去之而后快。我們的建議是,首先要為企業(yè)的總負(fù)債確定一個(gè)上限。擔(dān)保作為或有債務(wù),在銀行融資擔(dān)保時(shí)要計(jì)入總負(fù)債,資產(chǎn)總負(fù)債率高于80%或100%的企業(yè),既不予貸款,也不得為人擔(dān)保,從而在逐步斬?cái)鄵?dān)保鏈的同時(shí)控制好企業(yè)的杠桿率。其次要明確不良貸款的客觀標(biāo)準(zhǔn)。不良貸款不能由銀行或銀監(jiān)部門(mén)自定義,防止銀行在“不良”與“關(guān)注”之間騰挪,導(dǎo)致金融風(fēng)險(xiǎn)失真。我們的建議是將“逾期三個(gè)月”作為不良貸款的硬標(biāo)準(zhǔn)。第三要強(qiáng)化逾期清盤(pán)制度。貸款逾期三個(gè)月或五個(gè)月銀行必須訴諸法律,該破產(chǎn)的破產(chǎn)、該重組的重組,否則銀行要負(fù)資產(chǎn)損失責(zé)任。第四要建立銀行處置不良貸款的硬約束。處置不良貸款必然給銀行帶來(lái)?yè)p失,許多銀行為此“以時(shí)間換空間”,導(dǎo)致不良率居高不下。為此建議給各銀行確定一個(gè)不良率上限,如今年1.8%、明年1.6%、后年1.4%、2020年降至1.2%或1.0%等,超過(guò)上限的,即下調(diào)銀行的信用等級(jí)。
企業(yè)信用等級(jí)評(píng)定目前已比較普遍,具體有AAA級(jí)、AA級(jí)、A級(jí)、B級(jí)、C級(jí)五個(gè)等級(jí),但政府、企業(yè)、社會(huì)對(duì)銀行沒(méi)有信用等級(jí)評(píng)定。建議浙江先行先試,對(duì)在浙各銀行開(kāi)展信用等級(jí)評(píng)定,以此約束銀行的不良行為。
規(guī)范好民間借貸
浙江是民營(yíng)經(jīng)濟(jì)大省,也是民間資金大省、民間借貸大省。截止到2017年6月末,全省城鄉(xiāng)居民存款超過(guò)4萬(wàn)億元,比非金融企業(yè)存款多出6000億元,比財(cái)政及機(jī)關(guān)團(tuán)體存款多出2.2萬(wàn)億元;3.5萬(wàn)億非金融企業(yè)存款中,屬于民營(yíng)企業(yè)至少2萬(wàn)億元。依次推算,浙江以貨幣資金存在的民間資金超過(guò)6萬(wàn)億元。
大量的民間資金、民營(yíng)企業(yè)以及事實(shí)上存在的“融資難”,必然導(dǎo)致大量的民間借貸以及民間借貸糾紛的多發(fā)頻發(fā)。根據(jù)浙江省高級(jí)人民法院的統(tǒng)計(jì),從2012年至2015年,浙江法院民間借貸糾紛案收案數(shù)量每年超過(guò)10萬(wàn)件;2012年,溫州法院民間借貸糾紛案收案19406件,涉案標(biāo)的217.24億元。按此推算,浙江每年的民間借貸糾紛涉案標(biāo)的有千億規(guī)模。
民間借貸以及由此產(chǎn)生的民間借貸糾紛是民營(yíng)經(jīng)濟(jì)的伴生物,是金融改革發(fā)展滯后的必然現(xiàn)象,無(wú)需大驚小怪。但其中的非法集資則是金融風(fēng)險(xiǎn)隱患。2011年,浙江非法集資案160多起,涉案金額超過(guò)280億元。2016年,全省涉嫌非法集資案件400多起,涉案金額超過(guò)300億元。幾百億的涉案金額數(shù)額不大,但社會(huì)影響很大、社會(huì)危害很大。
打擊非法集資,規(guī)范民間借貸是基礎(chǔ)。2015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發(fā)布《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wèn)題的規(guī)定》,明確了“24%”和“36%”兩條“法線(xiàn)”,但沒(méi)有劃定以商業(yè)活動(dòng)為目的民間借貸與非法集資之間的紅線(xiàn)。
我們認(rèn)為,這條紅線(xiàn)應(yīng)包括三個(gè)方面的硬性規(guī)定:第一,借款人一次不得向30人或150人以上借款,超過(guò)30人或150人的,即涉嫌非法集資。第二,借款人所借款項(xiàng)不得超過(guò)其自有合法財(cái)產(chǎn)的兩倍或三倍,超過(guò)兩倍或三倍,即涉嫌非法集資。第三,民間借貸必須在民間借貸服務(wù)中心登記備案,未經(jīng)登記備案即涉嫌非法集資。
民間借貸服務(wù)中心是溫州金融改革的一項(xiàng)制度創(chuàng)新。截至2016年4月,溫州已設(shè)立7家民間借貸登記服務(wù)中心和5個(gè)民間借貸備案點(diǎn);通過(guò)民間借貸登記服務(wù)中心備案登記的25177筆民間借貸,總金額已達(dá)326.5億元。截止到2016年底,全省已有民間借貸服務(wù)中心41家,完全有條件在全省制定實(shí)施上述三條規(guī)定,建議省有關(guān)部門(mén)加快研究,以地方法規(guī)或行政規(guī)章出臺(tái),防止民間借貸轉(zhuǎn)化為非法集資。
管理好政府債務(wù)
政府債務(wù)本質(zhì)上是財(cái)政問(wèn)題而不是金融問(wèn)題,但如果政府債務(wù)也面臨還本付息難題,財(cái)政問(wèn)題就會(huì)演變?yōu)榻鹑趩?wèn)題,影響金融改革發(fā)展穩(wěn)定。
我國(guó)目前政府債務(wù)風(fēng)險(xiǎn)總體可控。根據(jù)財(cái)政部的消息(2016),截至2015年末,納入預(yù)算管理的中央政府債務(wù)10.66萬(wàn)億元、地方政府債務(wù)16萬(wàn)億元,兩項(xiàng)合計(jì),全國(guó)政府債務(wù)26.66萬(wàn)億元,占GDP的比重為39.4%。加上地方政府或有債務(wù),政府債務(wù)占GDP的比例在41.5%左右。再加上地方融資平臺(tái),政府債務(wù)的GDP占比為56.8%。
一些省市的政府債務(wù)風(fēng)險(xiǎn)比較突出。2015年末,地方政府債務(wù)率超過(guò)100%的有貴州、遼寧、云南、內(nèi)蒙古四省區(qū),分別為189%、157%、121%和106%。債務(wù)率在90%-100%之間的有浙江、陜西兩省。2015年,浙江地方政府債務(wù)為9188.3億元,政府債務(wù)率為92.9%,低于100%的國(guó)際通行警戒值。
浙江地方政府債務(wù)增長(zhǎng)很快。2008年,浙江地方政府債務(wù)2792億元,2009年至2015年年均增長(zhǎng)18.5%,高出GDP增長(zhǎng)約10個(gè)百分點(diǎn)。如果不加管控,將很快超過(guò)國(guó)際通行警戒線(xiàn)。
超過(guò)國(guó)際通行警戒線(xiàn)只是一個(gè)概念。真正的問(wèn)題一是政府貸款對(duì)企業(yè)特別是小微企業(yè)可能形成擠壓。根據(jù)省工商局的報(bào)告,截止到2016年末,全省在冊(cè)市場(chǎng)主體528.6萬(wàn)戶(hù),其中企業(yè)168.4萬(wàn)戶(hù)、個(gè)體工商戶(hù)360.2萬(wàn)戶(hù);浙江銀監(jiān)局報(bào)告,截止到2016年末,浙江轄內(nèi)小微企業(yè)貸款戶(hù)數(shù)為144.78萬(wàn)戶(hù),貸款余額2.34萬(wàn)億元。按照小微企業(yè)和個(gè)體工商戶(hù)占浙江省市場(chǎng)主體總量97%推算,至少有70%的小微企業(yè)和個(gè)體工商戶(hù)未能獲得銀行的陽(yáng)光雨露。
二是部分縣市、鄉(xiāng)鎮(zhèn)面臨較大的政府債務(wù)風(fēng)險(xiǎn)。根據(jù)浙江省審計(jì)廳的報(bào)告(2014),截至2012年底,全省有2個(gè)市級(jí)、18個(gè)縣級(jí)、97個(gè)鄉(xiāng)鎮(zhèn)政府負(fù)有償還責(zé)任債務(wù)的債務(wù)率超過(guò)100%;其中,有6個(gè)縣級(jí)、29個(gè)鄉(xiāng)鎮(zhèn)2012年政府負(fù)有償還責(zé)任債務(wù)的借新還舊率(舉借新債償還的債務(wù)本金占償還債務(wù)本金總額的比重)超過(guò)20%。
三是弱化了政府在化解企業(yè)資金鏈、擔(dān)保鏈問(wèn)題中的作用。企業(yè)發(fā)生貸款逾期、陷入資金鏈困境,傳統(tǒng)的做法是政府出面協(xié)調(diào)銀行和企業(yè)。如果協(xié)調(diào)者自身也面臨付息還本難題,前述的“逾期清盤(pán)”等舉措只能是不可普遍實(shí)施的原則。
為此建議,一要對(duì)政府債務(wù)再界定。政府債務(wù)應(yīng)該是財(cái)政負(fù)有還本付息責(zé)任的債務(wù)。比如,國(guó)有全資或控股的高速公路,貸款100億元,舉債主體和償還責(zé)任主體是高速公路公司,即使連年虧損、財(cái)政每年給予6個(gè)億的補(bǔ)貼予以還息,政府的償還責(zé)任不是100億元,而是6個(gè)億,屬于政府承擔(dān)一定救助責(zé)任的債務(wù);城投公司為市區(qū)道路建設(shè)舉債100億元,因?yàn)槭袇^(qū)道路沒(méi)有收益,所借款項(xiàng)只能財(cái)政還本付息,100億元即是政府債務(wù)。
二要明確地方政府債務(wù)的舉債主體。目前,浙江地方債務(wù)的舉債主體包括融資平臺(tái)、國(guó)有企業(yè)、事業(yè)單位、政府部門(mén)和機(jī)構(gòu),分別占地方政府債務(wù)的50%、30%、12%和8%左右。地方政府債務(wù)的舉債主體必須是省政府批準(zhǔn)的、列入當(dāng)?shù)刎?cái)政預(yù)算的融資平臺(tái)和政策性國(guó)有企業(yè),其他單位不得作為舉債主體。
三要明確政府舉債的法律程序或行政程序。在科學(xué)界定政府債務(wù)、明確舉債主體后,各市縣政府的新增債務(wù)必須報(bào)省政府備案;超過(guò)警戒線(xiàn)的市縣政府,要報(bào)省政府批準(zhǔn)同意。
服務(wù)好實(shí)體經(jīng)濟(jì)
金融改革發(fā)展必須堅(jiān)持以服務(wù)實(shí)體經(jīng)濟(jì)為本的方針。但現(xiàn)實(shí)中金融空轉(zhuǎn)、資金空轉(zhuǎn)很?chē)?yán)重。《人民日?qǐng)?bào)》的調(diào)查報(bào)告顯示(2017),目前不少銀行資金,有的輾轉(zhuǎn)進(jìn)入資本市場(chǎng)、債券市場(chǎng),在金融體系內(nèi)自我循環(huán);有的通過(guò)理財(cái)信托等進(jìn)行違規(guī)或不必要的資金通道業(yè)務(wù),層層轉(zhuǎn)手、拉長(zhǎng)鏈條,繞道進(jìn)入房地產(chǎn)市場(chǎng)或抬高實(shí)體企業(yè)融資成本。在這個(gè)過(guò)程中,銀行表外業(yè)務(wù)量瘋長(zhǎng)。
表外業(yè)務(wù)不等同于資金空轉(zhuǎn),但資金空轉(zhuǎn)必然要借道表外業(yè)務(wù)。根據(jù)央行的《中國(guó)金融穩(wěn)定報(bào)告(2013)》,截至2012年末,銀行業(yè)金融機(jī)構(gòu)表外業(yè)務(wù)(含委托貸款和委托投資)余額48.65萬(wàn)億元,同期銀行業(yè)金融機(jī)構(gòu)貸款余額為68.59萬(wàn)億元,表外業(yè)務(wù)總量與貸款余額的比率為70.9%。4年后,還是《中國(guó)金融穩(wěn)定報(bào)告(2017)》,截止到2016年末,銀行業(yè)金融機(jī)構(gòu)表外業(yè)務(wù)(含委托貸款和委托投資)余額235.52萬(wàn)億元,同期銀行業(yè)金融機(jī)構(gòu)貸款余額為106.6萬(wàn)億元,表外業(yè)務(wù)總量與貸款余額的比率為220.9%。
浙江銀行業(yè)金融機(jī)構(gòu)表外業(yè)務(wù)發(fā)展相對(duì)滯后。2013年,主要表外業(yè)務(wù)余額2.62萬(wàn)億元,與貸款余額的比率為40.1%,2016年主要表外業(yè)務(wù)余額9.90萬(wàn)億元,與貸款余額的比率為121.0%。
表外業(yè)務(wù)不是洪水猛獸。商業(yè)銀行在發(fā)展過(guò)程中,從傳統(tǒng)業(yè)務(wù)向表外業(yè)務(wù)拓展是一種趨勢(shì)。瑞士銀行的表外業(yè)務(wù)利潤(rùn)占比達(dá)到70%左右,德國(guó)銀行的這一比例通常也在60%以上。但五六年里表外業(yè)務(wù)保持年均50%的瘋狂增長(zhǎng),背后一定有對(duì)等的風(fēng)險(xiǎn),尤其是銀行的信用風(fēng)險(xiǎn)、或有風(fēng)險(xiǎn)。商業(yè)銀行以自己的信用風(fēng)險(xiǎn)謀取利潤(rùn)不關(guān)浙江的事,但抬高浙江企業(yè)的融資成本浙江不能坐視不管。袁家軍省長(zhǎng)最近指出,2016年全省銀行加權(quán)平均貸款利率為5.9%,比全國(guó)平均水平高出0.46個(gè)百分點(diǎn),今年6月末雖然下降到5.49%,仍然高于全國(guó)平均水平。浙江還要高度關(guān)注并嚴(yán)加管控的是“A銀行請(qǐng)B企業(yè)貸款5000萬(wàn),再請(qǐng)B企業(yè)向自己購(gòu)買(mǎi)5000萬(wàn)的理財(cái)產(chǎn)品,然后將5000萬(wàn)以委托貸款形式貸給C企業(yè),A銀行與B企業(yè)分享其間被抬高點(diǎn)利率”等資金游戲。
為此建議,對(duì)各銀行的加權(quán)平均貸款利率,要求銀行每季度自查上報(bào);對(duì)ABC資金游戲,一經(jīng)發(fā)現(xiàn),即在銀行信用網(wǎng)上予以不良信用記錄。
作者:李金珊,浙江大學(xué)教授、博導(dǎo);沈楠,浙江大學(xué)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