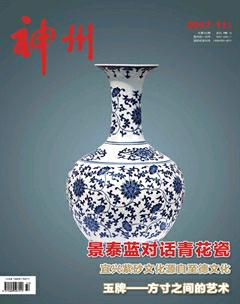市場經(jīng)濟與意義世界的式微
摘要:隨著市場經(jīng)濟體系在中國的逐步確定,人們在精神層面的追求則在漸漸萎縮,本文以以市場經(jīng)濟較為成熟的西方世界為對象,以西方相關(guān)哲學家思想為支持總結(jié)出市場經(jīng)濟、市場精神以及人的傳統(tǒng)倫理精神追求之間內(nèi)在的矛盾沖突之處以求相應借鑒。
關(guān)鍵詞:市場經(jīng)濟;市場精神;倫理精神
隨著市場經(jīng)濟體系的逐步確定,在當代中國,我們正愈益強烈地意識到精神的危機,意義世界的萎縮。而在市場經(jīng)濟發(fā)展較早的西方,思想大家們已經(jīng)對此作出過十分精準的剖析。
首先體現(xiàn)在市場精神內(nèi)在矛盾的暴露上。舍勒與韋伯對市場精神的不同定位正是代表了這一精神中內(nèi)在矛盾的兩個方面。在對這些矛盾的深度分析中,無疑舍勒更為深刻。舍勒也承認市場精神的勤奮、節(jié)儉、忠誠等特質(zhì),但是,他認為,這是進一步發(fā)展了最初的資本主義精神,但是在進一步追問中,作為形成中的市場精神,則是一種“怨恨”的心態(tài)。這是當時人與人關(guān)系的變化在精神上的表現(xiàn)。舍勒認為,在市場精神的形成中邁步向前的,并不是實干精神,不是市場競爭中的英雄成分,不是具有王者氣度的“商人”和組織者,而是心中充滿怨恨的小市民--他們渴求最安穩(wěn)的生活,渴求能夠預測他們那充滿精悍的生活,他們構(gòu)成了新的市民德行和價值體系,由此生成市場精神。所以,如果說韋伯對市場精神的分析體現(xiàn)著一種計算的理性精神,那么,舍勒則以怨恨這種情感性的東西作為市場精神的實質(zhì)。
其次,如果說韋伯和舍勒觀點的分歧說明市場精神中內(nèi)含著理性和怨恨的矛盾,那么,貝爾則發(fā)現(xiàn)了另外一對矛盾。貝爾認為倫理精神所倡導的勤勞和節(jié)儉之間、追求利益和禁欲之間存在著矛盾。他將其稱作“潛伏病灶”。倫理精神宣揚的是禁欲苦行,反對奢侈懶惰,從而促進了早期市場的發(fā)展。但是,這種禁欲苦行由出世向人世的轉(zhuǎn)化,使得對財富的追求由罪惡變成合理,這又必然使得人貪婪地攫取財富。一方面,倫理追求精神的價值,抑制肉體享受,以苦行來拯救靈魂;另一方面,它又鼓勵人不惜一切地聚斂財富,超出自然生理需要的界限,無止境地追求發(fā)財致富。難道人創(chuàng)造了財富而不能享受財富嗎?如果一味地禁欲,一味地反對享受,卻又拼命創(chuàng)造財富,這豈不是十分荒唐!事實上,隨著市場經(jīng)濟的確立,這種倫理就逐步失去了感召力,它的內(nèi)在的痼疾使得它走向了禁欲苦行的反面--縱欲享樂。禁欲苦行只是用于工人和其他勞動者,成為保護剝削制度的精神武器,而有產(chǎn)者自己則過上奢侈享受的生活。馬克思認為,市場生產(chǎn)是為交換而生產(chǎn),為生產(chǎn)而交換,在這一過程中,當交換者或生產(chǎn)者的財富越來越增加成為有產(chǎn)者甚至資產(chǎn)者,他就越背棄這種行為模式而成為揮霍者 。針對資本家勤儉、節(jié)欲的說法,馬克思進行了批判:認為有一種幻想,以為資本家看上去是“節(jié)欲”的,似乎正因為這樣他們才成為資本家。而事實上,這是一種在資本主義建立以前的時期才有意義的要求和想法,那時資本正從封建等等的關(guān)系中發(fā)展起來。雖然馬克思所點名批判的看似是產(chǎn)業(yè)資本家,但事實卻證明,這種狀況同樣適用于資產(chǎn)者甚至有產(chǎn)者。
第三,體現(xiàn)在人們精神向度的衰微上。自從尼采判定“上帝已死”之后,現(xiàn)代人的生活和工作也就失去了終極意義。人們失去導致了崇高的目標,失去了人生的價值和意義,人的精神危機、信仰危機,人失去了。人的精神處于孤立無依的境地。薩特的哲學以偏激的方式袒露了現(xiàn)代社會人們的這種心理體驗。薩特認為,在人之外,沒有上帝、沒有其他的邏輯必然性支配人,人不能指望在自身之外尋找任何自身存在的依托;人是孤獨的,人的一切行為都由人自我選擇、自我決定、自我負責;人處在一種孤立無援的狀態(tài)中,心靈充滿孤獨感;人的存在就是自由的存在,自由是不受任何外在力量限制的絕對化的東西;人的自由選擇和決定固然也要介人處境,要在一定境遇中進行,但是,處境并不能限制人的自由,因為處境也不過是人賦予世界的意義;人無所依靠,人被拋到世界上,人的存在沒有根據(jù)、沒有理由,人被判處了自由的徒刑,自由是人不可擺脫的宿命;人的選擇是五條件的,是完全由我自由作出的,因而,人要對自己的行為的后果承擔全部責任。
在倫理精神支柱坍塌之后,人們試圖用藝術(shù)取而代之,以填補精神生活的空虛。享樂主義時代的藝術(shù)是流行藝術(shù),它的特點是同經(jīng)濟生活、市場經(jīng)濟緊密聯(lián)系,按照市場上的價值規(guī)律進行生產(chǎn)和消費。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法蘭克福學派社會批判理論,對現(xiàn)代市場社會中人的精神生活的異化現(xiàn)象進行了揭露和批判。法蘭克福學派認為,在發(fā)達的市場社會,現(xiàn)代科學技術(shù)在藝術(shù)創(chuàng)作活動中的廣泛運用,使得藝術(shù)非個性化了,而是標準化、系列化了。藝術(shù)創(chuàng)造的模仿性、雷同性、形式化現(xiàn)象嚴重,創(chuàng)造活動成為無主體、無自我的活動。而這樣一來,消費者也成為被生產(chǎn)消極決定的了。認為從根本上來看,雖然消費者認為文化工業(yè)可以滿足他的一切需求,但是,從另外方面來看,消費者認為他被滿足的這些要求,都是社會預先規(guī)定的,他永遠只是被規(guī)定的需求的消費者,只是文化工業(yè)的對象。 由于藝術(shù)是在享樂主義盛行的時代被推上重要地位的,因此,藝術(shù)只是為了供人享樂、消遣,只是對勞動的緊張和疲勞的一種補償,一種肌肉和神經(jīng)的輕松、舒緩。娛樂消遣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是勞動的延續(xù)。那些想松緩一下機械化勞動過程,使自己能重新增長力量的人,都是這樣看的。這是勞動異化在勞動之外的一種延伸和繼續(xù)。既然人要通過娛樂、消遣調(diào)諧自己的身心,藝術(shù)享樂就變得呆板、平庸、無聊。因為要享樂,就不能再使人緊張,所以娛樂活動就得嚴格遵循社會的規(guī)定。觀眾不應該有自己的思想。藝術(shù)成為約束觀眾能動思維、抑制觀眾的想象力的活動,是對人的獨立自主精神的扼殺,對個性的扼殺。認為文化事業(yè)惡毒地使人體現(xiàn)為類本質(zhì)。每個人只是因為他可以代替別人,才能體現(xiàn)他的作用,表明他是一個人。他本人作為個人,是絕對可以代替的,是純粹虛的。
參考文獻:
[1](德),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閻克文 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2](德)馬克思·舍勒 ,《資本主義的未來》 羅悌倫 等譯,三聯(lián)書店1998年版
作者簡介:陳萍(1970.11-)女,漢,副教授,江蘇南京人,碩士,研究方向政治哲學,江蘇省委黨校哲學部。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