怡性弄情工而入逸(節選)
雒三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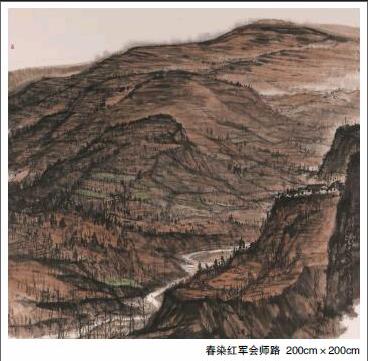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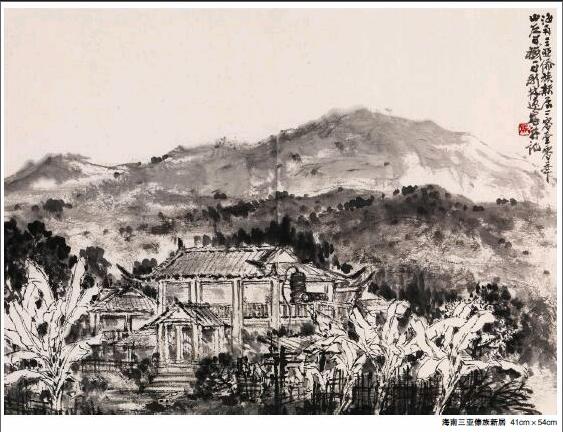

在當今的中國花鳥畫壇,馬新林是極少數能夠堅守傳統同時又自出新意的優秀畫家之一。能夠有今天的成就,與他長時期堅持不懈分不開。
馬新林從小就喜愛繪畫,并有所成。1983年,馬新林參加了孫其峰教授在洛陽西工區文化館的花鳥學習班。1989年,考入廣州美術學院中國畫系,師從尚濤教授。從此在尚濤和孫其峰兩位先生的耳提面命之下飛速進步。
馬新林師從孫其峰先生多年,他書、畫、印兼修,又勤于讀書、研古、知新,深得先生藝術之精髓,并結合自己的筆墨基礎和個性特點,不圖虛名默默耕耘,逐漸形成了自己的藝術特色。
首先是骨法用筆。馬新林有雄厚的書法篆刻基礎,他筆下的禽鳥和花卉用筆干凈利落,筆力遒勁,生動優雅,從起筆至收筆,往往一氣呵成,韻清而氣壯,用筆之遒勁,用墨之濃淡,均能得化工之巧,在傳達出花鳥繪畫優美動人的同時,更能使欣賞者感受到他筆下的抒寫之美和抒情愉悅。這種特色,在馬新林的作品之中都能見到。
馬新林的花鳥作品在細致觀察生活的同時做到了神韻傳達的生動和造型用筆的精準,使得其繪畫作品生氣勃發,郁郁生動。閑落枝頭的小鳥,徘徊花蔭的鵪鶉,振翅飛翔、穿梭于花木間的麻雀和異鳥無不神態安閑,仿佛其婉轉的啼鳴就在耳畔,將人帶入意境豐厚的畫境,給觀賞者帶來無數的愉悅。與中國傳統的山水繪畫主要為水墨山水或淺絳山水不同,花鳥繪畫對顏色的運用有著很高的要求。但中國花鳥繪畫反對艷俗,尤其反對用僵死的色塊破壞畫境筆韻,而更加講求嫻熟筆墨基礎上的略施粉黛,如出水芙蓉,天然生動。他的作品的設色十分雅致富麗,深得古人之精髓,并在傳統的基礎上推陳出新。在作品中,他盡量少用紅、綠一類鮮明的亮色,而多用赭、灰、桔黃、桔紅等色,使得畫面清雅而不失富麗,素樸而不失渾厚,果、花、鳥身等偶然出現的亮色與素雅的背景花卉用色往往形成雅致鮮明的對比,使人心曠神怡,百看不厭。如《長年日利》中掛滿枝頭、鮮艷欲滴的荔枝自然是馬新林曾經就學于廣州的體會之一,《秋趣》圖左上角的那只小鳥與其畫面的對比便是典型。
馬新林作品的另一個特點是有“勢”,這得力于他深厚的畫面布局功夫。與傳統的山水繪畫相比,花鳥繪畫往往顯得單薄,因此畫家往往在花卉的“勢”上下功夫。古人也以為,花鳥繪畫以得勢為主。他充分借用了書法布局中的基本規律,又精通篆刻,深諳知白守黑的藝術哲學,許多作品“疏處可使走馬,密處似不透風”,傳達出豐富的意趣,顯現出多重的神采,粗細、偃仰、穿插皆得其宜,既使觀賞者獲得美的感受,也使同道獲得有益的啟發。如《荷塘翠鳥》,密密的蒲草和荷梗、荷葉之中,一支低頭的翠鳥站立于右上方一根荷莖的折枝之上,既顯現出翠鳥背后深厚的空間背景,也使人感受到夏日荷塘的濃密與活潑。《秋趣》圖中,數根綠莖掛滿綠葉,直綴而下,兩只小鳥穿飛其間;左下方數枝花葉脫盡、紅果綴滿枝頭的果枝橫斜而過,既打破了綠莖直垂的單調,又有了鮮明的色、相對比,兩只穿飛于其中的小鳥則使畫面充滿的動感。再如《蘆塘小鳥》,占據畫面的主要是密密的蘆葦,深厚茂密,而挺立于蘆葦枝頭的幾只麻雀卻使我們聽到了鳥兒的歡叫,壓迫之感頓時變成了輕松小調。
馬新林有著豐厚的學養,這使得他在學習前人和古人的時候具備高超的眼光,審美水平的高超使他能夠迅速吸收傳統文化和前代畫家作品中最優秀的營養;而不斷地讀書學習、品鑒文物也成為他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書畫藝術的大忌就是庸俗,惟俗病最難醫治,一入于俗則猶人之病入膏肓。醫治俗病的惟一辦法是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是故前人每云不飽讀經史,終為畫匠。縱觀今日之宇內,終身為畫匠者不在少數。而馬新林這樣學養深厚、韻致優雅的藝術家就更值得我們推崇。
馬新林善于學古,善于學習前人。舉凡古今成就突出的畫家,無不走著一條“學古——入古——出古”的藝術之路。學古是為了掌握古人的藝術技巧,并領會中國傳統的藝術精神;只有入古甚深,才能深刻領會,達到這些目的。但學古、入古并不是為了給古人當畫奴,而是為了借古人之成就以開拓今日之生面。學詩如此,學文如此,學書法如此,學畫亦是如此。馬新林在努力學習探索新天地的同時,還在努力向當代大師學習。他是一位中國傳統繪畫藝術的捍衛者和守望者,用默默的耕耘傳承、發揚著不朽的中國書畫藝術。觀賞他的作品時,我常常想,畫如其人,人如其畫。欣賞馬新林的繪畫,充斥于其作品之中的蒼然之質,翩然之容常常使人動容,而縑素之間,郁有生氣,非筆端具造化者不能。馬新林又處在一個充滿創造力的年齡,他的花鳥繪畫終將超越自我,進入更高的理想境界是完全可以期待的。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