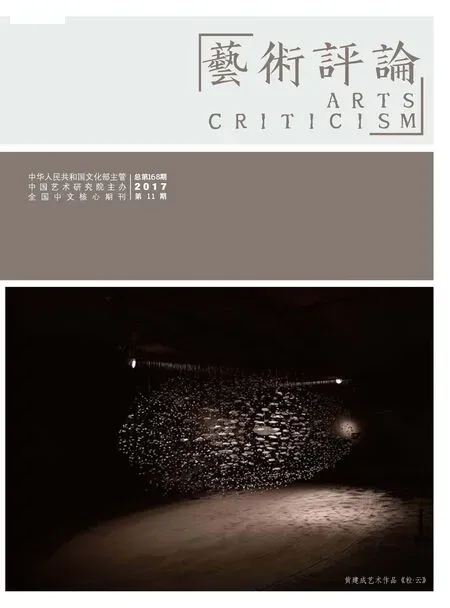王亞彬舞蹈創作中的對話性
仝 妍
舞臺表演藝術是表演者(或表演藝術)與觀眾之間的特殊交往活動,即通過交往實現審美主客體之間美的傳遞、精神的交流、情感上的理解和心靈的溝通。因此,表演藝術的舞臺審美交往方式,決定著其創作的范式。德國哲學家、社會學家哈貝馬斯在哲學層面分析現代性時著重強調了藝術的交往對話功能:“藝術要想能夠完成使分析的現代性統一起來的歷史使命,就不應死抓住個體不放,而必須對個體參與其中的生活方式加以轉化。……藝術應發揮交往、建立同感和團結的力量,即強調藝術的‘公共特征’”。作為一名青年女性舞者、編導,臺前幕后的王亞彬始終處于“自我”與“他者”的對話中:“自我”是個人的職業、年齡、性別身份與當代中國的時代、民族、文化身份等;“他者”是身體、時間、空間等劇場內外的表演場域;“對話”則表現為《青衣》里舞蹈與戲曲、戲劇的對話,《生長》中過去與現在、未來的對話以及“亞彬和她的朋友們”系列中所呈現出來舞蹈語言與表達的傳統與現代的對話。因此,王亞彬的舞蹈創作中有著各種或隱或顯的對話性;而這種對話性正凸顯出這一代的舞蹈家們在眾語喧嘩的時代文化語境中的成長與成熟。
對話一:“分化”與“去分化”
現代性的分化,使得藝術與日常生活分化,分化導致了體制化以及專業化,專業化則建構了藝術的獨立的審美價值。“歷史地看,正是藝術與非藝術出現了分化,及其藝術內部各門藝術之間不斷分化,逐漸催生出作為一門獨特藝術的舞蹈,在這個意義上說,舞蹈藝術乃是文化現代性的產物”。然而,專業化、職業化在具備合理性的另一面又有片面性,即自治的精英模式在專家與公眾之間造成了越來越大的距離,藝術在獲得主體化的獨立、合法身份后,又逐漸失去了與生活的深刻聯系。因此,現代性在分化的同時又導致了去分化批判的出現——從傳統文化形態中脫離出來的舞蹈藝術從劇場走出,又進入現代日常生活。這種“日常生活審美化”使得藝術走出了象牙塔,與大眾的生活發生了密切的聯系,審美和藝術不再是少數人的特權,而是轉為公共資源,成為一種文化共享。因此,“亞彬和她的朋友們”系列成為其以工作室這一創意生產和工作的社會化空間的系列產品,通過市場,走進大眾。這可以被看作是對“舞蹈家搖籃”、青年舞團的專業或職業分化的一種對話性對抗。從《與你共舞》(2009)、《尋》(2010)、《守望》(2010)、《亞彬和她的朋友們三年展》(2012)、《生長》(2013)、《夢·三則》(2014)到《青衣》(2015),演出季的軌跡折射出亞彬通過與朋友、與夢想、與舞蹈的一系列對話、交流、回應,實現自我的價值,在語言上突破了自身古典舞的專業分化,在言語上突破了舞蹈圈的群落分化。在這個“去分化”的過程中,亞彬通過磨煉完成了從舞者到編者的跨界,從國內到國際的跨越。
對話二:“傳統”與“現代”
即便做了一些當代作品,但是王亞彬仍然表現為一名純粹的“古典”舞者——用古典的舞蹈語言含蓄地表達現代人的情感。舞劇人物性格的塑造,與小說、電視劇的并無二樣,即筱燕秋骨子對戲曲的熱愛與執著。對于這種人物性格的塑造,小說用文字把對話的空間留給了讀者,電視劇用熒屏讓徐帆與觀眾對話,而舞劇則是王亞彬用最接近戲曲的中國古典舞語言,生動、共時、原真地在舞臺上呈現出一個有“溫度”的筱燕秋,表達了對于“生命該如何寄托”這樣一個現代哲理性主題的思考。這也是一個自幼學習中國古典舞的青年舞蹈家,面對傳統文化傳承以及現代社會對于人性的深層思考。這一思考,在其《生長》中得到了更為直接的表達:直面經典哲學命題——“所有人在生活中都會遇到的問題:‘生’,即我們從何而來?‘長’,我們要往何處去?”直面古典舞蹈的現代表達——“我是中國古典舞出身,在這個背景下,在詮釋現代舞時,可能會比單純用西方語言去闡釋現代舞多了更多韻味感,情感也更加豐富一些。”
我們可以看到,進入新世紀以來,以佟睿睿的《扇舞丹青》、張云峰的《風吟》等為代表的新生代編創者們,以傳統的方式對抗“現代”,他們可圈可點的“對話”表現被認為是“把握著根植傳統、立足當代、尋求自我的創新精神,更進一步的向當代舞蹈本體邁進。……在充分運用現代創作更為新穎的手段中,抓住當代中國人的民族文化心理并將其與藝術革新結合起來,強調當下的現代人對古典藝術的審美品位。”從這些中國“新古典舞”甚至是“新新古典舞”,無不顯示出中國古典舞的傳統與現代之間的自我超越、多元發展。
對話三:“語言”與“言語”
從審美角度理解,表演藝術的技巧就是使對象變得陌生,使形式變得困難,增加感覺的難度和時間長度,因為感覺過程本身就是審美目的,必須設法延長。藝術是體驗藝術對象的藝術構成的一種方式,而對象的構成在于對“自動化”語言對抗以產生“陌生化”效果。所謂自動化語言,是那種久用成習慣或習慣成自然的缺乏原創性和新鮮感的語言,這在日常語言中是司空見慣的;舞蹈中的自動化語言,是經過“規訓”的舞者身體或思維往往會自帶的無意識或下意識動作或套路。作為一名經過近十年中國古典舞“規訓”的非編導“科班”出身的亞彬,在努力對抗“自動化”而為我們帶來“陌生化”,首先是從單一的古典舞者成為表現出“眾語喧嘩”的當代舞者——良好的規訓身體被新的言語表達解構與重構。如對于《夢·三則》,她這樣說:“這部作品是三段體結構的舞作,每一個段落既是獨立的,又是相互關聯的,如同夢境中斷斷續續的片段,與現實有著某些隱秘的聯系,但又不同于現實。如夢般,三個作品在時空上可以疊加、錯落、重調,你可以把這‘三則’看作是一個‘順序’的微型舞劇,一個人,兩個人和一個群體,關于‘初識、遇見和重聚’;也可以在腦海中隨你的認識,像撲克一般,按照個人理解和感知,使‘三則’自由組合排列,再次創造出每位觀眾心中獨特的故事。”
如果說《夢·三則》是一個匯集藍、紅、白的色彩詩意的舞劇化探索,體現的是舞劇創作中“對現實時空的重建”,以運用獨舞、雙人舞、群舞等語體要素,完成獨白、對話、群言的言語能指與所指,那么《青衣》則是一個融舞蹈、文學、戲曲的戲劇抒情的舞劇化探索,以綜合宏觀、中觀、微觀、顯微的舞劇結構形態的系統層次,表現舞劇的情節、場景、意境、形象,從而表現關于理想、夢想、幻想的母題。如劇中有這樣一幕:筱燕秋立于象征現實、婚姻圍城的沙發一端之上,背對觀眾眺望著舞臺背景中高掛的一輪明月,她的新婚丈夫面瓜則站在沙發另一端之下,凝望著筱燕秋的背影……從舞臺調度的微觀層次上看,這樣一個看似簡單、普通的調度設計,巧妙地利用舞者在舞臺空間中的高度差異和視線的角度關聯,實現了“意境化”的舞臺效果,凸顯了作品的主題——“悲歌的嫦娥”。
對話四:“自我”與“他者”
在全球化的語境中,當代藝術創作身處一個語言雜多、眾聲喧嘩的文化轉型期,對話主義成為這一時期各類語言與文化之間對話與交流形式以及生存方式。在亞彬的舞蹈(劇)創作中,我們可以感受到舞者(自我)與人物(他者)的對話與交流,如在《青衣》中,編導、舞者(王亞彬)塑造的人物(筱燕秋),分別都是一個獨立的主體,具有自覺意識。編導、舞者創造了人物形象,是因為編導、舞者在努力追求和實現自己的自覺意識,確立其主體性。對于表演藝術而言,演員與角色的合而為一是達到表演要求與表演境界的標志,在舞劇《青衣》中,我們也似乎確實看到了:在舞臺上,亞彬在與筱燕秋的自覺意識的平等對話中,實現了自己的自覺意識。這實際上可以理解為:為了完成自我,必須創造一個他者。在中國傳統文藝理論中,自我與他者對話的實現是在“物我兩忘”的藝術境界中;而在西方文化理論中,巴赫金的對話美學凸顯了作者與主角、自我與他者的對話的“主體性”意識。
從舞劇作品的“自我”與現實生活的“他者”的“對話”層面來看,藝術創作中實現“自我”與“他者”的對話,呈現出一定的“時空型”,即我們所說的“藝術來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這句話指出了藝術創作有著生活的原型,但又不是簡單的原型反映,藝術中的時空型往往比現實生活中的時空型變化更為敏感與夸張。如從敘事角度來說,“故事”與“情節”常常是按照事情“原有的”(即現實)時序發展為素材,通過對“故事”與“情節”的加工、編輯、組織,強調其內在聯系性——時間與空間、真實時空與敘事時空的內在相關性。如《夢·三則》旨在“對現實時空的重建”,用藍、白、紅的色彩建構起舞臺的敘事時空,照進“當下中國環境中青年人”的人生夢想的現實中;而更加接近現代舞的當代舞蹈語匯,表達出面向現代、面向未來的青年人,努力以一種世界性、現代感的中國舞蹈語言,實現與“他者”的對話。
注釋:
[1]哈貝馬斯.現代性的哲學話語[M].曹衛東等譯. 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53.
[2]周憲. 從舞臺到街角: 舞蹈現代性的思考[J]. 北京舞蹈學院學報,2015(3):2.
[3]顏亮.編舞大師徹克奧維攜手舞蹈家王亞彬帶來現代舞劇:《生長》里有對人類和劇作的愛[N].南方都市報,2013-11-22(RB13).
[4]金浩.論中國古典舞創作的“后身韻時段”[J]. 北京舞蹈學院學報,2006(3):67.
[5]夕君.“亞彬和她朋友”演繹《夢·三則》[N].中國文化報,2014-08-12(06).
[6]巴赫金(1895-1975)蘇聯著名文藝學家、文藝理論家、批評家、世界知名的符號學家、蘇聯結構主義符號學的代表人物之一,其理論對文藝學、民俗學、人類學、心理學都有巨大影響。他的對話理論力圖提供一種全新的關于人的存在的交往對話思想體系,為文學、文化研究開辟了新的研究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