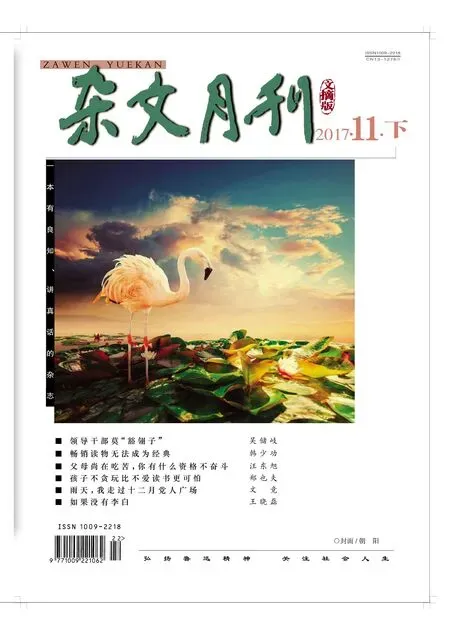托爾斯泰的懺悔
□狄青
1852年7月,彼得堡《現代人》雜志收到一篇來稿,作者是一名在高加索山區駐防的炮兵下士,署名“耳·恩”,小說題目叫《童年》。雜志主編涅克拉索夫覺得這是位天才,把作品拿給屠格涅夫看,屠格涅夫說:“給他寫信,告訴他我歡迎他,向他致敬并祝賀他。”涅克拉索夫回信給小說作者,希望他繼續寫作,同時商量小說發表時可否用真名,對方回信同意——于是,一個叫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的作家從此聲名鵲起。
許多年后,屠格涅夫在臨終前,給托爾斯泰寫去一封信,誠懇希望托爾斯泰回到文學,不要辜負自己的才華。而這時候,托爾斯泰正每天穿著長褂和他自己親手縫制的布鞋,行走在底層農夫之間。事實上,在完成了《安娜·卡列尼娜》后,他的文學創作便停止了。而他給世人的解釋是一篇《懺悔錄》。這是一篇懺悔自己同時也在剖析他人的文字,與盧梭、奧古斯丁《懺悔錄》中敘述的內容迥然不同,托爾斯泰要探討的問題其實只有一個:人生的意義何在?我們為什么而活?
說實話,初讀《懺悔錄》,我就被震驚了,因為托爾斯泰完全顛覆了我們對傳統意義上“作家”的認知,那就是,作家不能只是一個寫作者,還要懂得懺悔、接受心靈的拷問,繼而才有可能超拔。懺悔不易,救贖更難,一個人要拉他人出沼澤,自己卻站在泥塘里,誰救贖誰?身為貴族的托爾斯泰產生了放棄所有財產的想法,但遭到妻子強烈反對,這成為他們夫妻關系惡化的重要因素。結果是:托爾斯泰放棄個人財產,轉到夫人索尼婭名下。我們不能責怪索尼婭,她為托爾斯泰生了十三個孩子,單一部《安娜·卡列尼娜》她就抄了七遍。她只是一個希望過安穩生活的女人,她崇拜但不理解托爾斯泰。
從《懺悔錄》里我感到,對托爾斯泰來說,思考生命的價值和信仰的意義,是他的天生責任和義務。所以,他開始俯下身子去傾聽那些沉默的大多數。從那些隱忍的底層人群中,他看到了信仰對于生命的意義,看到了信仰與浮華生活之間隱秘的對峙關系。
蘇格拉底說:“未經審視的人生是不值得過的。”托爾斯泰從很早就開始審視自己了。在他的許多作品中都能讀到這種痛苦求索的痕跡,皮埃爾、列文、聶赫留朵夫,也包括安娜,他們之所以成為經典形象,不是因為他們有過人的英雄壯舉,而是因為他們背后有一個偉大的思想者。
俄國思想家別爾嘉耶夫說,托爾斯泰的吶喊是與眾不同的,他擁有一切,卻不能忍受自己的特權地位。人們追逐榮譽、錢財、顯赫的地位和家庭幸福,并把這一切看成是生活目標。而托爾斯泰擁有這一切,卻竭力放棄這一切,他希望平民化并且和勞動人民融為一體,是源于一個思想者、一個作家的創造精神。
事實上,在俄羅斯,作家對自我的懺悔促使他們的筆觸突破表層,向社會縱深方向挺進,向人的靈魂深處邁進。就如魯迅所言,這種“對人的心靈進行拷問,在潔白的心靈下面,拷問出心靈的污穢,而又在心靈的污穢中拷問出那心靈的真正的潔白”。
放下文學創作的托爾斯泰,卻為教育普通民眾寫了《民眾教育論》,為兒童寫了《啟蒙讀本》《與兒童談道德》,為農民寫了《荒年補救方法》《拯救饑民》等。他以這種方式,凸顯一個作家的價值與擔當。
有多少人可以認識到自己身上揮之難去的惡念?認識到生命中已經腐爛的那些部分?認識到生之中即隱藏了死亡呢?因而,得以鼓足勇氣,真正的否定自我,重新來超越自我?
這些年,我聽到最多的話,就是一個作家一定要把故事編好,將作品寫好,而思考嘛,想多了不僅無益,有時候甚至會阻礙一個作家的發展。是啊,“速食化”“數字化”疊加,我們要的是腦洞大開的想象力,要的是只爭朝夕出東西,思考也好,思想也罷,那是思想家的事情,不是作家的事情。而個別文學創作越來越像大工業生產,誰在上游工作,誰盯下游工序,都已安排好。我們還需要懺悔什么?那不是沒事找事嘛!這一切,托爾斯泰一定想象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