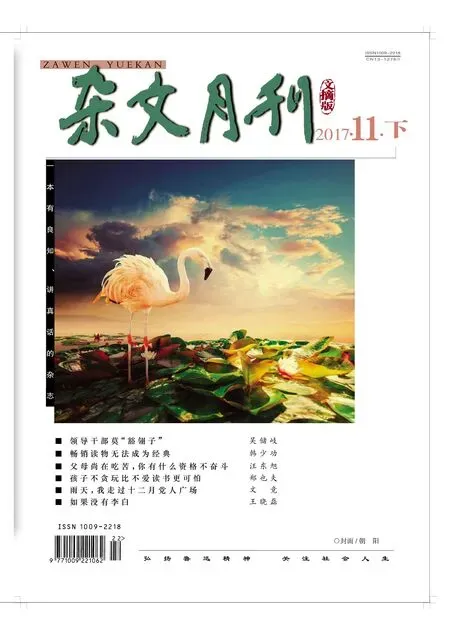生命的絕唱
□ 沈光金
在李清照的作品中,我最愛讀她的《金石錄后序》,兩千來字,鋪張有序,一氣呵成。《金石錄后序》是先生晚年的作品,除了追述恬夢般的幸福,也記載了噩夢般災難。《金石錄后序》不僅記述了家亡的悲傷,也咀嚼著國破的痛苦。“南渡”之后,先生淪為難民,生活越發艱辛,身世越加悲慘,更不說顧及金石字畫了。易安先生如一葉浮萍,漂泊在凄涼和困苦之中。
如果以靖康之變的“南渡”為分界,先生的前半生是風花雪月添多愁傷感,后半生顛沛流離加凄風苦雨。“風花雪月”表現了對生活的滿足和無憂,“多愁傷感”訴說著對愛情的執著和珍惜;“顛沛流離”痛苦著亡國的倉惶和離亂,“凄風苦雨”哭訴著家破的痛楚和無奈。在先生輾轉的軌跡里,在傳世的詩文中,還可以看見另外一個李清照,一個心存壯志、舉翅欲飛的大鵬,一個對國家存亡、民族中興時刻牽掛的赤子。
詩言志,詞言情,易安先生存世的五十余首詞,絕大部分是抒情之作,都是能唱的“樂府詞”,按先生的“規矩”,她的詞絕不是“句讀不葺之詩耳”。但是,我以為,先生的詞也言志,“天接云濤連曉霧”的《漁家傲》就言志,《漁家傲》抒發了先生被壓抑的政治抱負和熱情,對自由的渴望和光明的向往,豪邁氣概和浪漫精神體現出先生“詞風”的另一面,是“生當作人杰,死亦為鬼雄”的潛質所在。
“九萬里風鵬正舉,風休住,篷舟吹取三山去。”何等的豪放,何等的壯勇,詞也言志。“志”和“情”是分不開的,無情何言志,有志定有情,正因為“志”和“情”于人、于世是分不開的,所以寓含在“詩”和“詞”形式內的“志”和“情”也是不能確切地分出彼此的。譬如,易安先生有七絕“春殘何事苦思鄉?病里梳妝恨發長。梁燕語多終日在,薔薇風細一簾香”,卻不是詠志的。
易安先生晚年的一些散文和詩作的憂國憂民情結更重,既憂傷多難的國家,又痛恨茍且的朝廷。“兩漢本繼紹,新室如贅疣。所以稽中散,至死薄殷周”,表明了對金人扶持漢奸張邦昌(偽楚)和劉豫(偽齊)的傀儡政權的鄙視和譏諷,表現了先生高尚的民族氣節和愛國精神。《夏日絕句》唱詠了寧死不肯忍辱偷生的亮節,譴責了趙構偏安江南、妥協茍生的行徑。可惜了女杰,可惜了詩人,可惜了不能為須眉,可惜了不能為李鋼、岳飛。
有趣的是,易安先生的“言志”絕不用“詞”,而必用“詩”,堅持“詞別是一家”,絕不像東坡“詞”那樣,只可關西大漢,手撥銅鐵琵琶,高聲“大江東去……”詩人的執著和守制可見一斑,這“守制”就是堅持“詩莊詞媚”,至死不棄,這“執著”也就可愛極了。
我想起個人,就是“桃花扇底送南朝”的李香君。
侯方域沒有銀子給李香君贖身,“閹黨”阮大鋮假楊龍友之手出錢,意欲拉攏侯方域入僚。侯方域尚自猶豫,但是,李香君痛罵侯、阮,把錢扔還給了阮大鋮。“侯公子”因被通緝而逃之夭夭,李香君洗盡鉛華,閉門謝客,“一頭撞在欄桿上,血濺桃花扇”而拒田仰。明亡清入,復社四公子的陳貞慧隱居,冒辟疆游歷,方以智出家,唯“侯公子”參加了順治的鄉試,進了副榜,有負盛名,有負紅顏,“士大夫之無恥,謂之國恥”,不如一個青樓。
世人皆推崇易安先生的詞,以我所見,一篇《金石錄后序》就蓋過了她的詞,先生的“骨”見于她的“文”,雖然留下的“文”并不多,而我所能見到、讀到的更少,除了《金石錄后序》外,還有《詞論》《打馬圖經序》《打馬賦》和《上內翰綦公(崇禮)啟》。特別是《上內翰綦公(崇禮)啟》,因洗脫“玉壺頒金”的冤屈而致綦崇禮的感謝信,言辭懇切,親疏得體,感恩而不卑微,細說而不累贅。“高鵬、尺鷃,本異升沉;火鼠、冰蠶,難同嗜好。”更是“達人共悉,童子皆知”,層層說理,娓娓道來,真好文章也。
散文家、詩家、詞家李清照。伊人愛國,須眉可讓;斯人壯志,天地可鑒。愛人,“才下眉頭,卻上心頭”,是刻刻縈懷;懷國,“只有情懷,不似舊家時”,悲物是人非。
陸游說過:“易安居士能書、能畫、又能詞,而尤長于文藻。迄今學士每讀《金石錄后序》,頓覺心神開爽,何物老嫗,生此寧馨,大奇大奇。”陸游,居士之同代人,尊清照先生為老嫗。我當說“何物先賢,生此不二之才,偉哉偉哉”。我獨愛《金石錄后序》是尊易安先賢,是步放翁后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