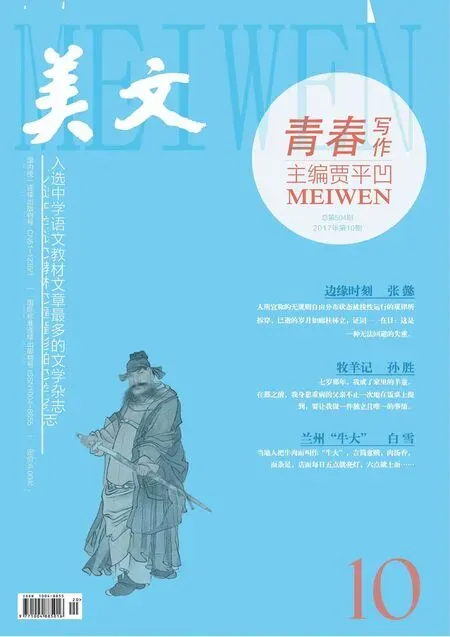沒有標題的愛
沒有標題的愛
之一
秋天來的時候,我的鋒利也跟著鈍化下來。
總是有這樣的時期,對于黑暗的嗜血癥狀減輕,整個人松散下來,像一把未拉滿的彈弓,或是未經擠壓的彈簧。我像一把匕首,因為找不到自己的寒光而恐懼。
我原本是清晰地了解起點,也了解終點,甚至熟悉抵達的路徑的,我知道這一切都很安全,包括在哪個拐角應當攝取什么,一切似乎都可以在掌控之中。必經的痛苦,反抗的方式,放棄的模式,經由多次重復而變得可親可近,像一只寵物刺猬,每一次扎出傷口都令我更加愛惜它,又回避它,如同小心翼翼地回避自我。自我是丑陋的海上毒沫,身為精神的魚每吸食一點,就會麻痹窒息一回。然而這依然安全:你掌握痛感的來源,并精心梳理其纖維,并試圖將其偽裝成美。駕馭這種勾當,你輕車熟路。
但或許是因為南方,也或許是因為秋風,我卻輕而易舉地踏上了陌生的分徑。我謹慎而緩慢,懷抱著在下一刻鐘成為一灘碎瓷的風險預估,走著。秋天的密林,光線時亮時暗,有人從時間里,切下銅錢大的白燭光,為我沿路安放。我依然看不見晝的輪廓,憑著人造光一一指認林中隧道的曲折。我有時會害怕地哭起來,希望握住一只不存在的手,兔子也好,狐貍也好,那急匆匆過去的土拔鼠也好,握住那種靈動跳脫,不要走得像一個躑躅的象形漢字,尤其是在秋天。
我怕自己會被再次吹滅,我更怕失去進入叢林深處的勇氣。我害怕失去自己的銳度,又渴望進入一片明亮的曠野,夕陽照著,我如谷垛般柔和,色澤細膩,蓬松而微溫。我隸屬于我的猶豫,我是它的陀螺,在十月的寂靜里,被我的矛盾反復抽打。
然而最終我還是背叛了自己,在陀螺減速的間隙,突然向宇宙叫出了一聲:等等我。
之二
我們不要去雪山了吧,像我這樣,煙霧一樣的東西,會和我的文字,我的說話,還有我的小心思一起,全部變成整齊的冰塊的。給人拿去砌成房屋,砌成橋梁,會有咕嚕咕嚕的囈語,在星星藍得像海水的夜晚,泡在空氣里,擾人清夢的。
那樣可太糟了。
還是去赤道搭建涼棚吧,把耳朵深深埋進沙里,變成熱風吹過時的小小丘陵。四肢綿軟,滿儲寶藏;頭發里全是綠洲,駱駝從額頭東邊升起西邊落下,像金色的雪。讓一切為之旋轉一分鐘,再輕輕落回原地。忘了悲傷,忘了擔憂,忘了夜晚要終結于白天,忘了人生的難。讓生活干燥疏松,不含水分,所有的鹽都用以釀造水晶,在腹地的幽冥里。
眼淚呀,眼淚是最珍貴的雨,是倒流的森林,誰也不要舍得讓對方落下。
之三
我的眼睛天生帶著霧氣,無論看什么,都隔著清晨的一片大霧。我清晰辨出過的只有死神的手,冰冷而充滿憐憫。我常在人的叢林與平原里感覺恐懼、慌張、不知所措。我始終無法處理好與生存的關系,汗從腳底爬上來,像掙不脫的蛇。
然后你來了。像冬日緩緩灑在結滿白霜的屋宇、枯枝、草地的陽光。
我很久沒有這樣安靜地觀察過自己的疆域與地貌了,我凝視著你,看你的光芒將霜氣化而為露,萬物被折射于一片晶瑩當中。你輕輕撥開我眼里的霧氣,我害怕得想逃避,腳步卻沒有挪開。我看見我所有的屋檐都潮濕,所有的枝葉都顫栗,所有的草尖都青碧,我在你手心快樂地發抖,心中知道,這一刻在愛情的時間線上,將幾乎等同于悲傷。
我這樣畏懼著愛,又心甘情愿被它的灼熱收買。我靠近你,像一只初生的麋鹿靠近樹林,在你面前暴露我的脆弱與欣喜,仿佛不知愛是最久遠的孤獨。
不應當無所防御,然而,那個吹走霧氣的人啊,他看起來像積滿厚厚落葉的林中空地一樣安全,他有金色的溫暖胸膛。他是我的平均率。
之四
血在世界的某個角落紛飛,顱骨上盛開大朵無辜的玫瑰。懷抱用來溫暖深愛的人冷卻的軀體,吻獻給已經停止的哭泣。憤怒與絕望是兩匹野馬,將瑟瑟發抖的心分尸。黑夜像一個漏雨的避難所,流彈從屋頂漏了下來,落在手無寸鐵的恐懼之上。
而在另一處,人類為人類劃上界限與等級,人類為人類制造恐懼,區分敵我,人類的心擁有著最險惡的氣候,并以自相殘殺為樂。
但我們相愛。不免帶著罪意與歉疚,為這人世間所有我們無法拯救的不幸。像在戰斗間歇的壕溝上,無視著犧牲者的鮮血而忘情擁吻,想要以此確認一息尚存。哪怕假如下一刻死去,射穿你的子彈也會射穿我;而作為幸存者,我們將一起對著煙花顫栗,像嗅到美與危險的豹子,在對同伴痛苦的回憶里,緊緊銜住對方的脖頸。我們會是再次日出之時,廢墟上升騰起的最后的塵氣:一縷濕潤的炊煙,一塊文明的尾骨,一個攥緊歷史的拳頭,一對愛情的遺孤。
讓我們重新教雨走路,教它以溫柔的腳趾,安撫遍布大地與時間的傷痛。
之五
我走向你的時候像是一只孟加拉虎,赤著腳,濕淋淋的。你打開你的叢林,如同打開巖石層的合頁。
我曾是羈留其中的化石嗎?億萬年過去,靈魂留下物化的痕跡。在你尚未出現時,就守著星球變遷的秘密。
你望著我,像月亮低垂在水面上。我的憂郁是湖水,很快吞沒了你的投影。黑暗是一串鉸鏈,牽制我的時候也浸蝕你。
但我們相擁著,就像從隕石坑向地球回望,只見大陸低懸,山巒聳立,萬家燈火匯聚,你我的影子像兩塊洲際拼圖,被洋流移挪。
我大聲叫喊,想聽到山谷目擊者般的回音,卻只聽見地球那龐然無聲的寂靜。無人作證,愛情像一段對神的告解。
你在真空里抱緊我。而我懷抱著來自一個年輕身體的欲望,不知如何是好。
之六
所有的故事都始于夏季。夏天真好啊,我在夏天是最快樂的,體態輕盈,四肢舒展,沒有擾人的疼痛。
我依然覺得你像初夏,溫和而晴朗,樂天的像一架手風琴。我咚咚走過,隨手拉響你的音階,你就讓旋律跟在我身后,輕快地跑動起來,像一匹紫色的馬。當我懊惱你為何這樣歡快時,你就變成一只藍色的小鼓,咚咚地,用你海水一樣的眼睛看著我,用你的海浪包圍我。
我愿意你的眼睛沒有風雪,如果一定要有的話,還是讓我來做你眼底那淡淡的陰影。
不需要取悅全世界了,取悅你,或者我,就好。戀愛的人都是自大的自私鬼,這是僅僅屬于他們的權利。而我把這份權利交給了你。
你丟失清晨的時候,我也丟失了傍晚。夢的舟楫交互滑過,我聽到你的靈魂在睡夢中低吟的聲音,像封禁的熱帶雨林,叢林茂密植物蔓生,充滿多汁而飽滿的香氣。我看見你的心長出屋宇,金屬的飛鳥在其間輕輕碰撞,成為白晝的容器,夜來時便盛滿飛旋的流光;而你的眼睛,是地心引力,是星系,是時間,我可以旅行很久。
之七
戀人一經擁吻就化為酒,將彼此啜飲。酒是星河,淌過你肋間的鐵軌,也淌過我腹部的稻田。我巖漿般的支流零散而細小,帶著所有的火光和熾熱流向你,而你是幽深的河床,以金色而空曠的回聲為我導航。
你這光的孩子,隕石一般,在我的宇宙撞開一個裂口,教自己充盈其中。我看見你,在漂浮著微小記憶的塵埃里,透明而耀眼。愛幾乎是痛苦的,你的話語像春天的手指,在我的地表覆上薄薄的青苔,又以撫觸,要求我沉睡的種子一一醒來。吻是一種小型的炸裂,像鈴聲突然在風里抖落,我的靈魂也為之一震。
我抵擋不了你。
我要如何抵擋你呢?你讓我覺得自己是廣漠的草原,狂沙、灌木、跑馬、平靜時波浪起伏般的舒滑。你讓我覺得自己是落日低垂的山峰,雪是我的脈搏而你是我身上的針葉林。你何曾賦予什么,你不過是要我自己顯現。那無限的可能性令我迷戀。
你就像是一個無法訴之于人的愿望,我獨自抱著不懷希冀的構想,在渺茫的海里飄蕩。你看見了我,你伸出地平線召喚我,并以我無法預知的方式,解開了自己。
我竟滿足得害怕起來:為什么,又一次交出了深深依戀?
之八
牛羊從不在我的山坡上跑,牧童也從未吹響竹笛,鄉野是一種想象,僅存在于他人的語言地質層里,那是別人的礦藏。我只擁有一個古老、衰敗的小城,和它那被災難埋葬的往昔,那繚繞其上的傷感,那潛流于平靜生活下的痛楚。無需掘地三尺。
我是沒有心理上的故鄉的,我的鄉愁在詩經,“我徂東山,滔滔不歸”,在漢樂府,“回車駕言邁”,在唐詩,“花重錦官城”,在宋詞,“買花載酒長安市,又怎似家山見桃李”,在你,你是我一個人的詩,從前往后,再不會有人這樣將你寫起——我不許。你就是我的“采采卷耳,不盈頃筐”,你就是我的“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是我的“明月出天山,蒼茫云海間”,也是我的“待得歸鞍到時,只怕春深”。我不費絲毫力氣就可以將你想念。
念你,念你的岬角、港灣,念你的半島與瀉湖。你遠的像在另一個宇宙,存活于另一套生態系統,有自己的地貌和物候。我觸不到你,我只能瞇著眼辨認,可你就像一張舊時的黑白照片,底色模糊了,容顏也迅速褪去,視覺被置于一片灰蒙之中,那籠蓋萬物的灰色帶著起伏的顆粒,在指尖形成一種令人心碎的觸感。此時我聽見自行車散漫而急促地搖著鈴,犬吠著,越劇從舊收音機里吱吱嘎嘎傳來,你從童年汗水涔涔跑來,經過我,又跑向了你的現在。我們像兩列火車,在某趟旅行的中途并行停下。你的車窗映著我的桌椅,你的乘客對視著我的旅者,彼此大膽凝望,然后,微微別過臉。時間為此走了弧線。它為我拉開一張弓,而你是我弓上遲遲不肯發出的箭。
念不到你,只能將你的故鄉懷想。我真羨慕你,你的鄉愁多么具體,不像我,只能寄之于人。我曾經一次又一次想起那些白鷺、稻田與河流,你上學必經的工廠和山坡,在心里拿了手指細細描摹,直到成為最為稔熟的版圖。我連自己的故鄉,都沒有過這等熟悉。那景象一半來自于你偶爾的簡短提起,一半來自于我的想象。拋卻虛構成分以后,我發現我是不了解你的故鄉,也不太了解你的。然而我依舊對那塊土地懷著一份難以言喻的柔情,就像我對于你,滿懷著的無非是一團混沌的溫柔。你在我身上喚起的,是一種無端的惆悵,影子一般跟著,我卻舍不得剪。
那種惆悵大概叫童年。又大概,是一種我所不能真正明白的鄉愁。
之九
每天,你在你身體里活上二十四小時,并在我的文字里活上一分鐘。你的時間如魚群,而我是你溫柔的掠奪者,覓食的魚鷹。
吾愛,我想以月光的方式抵達你。無論時間如何套疊、彎轉,我都能準確無誤地找到你,潛入你,像一行詩與另一行切合,像一個音節嵌入另一個。月光是我的百合花束,將在你的唇上緩緩舒展。
春天尚未到來,我就開始破譯你的韻腳。一切青蔥的事物都像你,你就是生機勃勃的代名詞。風吹過,你就會滿山坡長毛茸茸的小草,那是你蘇醒時的下巴。而我將隨意地走著,散漫得毫不經心,直到伏身聽見你的心臟在十億顆種子里跳動的聲音,才驚覺你就是春天黃昏的鴿哨:
一吹,東風就滿了。我的心像一葉綠舟,在你的聲音里,漸漸浮了起來。
之十
為了抵抗時間的萬有引力,我們在深夜醒來,在夜的濃蔭之下,愛像地衣一般生長。我在暗處,在地界,把等待充作刺刀,斬開不斷朝我涌來的荊棘。而你在光的彼岸,在神啟的東方,你像一卷飽蘸雨水的藍色預言,宛然伸展,道路漫長;你要走遍人間,才能抵達我,每天每天。
你的身體像一叢密實的紙莎草,我要以手指采集你,以雙臂環抱你,再將你浸在我尼羅河的水里,用吻不斷敲打,才能萃取你薄如紙的精華。然后裁你為舟,為馬,為灰雁,教你在飛山渡水時,更為輕盈迅捷,教你在秦桑燕草間行走時,記得我視線的溫度,你于是要在每一步里背負我的思念。
我想成為你的刺青,因我是驕蠻的自私的。我還要在你身上織錦。你看不見我的繡線,我耐心地在你的生命里回溯,把你所分贈予我的往事,清潔、浸泡、煉而為絲為線,再一針一針,繡成我的圖案。我不必將你修葺一新,我只要一叢雜草,幾片瓦磚,一兩件你所廢棄的家具就夠了。我要做你的金繕匠人,在你所空缺的地方,統統補上我。
我知道我是太蠻橫了,然而我也不為之道歉。我知道這一切,我都不能。我只能等雨燕自你的屋檐向下垂直飛行時,奉上一個潦草的信號,要你踩著夜的脊骨,到我的疆域來。我陌生的異界。
如果你不來,我就以自己為火種,燒去地界的植被,煉掉寓居于我的鬼魅,再無可燒了,便冷卻、熄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