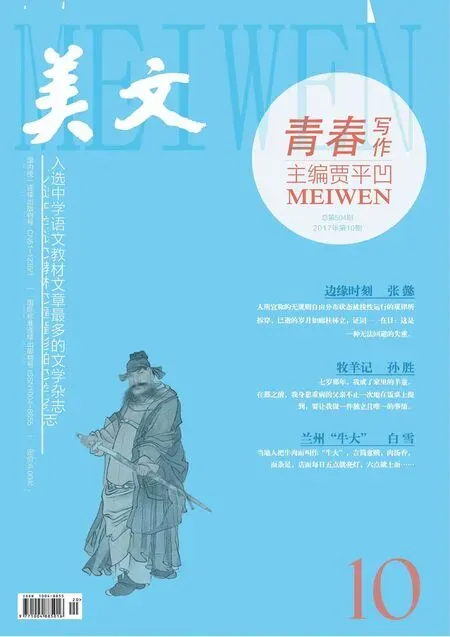她
孫 婷
她
孫 婷
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邊的累贅又是笨重的。
——蕭紅
她的一生,就是一部小說。
她雖生于富裕家庭,卻早早地被算命先生認定是命賤不詳之人,受到父親冷遇。幼年喪母。母親去世當年,父親就迫不及待地續了弦,把繼母接進家門。
少女初長成,好奇之心未及探索這萬千世界,分明世上的善惡之心,便由父親做主,將她許配給一個沒有人生理想,只喜歡抽鴉片的小學教員。那一年,她14歲。
她不甘心。她要自由。她要讀書。父親大怒,強迫她輟學在家,形同軟禁。一年的時光,她是在阻撓、逼婚、惡言惡語中捱過來的。童年已是萬分不幸,唯有祖父的愛能撫慰她多愁善感、孤苦飄零的靈魂,如今,父親的壓迫反讓她的性格越來越倔強、極端,如同導火索一般,觸發了她一生不幸的潘多拉魔盒,命中了算命先生的定論。人就是這么奇怪,總是往對自己充滿負面評價的路上義無反顧地走下去,頭也不回,然后把這叫作“命運”。
18歲,祖父去世。世界上最疼愛她的那個人走了,家也再無可留戀之處。
19歲,她逃離了那個沒有愛和溫暖的所謂的家。
她結識了讀大學的遠方表哥,并在他的幫助下來到北平,進入女師附中讀書。她用多么新奇的目光打量著這座陌生的城市,聽著它巨大的喘息聲,想往著沒有束縛和壓抑的生活啊!然而北平居大不易,她必須停下所有美好的想象,低頭瞅一瞅身上的破衣爛襪,發愁每天的吃飯錢從哪里能籌措到。逃婚的“出格行徑”讓整個家族都震怒,感到“蒙羞”,為此斷絕了她的經濟來源。無奈之中,她只得再次回家。軟禁,打官司,敗訴,轟轟烈烈的一番折騰后,全家搬往鄉下,她也被迫同外界隔絕。
在鄉下的時候,因為幫佃戶說情,她遭到伯父痛打和軟禁。伯父揚言要勸她的父親勒死她,以免再連累和危害家族。恐懼一次次攫住她的心。后來,在小姑和小嬸的同情和幫助下,她再次出逃。
那段日子居無定所,險些流落街頭。家鄉封閉的空間和落后的思想讓她壓抑,但她不得不依附于此。她的一切行為在那個小小的天地里,都被看做是離經叛道,惹得親友痛恨不已,就連她嫌棄的未婚夫,那戶人家也厭惡了她。愛也好,恨也罷,那就是她的家,她的故鄉,刻進骨子里,融進血液中的地方。她該怎么辦呢?她能怎么辦呢?
她同未婚夫找了間旅館,住了下來。雖不至于流落街頭,但生活的困頓讓她灰心喪氣,茍延殘喘。她開始和未婚夫一起在逼仄的旅館住處吞云吐霧,行尸走肉般的生存于世。半年后,她懷孕,產期臨近時,未婚夫不辭而別。
挺著大肚子,無力支付房費,又無生存技能,只會寫作。萬般無奈之下,她寫信給報社,并寄去自己的小詩。她是那樣有才情,一首小詩就打動了一個文學青年的心。他似乎是順理成章地出現在旅館門口。那一年,她20歲。
孩子生下后隨即送人,后夭折。她不是不愿意撫養孩子,她那顆善良敏感的靈魂連一只小金魚的死都難過萬分,何況自己的骨血?但她實在無力撫養這個孩子,自己饑一頓飽一頓,連自己都照顧不好,何談照顧一個嗷嗷待哺的嬰兒?
21歲,她同那個文學青年生活在一處。同他在一起的那幾年里,他一邊做家庭教師賺錢養活兩個人,一邊在外借錢度日,她則在家徒四壁的旅館小房間里,看著外面的鵝毛大雪,等著他回來。
等的無聊了,她便拿起筆寫作,寫下她的困頓,她的饑餓,她的寂寞。二十多歲的她寫了那么多文字,唯獨沒有寫下的,是她的青春。
她同他一起生活了六年。六年里,她為他洗衣做飯,疊衣鋪被,抄寫文稿,日日等待。她像一個孩子一樣依戀他。盡管逃離了那個壓抑逼迫的家,但她的思想被那個家浸淫腐蝕已深,女子的自卑生生地壓在心頭,使她無法獨立自主,掌握自己的命運。并非命中注定,而是成長環境,讓她既然不能夠長成一棵大樹,便只能依靠另一棵大樹。
六年里,他不斷地愛慕上別的女子,與她們暗通款曲,她心有不快,卻裝作不明就里的糊涂樣子,最后一次,她終于憤怒相向,換來的卻是拳腳相加。她的身體和心靈遍布傷口,再醫下去已無必要。一場愛情悲劇就此收場。
可笑的是,他在友人面前不斷地強調她沒有“妻性”,作為對他們分手的解釋。他認為她有著普通女人一樣愛吃醋的性子;他認為妻子就該像舊社會的正妻一樣,賢淑到主動為丈夫納妾,才算有德;他認為她的寫作才華太突出,作為妻子,怎么能搶去丈夫的風頭,甚至獨領風騷?六年里,他看到的都是她的缺點,卻看不到她的付出和等待,也讀不懂她的寂寞和憂傷。
作為文學上的伙伴,他心安理得地接受她的付出,滿意她為他抄寫的手稿,允許她與自己走得很近;
作為生活上的伴侶,他厭惡婚姻里的“平等”“相互尊重”,嫉妒她的才華,瞧不上她和她的創作,帶著憐憫和施舍的目光遠遠地打量著她。
散了吧。
懷著他的孩子,她投入到另一個男子的懷抱。那一年,她27歲。
她累了,也倦了,與新婚丈夫的關系不過是想安穩地過普通人的生活,不再顛沛流離。她想找一棵堅實的大樹依靠,卻不想這棵樹還是小樹苗,能不能長成參天大樹都未可知。這個依賴性很強的新婚丈夫在日軍轟炸時,丟下大腹便便的她,一人跑路,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再次拋下她,獨自逃亡。
她躺在異鄉冰冷的醫院里,已經不能開口說話,生命的最后44天,守護她的,是另一個才認識不久的男人。
她曾說過:“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為我是一個女人。”
她沒有林徽因的理智,沒有張愛玲的決絕,沒有丁玲的颯爽,沒有冰心的美滿。她離世時才31歲,正當風華正茂的年紀,卻嘗盡了人世間的辛酸苦辣,心有不甘。
她以卑微之身,寫出世間冷暖,不恨不怨,一切皆受;
她說自己就是《紅樓夢》里的香菱,“我將與藍天碧水永處,留下那半部《紅樓》給別人寫”;
她在生命彌留之際,留世的最后一行文字是“半生盡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