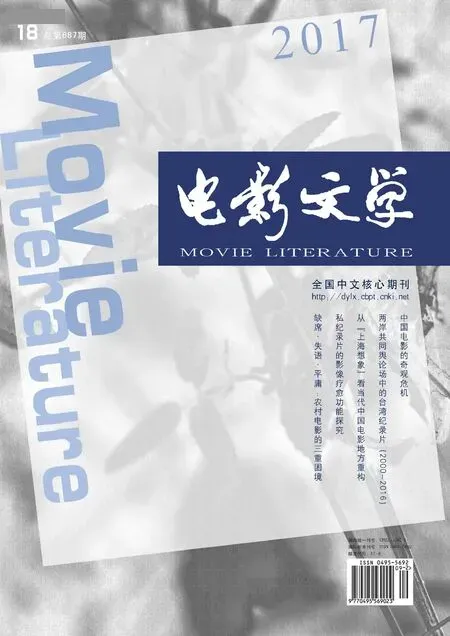兩岸共同輿論場中的臺灣紀錄片(2000—2016)
王 偉
(泉州師范學院文學與傳播學院,福建 泉州 362000)
一、顯影與定影:作為方法的臺灣
在2013年到2017年6月之間,海峽兩岸曾流傳著一個突破主流價值、實現心中夢想的追夢故事。若用“后見之明”回溯,那一時段的故事顯得如此勵志與熱血,而沒有之后終了的惋惜與遺憾。這一故事的主人公據說是一位與德國知名飛行員“齊柏林”同名的臺灣前公務人員。盡管其之前沒有受過正規科班的專業訓練,但為了籌拍一部名為《看見臺灣》的紀錄片,在還有三年即可從現任崗位功成身退的最后時刻,毅然拋棄端了23年之久的“鐵飯碗”,以破釜沉舟的決絕勇氣押上畢生積蓄并四處借貸而募集9000萬新臺幣,投入這部臺灣有史以來最為昂貴的紀錄片的拍攝。據主創人員在各種場合充滿激情與悲情的反復陳述,拍攝過程可謂一波三折、充滿艱辛,除了沉重巨大的經費壓力和齊柏林的先天恐高之外,還面臨影響空拍之復雜多變、難以捉摸的氣候條件。當然根據古往今來眾多耳熟能詳的心靈雞湯,任何暫時圓夢的感人故事,雖有一個起步艱難、好事多磨的過程,但總歸是有志者事竟成,而這一美好瞬間終將被定格下來,以避免日后難以避免的落差與遺憾。與其說為夢想而努力的齊柏林是感人的,毋寧說其講故事的角度與方式是有吸引力的。其勇于投身于讓人仰望的藍天白云間,設想在前所未有的高度觀看臺灣這個島嶼的“美麗與哀愁”,讓島內民眾得以俯瞰朝夕相處的家園鄉土,不僅極其深刻地感動并于日后葬送其生命,也頗為有效地感動并說服追隨他以及能幫助他的人。這些貴人就有享譽世界的大導演侯孝賢,據稱為了方便這位新人籌款,與之并不算太熟的侯孝賢同意出借大名、掛名監制;而素有“臺灣最會講故事的人”美譽的吳念真導演則親自擔任旁白,其娓娓道來的在地嗓音亦為影片加分不少。
氣勢恢宏、畫面精致的《看見臺灣》借助全程航拍的技術賣點與生態環保的議題征用,在島內外贏得意料之外與情理之中的巨大成功,重塑臺灣紀錄片的內容生產與行銷方式。其眾望所歸地榮獲第50屆臺灣電影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獎,令人咂舌地收獲近2億新臺幣的高票房,為臺灣電影在疲軟已久后的復興注入一針強心劑。素來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的各路媒體,在晃過神來后紛紛跟進炒作。“三大報”之一的《聯合報》在歡欣之余,直接將島內民眾的影院觀影升格為一場新的“愛臺灣運動”,借助族群認同的敏感議題造勢營銷。在傳統大眾媒體大肆渲染、網絡社交媒體推波助瀾、觀眾口碑效應持續發酵之下,其社會影響甚至跨越藍綠兩極的政治光譜。“藍營”方面,時任臺灣地區領導人馬英九在副領導人吳敦義、行政部門負責人江宜樺、文化部門主管龍應臺陪同下觀看本片,并指示有司就其所揭示的環保問題進行改進。長期消費環保議題的“綠營”更是不遑多讓,“民進黨前主席謝長廷走進影院觀看,蔡英文則在臉譜網上分享此片上映的消息”[1]。
轉眼間一晃數年,臺灣又完成新一輪政黨輪替,而這位高空逐夢的主人公亦在現實與鏡頭的貼身肉搏中隨風而逝,于一片扼腕嘆息聲中退出歷史舞臺。隨著攝影機背后人物的謝幕退場、漸行漸遠,這一事件引發的輿論熱潮終將平靜,可以預估的是喜新厭舊的各式媒體也會迅速追逐新的焦點,塑造新的追夢人。然而從另一維度上看,或許因為時間的沉淀與過濾、空間的釋放與打開,人們終有可能褪去非理性的悲情,轉而以更從容的理性心態重新打撈這一現象級紀錄片,討論其略帶煽情的“講故事的方式”,反思其鏡頭語法的知識立場與提問角度,并以之為對話對象來探討臺灣的昨天、今天與明天。
著眼于此,試圖從歷史源流驗明現實正身的論者不免要從自我與世界交互關系的辯證視角反身檢討,標榜體現時代熱度與烈度的《看見臺灣》,究竟看見臺灣的什么?進而從“誰在看?”“什么被看見?”“什么又不被看見?”等方面展開論述。或許有心人還能進而指出,處于取景框之外的人們在討論臺灣紀錄片的時候,究竟在討論它的什么?由之,上述問題似乎還可以穿透時間、跨域空間,延展到“誰講述的臺灣故事”“臺灣故事由誰來講述”“為什么要講述這個故事”以及“怎樣講述這個故事”。與“界內”焦點保持若即若離美學距離的我們作為“界外人”,由此敘事學視域來召回歷史或曰進入時空深處審視臺灣紀錄片書寫現實的延續與斷裂,不難發現其恰逢其時的脫穎而出、影展亮相后的浮沉跌宕,并不純然是“化凡庸為神奇”之藝術邏輯的作用結果,而是深刻內在于臺灣社會、東亞格局乃至世界大勢的脈動之中。因之,其定型抑或變異的再現表達、喚醒還是壓抑的選擇過濾、編碼以及解碼的意義生產,盡管具有美學傳統之綿延不斷的接續面容,但無不因現實生存之“緣”而“起”,或隱或顯、或直接或間接地關涉時人對社會記憶與文化資源的激活方式、詮釋態度與時新需求。
二、光的隱喻:“臺灣紀錄”與“紀錄臺灣”
記得兩岸紀錄影像的卓越研究者、“新紀錄運動”的命名者呂新雨教授曾以其悲天憫人的人文情懷意味綿長地指出,“紀錄片是把光投到晦暗的地方”[2]。循此思想取向,處在這一判斷句賓語位置的“晦暗的地方”,顯然是一個頗值得玩味、富有潛隱能量的繁復語碼,其不無尷尬地用于意指“日常之光”未能照進的陰暗角落,如曾被主流敘事話語放逐于邊緣而隱形消聲的“社會棄民”(臺灣少數民族、失地的農民、城市貧民、不同性向者等);再如人們(特別是自詡為本土社會中堅力量的中產階層)熟視無睹抑或不愿正視之庸常瑣碎、刻板無趣的生存狀態;還有那些所有人都不愿回首、不愿正視的某個“有名”而“無名”的時刻。回到句首,僭越主語位置的紀錄片一詞,不僅指涉經由鏡頭“真實”呈現的生存方式,亦關涉攝影主體及其置身其中之歷史觀念敘述話語的內在關系。是以,即使是與人類看似無涉之反映自然的紀實影像(如“流離島影”系列中的“島”,臺灣自然書寫運動中頻頻再現的“荒野”),據說也是為了更好地敞開人類自身的在世生存與心靈腹地。
若對兩岸共同輿論場中日漸升溫的臺灣新紀錄與“后”新紀錄影像(如果有的話)有所了解,或許不難發現,其以自己特有的表現方式成就一種精微而又宏大的時代抒情,從而與大陸曾經風起云涌的“新紀錄運動”高度相似或曰構成巧妙而又微妙的對話關系。一波又一波的臺島影像記錄者(無論是否接受正規的建制內學院教育),一面篤定地追尋眾多前輩的浪漫宣言與工作軌跡;一面執著地以其迫近本源、“見不可見者”的作品質感,慷慨激昂并且不厭其煩地向世人也向自己重復訴說如下信念(實為難以撼動的內心執念):光之所在,本真存焉;“光”之闕如,要么是混沌一片、未曾明朗,要么是虛妄無稽、荒誕悲涼。但是同樣曖昧的是,在一番熱血沸騰、激情燃燒過后,冷卻下來、重返現實的人們是否有可能或曰有必要繼續追問,何為“光”與“光”何為?倘若對臺灣影像的紀錄光譜返本溯源,追索“光”是由何方主體以何方式因何投射?或者換一種不那么玄學化的正常表述方式,現實生存到底是由誰來“記”,其所“錄”者究竟為何物?在這之間,島嶼內外有哪些“遺失的美好”借由取景框而躍出歷史黑暗底層、進入現實光亮世界,在“能指化”的當下世界中錨定自我并為眾人所聞所知、所念所記;又有哪些歷史存在物就此被塵封霧鎖,失卻話語轉述活動中的符號性身份而被本就健忘的人們順勢忘卻?正是在此“屏/憶”的視聽美學意義上,我們或許可以大膽指認,在裂解為碎片化的現實世界中,細膩幽微、真切可感的平實“紀錄”,也許只是重新剪輯而成的“新的歷史碎片”,演化為一種不易察覺的另類遺忘機制,而看似無關痛癢、自我撫慰的“遺忘”未嘗不無吊詭地成為一種另辟蒼穹、清除霧障的反向紀錄活動,緣此這一互相關聯而又錯雜參差的美學鏡語,或許是探究臺灣紀實影像如何跨越鴻溝、整合資源、重構共識的重要入口。
在島外的我們對當下臺灣紀錄影像所顯現之紀實美學精神的本源釋義,顯然不能脫離特定時空分層中的審美心理與情感結構,武斷草率地進行本質主義形上思維的單維釋義與單向界定,而是應該尋繹其后的文本內在肌理與社會規訓機制,反思島內多元主義大纛下隱而不彰、不甚明確的視覺觀看秩序。承前所言,“光”之所至,一方面令人興奮地意味了幽暗洞穴的陡然敞亮,同時也在另一方面暗含了與光共存的陰影遮翳。倘若征用“紀錄詮釋世界”[3]的理論視域透析鏡頭之下的臺灣形象或曰意象,其就不是歷史本相的真實還原與原樣現實的自我糾纏,而是現實缺席之歷史記憶似有還無、似無還有的今朝重構。在“紀錄片社會啟示錄”論者看來,新一代與后新一代之臺灣形象的歷史記錄者,其矢志不渝、上下求索的記錄目標,不應僅僅停留在對這方水土及其所養育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進行纖毫畢見卻空洞譫妄的“實錄”,或是巨細靡遺卻言之無物的“紀實”,以供今人抑或后代、自己抑或他者做空閑之余的文化緬懷;而是應該秉持“讓不可見的被看見,將不可留的留下來”的紀錄理念,正視其介入現實風云變幻、書寫異質性記憶、重組生活世界的媒介本命。
三、島嶼邊緣:社會紀實中的精神私史
全景映像工作室創始人吳乙峰曾經有言,“紀錄片對我們來說只是工具,我們關心的是社會弱勢者、社會議題這部分”。若以這一紀實理念來重審新世紀以來的臺灣新紀錄與“后”(“新”)新紀錄影像,我們不難發現其再現歷史、再造真實的觀念形態訴求。君不見,無論是嘗試刻畫“二二八”事件這一歷史性能指之當下所指的《證言二二八》(藍博洲,2002年)、《還原二二八》(王育麟導演,2005年),還是企圖呈現世紀之交臺北“廢娼”事件的《公娼啟示錄——一群臺北妓女絕境求生的故事》(蔡崇隆導演,2001年完成),抑或是細膩顯影臺灣男性沙文主義籠罩下艱難生存的外籍新娘(《我的強娜威》)與“同性戀的‘私角落’”[4](周美玲,2001年),當中浸潤著現實溫情的人文關懷與審美激情的浪漫想象,無一不指向創作主體之為主體(盡管不一定是舊啟蒙主義式的“大寫的人”)的鏡像式詢喚。質而言之,在彼此映射、交相輝映的審美光譜之下,作為思想布道者與未來預言家的傳者,宛如中華上古神話中“與日逐走”的巨人夸父,胸懷大志、矢志不渝而主體性日漸顯現、存在感日強。與之相應,以聆聽者與受教者姿態呈現的蕓蕓觀者,亦在前者同情式的鏡頭誘導乃至審美詰問中猛然開悟,上述“光”的投射就是新啟蒙乃至后啟蒙(通常以“反啟蒙”為其現實假面)理念的現實投影,即運用并未如期而至的新舊啟蒙之光(Light)去“照亮”(Enlighten)周遭世界與內在心靈。是以,在文本互涉、復調多聲的光影游戲之中,本已麻木的邊緣人物與久經壓抑的懵懂大眾被眼前光亮一朝喚醒,開始反思“存在的不合理”與“不合理的存在”,觸碰“合理的不存在”與“不存在的合理”,從而在見出端倪的“蒙啟”之后成其為不再“中空化”的“人”(想象性地獲取美學意義上的主體性地位),甚或啟蒙渾渾噩噩、睡夢正酣的他者。
新世紀以來,特立獨行、爭議不斷的臺灣紀錄片創作者,盡管在政策明面空間與輿論生態表象較之對岸同行似乎更加開闊,但正如我們所注意到的是,二者在制作經費與行銷費用等方面同樣面臨相同的窘迫情況。難能可貴的是,他們不改初衷、砥礪前行,一方面拒斥與主流合謀共同復制資本社會的話語結構,拒絕在景觀化社會中講述順滑流暢、搖曳生姿的資本故事,格格不入地堅持運用鏡頭直觀權力罅隙中跌宕起伏但鮮有人問津的民生百態,彌補或曰平衡島內大眾新聞媒體急功近利地追求“新、怪、奇”的片面與缺失;另一方面也急于超脫其本身亦未能妥善解決之“客觀記錄”的藩籬限制,適當融入實驗影像注重主體意念情緒的審美傳達,不乏敏銳地墾拓臺灣紀錄影像之新的美學空間。顯然,這一文化實踐背后的美學追求足以讓身處對岸的大陸同行心有戚戚,為之(為己?)擊節而嘆,也為之(為己?)悵然不已。毫不夸張地說,在“我和你們聽他們講我自己”[5]之后,那些被權力話語吸納其中而又放逐之外的“我們”,反身拷問那些以倫理之名復制既定結構的重重幻影,并通過“尋找自我”的“自我表述”來促進與自身生存緊密相關之現存價值體系的適度調整。正是在這一交互主體性存在論美學意義上,兩岸新紀錄影像雖然表面上花開兩枝,但在文化根性上一脈相承。其所反復重申的“真實性”,明顯不等同于以“跟蹤拍攝、同期聲、長鏡頭、客觀記錄”[6]為特征標識的紀實戳記,“畢竟上述技術表現手法類似稀松平常、無甚稀奇的萬金油被廣為征用,從而為林林總總、層出不窮的虛構文本抹上所謂的真實光亮”[7]。如有論者頗具識見地指出,“紀錄真實”并非不需論證、無須描繪的自在自明自證之物,其不容忽視地聯系著現象學顯現的“意義真實”。因之,其并非單純意指工具層面舉世皆有卻無以言說的技術真實,否則那些無所不在、無微不至、無孔不入的大小監控裝置,豈不成為現成世間簡單有效的最佳“紀錄”?進而言之,費盡周折地分離主流話語但卻承認并保留個體話語的“本真紀錄”與“紀錄本真”,乃是詮釋美學意義上的“理念之真”(“價值真實”),其作為一種建構而成的基本話語事實,殷切征召主體意識的最終形成與道義擔當的審美介入,進而在紀實當下、書寫歷史的綿延想象中構筑共有記憶與身份認同,最終成就對兩岸現實的超現實審視和對兩岸歷史的超歷史質詢。
四、結語:“因歷史顯影”與“為時代留聲”
長期以來,臺灣紀錄片在全球本土化語境中深耕本土、不忘初心,在明面邏輯上依然徘徊在“紀實精神”為其影像詩學的本體追求,卻極具癥候意味地充溢著濃郁在地色彩的創作激情、現實溫情與文化悲情,因而呈現出抒情性與現場感匯融交織的美學特質。其念茲在茲、魂牽夢縈的“真實性”,并非自足存在之與主體價值無涉的純然客體鏡像。恰恰相反,本真性作為普泛意義上的紀錄片美學內核,乃是公共空間中不同主體進行對話協商、尋求共識的想象物,并在不期然間演化為一套繁復豐贍、動態開放的意義系統,故而與其將之說成是一種創作手法,毋寧視之為一種美學承諾。處于轉型焦慮、急于突圍的臺灣新紀錄影像,在原型層面投其所好的受眾心理捕捉上,有意無意、自覺不自覺地試圖滿足島內中產階層(敘事視點的占有者)在庸常生活中窺探他者隱私的獵奇心態,真切顯影已然跨入后現代消費社會的臺灣文化癥候。在現實層面的社會議題表達上(如歷史記憶的當下重構、鄉土情懷的影像傳達、身份認同的多維透視、生態議題的立體呈現等),其以“雜語共生、眾聲喧嘩”的復調話語結構,小心翼翼地穿透時代素描與社會寓言的文本關系網絡,悠然恰如地映射草根性的民間素樸話語、操控性的觀念形態話語、知識者的外來啟蒙話語、商業化的跨國資本話語在多元輿論場中既彼此托舉又劇烈競逐的博弈關系。在審美層面的理想建構上,其又以謙卑而又敬畏的美學姿態鍛造主體間性的生命影像,慨然允諾每個主體都有進入光亮的權利與可能,欣然表現出對生命平等理念的肯定與尊重,對社會異化狀態的反思與超越,在忽然敞開與驟然遮蔽的相互作用中悄然建構兩岸共同輿論場中的另類美學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