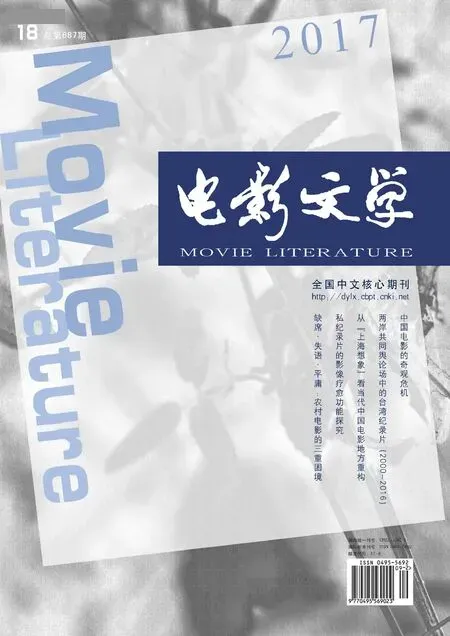從“上海想象”看當代中國電影地方重構
汪黎黎
(南京藝術學院傳媒學院,江蘇 南京 210013)
作為當代最重要的文化想象媒介之一,電影在全球化的語境中又是如何重構地方的呢?當代中國電影的“地方想象”正通過“多地性”的地點建構策略,用更為開放性的影像文本重塑著地方的面相,與全球化、本土變革等現實因素開展著積極的互動,這一重構過程潛藏著復雜的權力關系和豐富的文化意義。本文所謂的多地性,是指在一個影像文本內部,通過遷徙、交通、通信、想象等各種途徑,使某一個地點與其他地點之間互相連通,并以此構建起敘事基本框架的策略。以“上海想象”①為例,一是因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電影對上海發起了大規模的集體想象,顯示出重構上海的熱切欲望,這是電影重構地方的典型現象,也生成了大量典型的多地性文本;二是由于上海是中國一個頗為特殊又具代表性的地方,它有著復雜的歷史身份,如今又身處中國改革開放和全球化的前沿,“上海想象”中地方性和全球性的博弈頗具典型意義。
一、多地流動中的地方性書寫
在當代中國電影中,雖然全球性面相日益突出,但多地性文本中的地方性書寫并未減弱。它們將地方文化傳統在當下,特別是在多地流動中的表現形式進行想象性的再現,以喚起集體記憶的方式強化對地方性的認同。比如在近年來的“上海想象”中,黃浦江、蘇州河等典型的地方自然景觀,石庫門、弄堂等具有時間感的地方性老建筑,成為眾多流動故事的聚集地;穿越歷史風霜的老人成為承載地方性的中介,他們的人生經歷是整個城市歷史的縮影,地方性通過他們穿越幾個時代的記憶凝結成帶有個體性的情感文本。
地方性是經時間沉淀和發酵后的產物,但同時也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斷變遷,電影中的上海人形象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西方文化地理學者西蒙(Seamon)將人的日常生活實踐稱為“身體芭蕾”,而由許多當地人的日常生活所合演的就是“地方芭蕾”,這種“地方芭蕾”所上演的舞臺是能使個人及群體產生良好“地方感”的空間。②電影通過對上海人日常生活的展示,滲透出本地普通人在逼仄空間中的生活哲學,流露出交織在當地人生活空間中的思想觀念。《我很丑,可是我很溫柔》中的肉嫂,《股瘋》里的范莉、三寶和一眾小股民,《美麗新世界》中的金芳,《股啊,股》中的阿莉,《姨媽的后現代生活》中的姨媽和水太太等都是典型的上海人。正如著名上海導演彭小蓮曾說的,這些人“是現代和保守,善良和狡猾,精明和守法,各種品質構成的,……他們的品質和性格是那么矛盾,所以這個城市也常常顯示出她的‘上海人氣質’”③,這種矛盾性恰恰構成了上海地方性的獨特魅力。值得一提的是,在多地性的文本中,上海人往往在與外來者的對比中顯示出鮮明的性格反差,他們大多伶牙俐齒、愛面子,有著精明、重利、世俗的一面,但同時也具有小市民身上樸素的善良和生活的智慧。上海人通常在與外來者的接觸、交往和較量中,逐漸激發出性格中向善向上的一面,修正自身性格中勢利、拜金、唯利是圖等缺陷。在這些上海人身上,既濃縮了上海的城市性格和文化氣質,又折射出上海在新的時代語境中對自身地方性的某種反思。
二、全球經驗中的地方認同
當代文化地理學認為,關于地方的知識和意義,并非來自地理學家、社會學家們的專利,也不是出自宏大話語體系下的闡釋,是主要由個體多樣化的地方認同所集聚起來的。羅德曼主張將地方建構成一個激勵人們用不同方式對話和相處的概念,并認為地方的反思關系,需要多地的(multilocal)分析方法才能呈現意義。他所謂的“多地的分析方法”,是指“單一的物理空間可能是多地的,因為它為不同的使用者塑造并表達出多元含義(polysemic meanings)”④,也就是通過“地方使用者們”不同的地方認同來分析地方性。電影在重構地方的過程中,這種“多地的方法”必然包括將地方置入和其他地點連接的網絡中(也就是本文所說的“多地性”)進行考察,因為不同地方認同的建構是與跨地流動分不開的,這種跨地流動包括人群的移動,移動中的人們在情感上有可能產生對多個地點的認同;也包括“資本、創意、影像、商品、生活方式、服務、疾病、技術以及交流手段的流動”,因為“媒介信息的流動代表了無需人的移動的跨地性的主要形式,所以即使人們留居本地,他們的主體性仍有可能被跨地性的過程(比如電視媒介)所改變”⑤,多重意義上的地點流動直接改變了人們對地方的認同方式。
“上海想象”提供了一幅在全球化背景下考察多元地方認同的圖景,電影中的人在跨越地理邊界的過程中形成了對上海不同的認同方式,不斷豐富著上海在全球經驗中作為地方的意義。“上海想象”中,許多角色對上海的認同是在跨境流動的過程中實現的,他們本身是全球文化基因的攜帶者,以他們為中介,全球性和本土性在上海空間發生了諸多化學反應,地方認同的建立標志著兩者互補過程的完成。
旅行,作為跨地流動的主要方式,是打破穩定慣性的潤滑劑,是向地方開放空間的方式,是激起文化碰撞的機緣。“上海想象”中經常設置異域旅行者的角色,他們在上海或長或短的旅程,啟動了全球性和本土性的文化攪拌機制。《上海假期》中來上海爺爺家短期度假的小華僑顧明,起初對中國傳統的倫理價值觀無法產生認同,但后來落難鄉間被救助的經歷使他對爺爺家所在的社區產生了認同感。在另一個方向上,顧明身上的全球性價值觀也給代表本土文化的里弄帶來了新鮮的氣息。顧明對上海的認同是建立在對本土文化尋根的意識形態之上的,雖然本土文化在全球性面前顯示出強大的馴化力量,但片中停留在前現代時期的上海社區依然對全球性中自由開放的氣息展現了包容、歡迎的姿態。《最后的愛,最初的愛》中,在故土東京遭遇愛情、友情雙重背叛的早瀨因跨國公司工作調動來到上海,他遇到了代表著本土性力量的方敏一家,繼而對上海產生了地方認同,為此他最終放棄了“全球人”的身份(跨國公司員工),上海的本土性面向再次想象性地顯示了其在全球性面前的反抗性力量。
借助外籍人士的地方認同,電影中的上海被想象為一個全球性和本土性相互包容、雙向互動的“全球—本土城市”,而本地人的地方認同,也同樣在兩種力量的張力之下強化著上海的這一地方屬性。《股瘋》展示了上海在20世紀90年代股市這一象征全球性的金融大潮沖擊下的眾生相,劇中人對上海的認同基本可以等同為對金錢的瘋狂膜拜,但這種“荒誕和非理性”的地方認同恰恰是全球性沖擊之下本土性的一種體現。與西方社會對商品經濟的長期涵養不同,中國與這一浪潮的接觸幾乎是電光石火般的,在毫無商品經濟意識和知識的儲備下,瞬間涌入的金錢投機誘惑必然產生非理性的都市狂熱。《股瘋》中本土性的張力還集中體現在主人公范莉身上,她“在影片中是本土和全球的中介人。她一方面由街坊眾人民主選舉為投資代理人,為‘本土’利益服務,另一方面又與全球交易,出入股市貴賓投資室……范莉的“主動性”是一種混合物,混本土(街坊)與全球(金融)于一體,代表新興的上海”⑥。
在多地流動甚至全球流動的經驗中挖掘新的、多重的地方認同,是當代中國電影重構地方的重要方式,張英進稱之為“重寫”。他認為全球性所帶來的“文化消失”只是一種可能性,而“重寫就是一種進行重新本土化、重建主體性和重新獲得歷史主體身份的有效方式”,在這種策略下,“本土性也還是不可避免地會找到方法在世界性霸權話語的跨國、跨地區空間中重寫其自身,方法就是在面對其預測中的消失——如果還不是其已被宣稱的死亡時——斷然聲稱其自身的差異”⑦。
三、多地流轉的現代“傳奇”
在文學范疇內,傳奇以摒棄、超越日常生活和庸常人生的飛揚,成為一種夢幻性的文本。在當代中國電影書寫地方的多地性文本中,常常通過一個個跨地流轉的故事,塑造一個“集多地為一體的地方……一個孕育傳奇并將其作為一種特殊敘事方式的地方,一個通過這些傳奇的流動來強化自身地位的城市,一個不斷通過聚集和離散來轉移和擴大其邊界的地方”⑧。在全球化時代更為頻繁的聚集和離散中,地方不再是古老史詩的詠嘆之所,而是現代性傳奇的大舞臺。
在許多“上海想象”中,上海從一個“人來人往的碼頭”進一步被建構為全球流動中的樞紐站——既不是出發地,也不是目的地,只在此做或長或短的停留,“他們攜帶著各自的史前史故事從原生地啟程,譬如日本、美國、丹麥或英國等,而經濟全球化浪潮帶給他們得以暫時駐留上海的工作合約”⑨。旅行中轉中頻繁的來去、短暫的停留、偶然性的事件等,為充滿巧合的邂逅、瞬間迸發的默契、爭分奪秒的廝守以及宿命般的分離、傷感的結局等傳奇必備要素提供了充分的敘事契機。《夜·上海》故事的傳奇性在于突破日常戀愛程式的快速升溫的男女情感,這種快速升溫需要一系列戲劇性的事件作為鋪墊,同時,語言不通所帶來的交流障礙、水島頂級發型師的時尚職業、林夕灰姑娘般的愛情眷顧等都增添了其作為都市傳奇的夢幻色彩。《窈窕紳士》中每一個主人公都自異地流動而來,在上海這個中轉站相遇,然后上演了一出令人啼笑皆非的現代“變身”傳奇。《紅美麗》中在上海逗留的是美國人邁克,他的“上海傳奇”更加曲折離奇,復仇、愛情、背叛、火并、犧牲,交織出足夠濃重的傳奇氛圍。
在多地流動的傳奇故事中,還常常流露出一種漂泊感。《新十字街頭》里四海為家的黑人音樂家,《夜·上海》中經常輾轉世界各地的酒吧駐唱歌手,《美麗新世界》中被寶根視為知己的地下歌手阿亮等,都是現代意義上的都市流浪者,他們居無定所,來去自由,整個世界都是他們的暢游之地,上海只不過是他們漂游旅程中暫時停靠的站點,而下一站將去向何處,則一切隨緣、隨性。這些在全球化境遇中四處漂泊的人瓦解了固定的家園,游蕩出一種不安定的斷裂感和破碎感,但是沒有疆界的生活、體驗和存在又散發著自由的理想生活的氣息,而自由正是上海的地方性在當下的核心價值之一。有關漂泊的現代傳奇不僅僅只具有滄桑、傷感的底色,它們更體現出對掙脫命運枷鎖、超越生命極限的向往。
正如張英進所說,中國電影“重寫”策略的力量不容小覷,它可以為中國地方在影像的世界里開辟出一個新世界,“標志著這一新世界的,是同時性與多樣性的混亂,是相互競爭的意識形態和生活方式,是跨越了全球性與本土性之間所有空間范疇的不斷移動,是互有交疊的界限和不斷變化的關系,也是現存體系中的裂痕與縫隙,它們喻示著新的自由與新的機會”⑩。在這種“裂痕”和“縫隙”中,一種有關自由的啟蒙意識,一種更具普世意義的平等、民主的價值觀,在“地方想象”的文本中逐漸滋生和蔓延,這無疑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國電影重構地方的革命性意義。
注釋:
① 本文中指以上海為主要敘事空間的虛構電影。
② Seamon D:AGeographyoftheLifeworld:Movement,Rest,andEncounter,Croom Helm,1979:148.
③ 彭小蓮、賈磊磊:《都市的文化影像與心理空間》,《電影藝術》,2004年第2期。
④ Margaret C.Rodman:EmpoweringPlace:MultilocalityandMultivocality,in Setha Low and Denise Lawrence-Zuniga,eds.TheAnthropologyofSpaceandPlace,Blackwell,2003:212.
⑤ 張英進:《全球化中國的電影與多地性》,《電影藝術》,2009年第1期。
⑥ 張英進:《中國城市電影的文化消失和文化重寫的方式》,《電影藝術》,2004年第4期。
⑦⑩ 張英進:《影像中國:當代中國電影的批評重構及跨國想象》,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363頁,第340-341頁。
⑧ 張英進:《賈樟柯的〈海上傳奇〉與多音性、多地性的都市敘事》,倪祥保:《華語電影如何影響世界:當代華語電影文化影響力研究國際論壇論文集》,蘇州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34期。
⑨ 聶偉:《想象的“本邦”與“看不見”的城市》,《當代電影》,200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