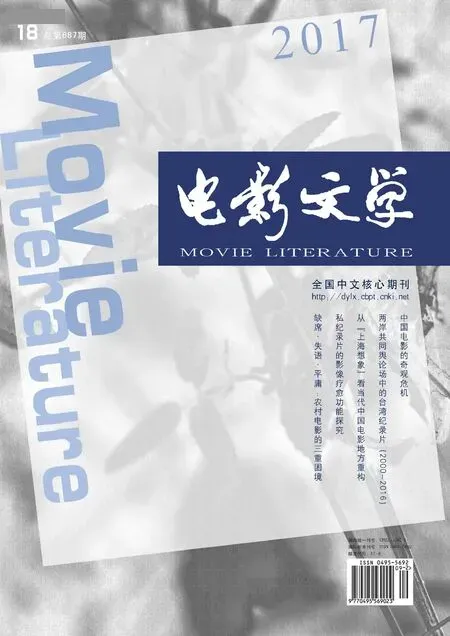論英美電影中的軍旅文化
張樹光
(赤峰學院,內蒙古 赤峰 024000)
軍旅題材所展現的主旨,在英美影片中不斷地以或隱或現的原型母題出現,這已經不單純只是一個抽象的美學命題,而是如杰姆遜所說的“文化深度模式”話語場域,其與現實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大眾心理結構有著復雜的對話關系。起初,軍旅文化主題的發展、派生僅僅依賴于西方本土文化,后不斷地加以模式變形,構建起一套世界性成規化的敘事和影像體系。其結構模式著重展現惡的毀滅、暴力的宣泄、正義的勝利,夾雜樂觀而感傷的情緒和超越現實的宗教情懷,成為民族集體無意識和心理積淀的外化與再現。從其內部生發譜系考察,當英美世界還只是處在攝影機和轉動架剛剛研發的階段,軍旅文化題材便成為其重點關注對象,諸如《戰前和戰后的后備兵》(1900)、《將軍》(1926)、《鐵騎》(1924)等早期影像產品。近幾年的英美電影不再僅僅局限于軍旅,而著重偏向于文化闡釋的深度,如倫理敘事、現代性,對這個題材電影的探究,打開了了解英美電影結構系統乃至文化傳統的一道隱微窗口。
一、傳統倫理訴求背后的現代性“迷思”
英美軍旅題材影片因其折射出的文化意義,形成了具有特定風格的類型片。它的誕生、發展、繁榮,與英美文化傳統中的“英雄史詩”“騎士文學”“西部傳說”等有著深刻的淵源與對應關系。基于文本模式的變形、替換,此類型片形成了以戰爭為主要敘事背景,以文明與野蠻、邪惡與正義、個體與國家等基本矛盾為主題范疇和文化形態的模式。在社會心理、價值架構、審美塑造上,其呈現為既有傳統倫理的訴求表達,又貫穿著現代性的“迷思”敘述。
首先,戰爭主題的想象性表達包含著一套英美軍旅文化的價值觀機制。此類型片中,社會準則、道德倫理、國家忠誠與個人情感等,形成彌合社會通行的價值系統缺陷的一種倫理訴求,與官方的意識形態一起參與英美文化觀念體系的建構,同時也為電影戲劇性沖突提供復雜而微妙的表現空間。英國電影《百戰將軍》(TheLifeandDeathofColonelBlimp,1943)就是此文化景觀樣本。影片里的懷恩肯迪將軍,在對其戎馬生涯的講述中,充分展現英美系軍旅文化敘事里慣見的崇高和人性力量。其中既有將軍充滿智慧和勇氣的戰場指揮,又有其與軍官Theodor間感人的情誼,當然還有他和亨特小姐的生死愛戀。片中,一般社會中的職業區分準則,悄然讓位于人物在非常態社會關系中所展現出來的情感張力,這既滿足了大眾在現實生活的抑制下深埋心底的宣泄訴求,又呼喚和想象著超越社會真正需要的情感和價值追求,成為深度參與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建構的大眾文化產品。可以說,這類軍旅題材的電影,在或隱或現的層面上,都表現出其內在意識形態機制對觀眾的建構性詢喚,明顯帶有英美文化倫理色彩的價值認同表征。
其次,現代性的反省與“迷思”。影片敘事策略往往都是通過縮影化表述來完成,其敘事不僅指涉現實中的社會生態,也將潛藏的隱喻關系透過內構化處理得到反諷式表露。當前,軍旅電影不再停留在過往題材電影的正義必勝、國家至上、榮譽大于生命等簡單的價值認同上,而是展現出現代性的反思。科波拉執導的《現代啟示錄》(ApocalypseNow,1979)將隱含的社會情境放置在越戰期間柬埔寨一系列具象化的視覺圖譜之中:蒿草叢生的原野、餓殍遍地的難民、血肉橫飛的士兵尸體、空曠而寂寥的所謂戰場,這一荒蠻地帶隱喻任意放逐的無序的現代荒原,戰場成了現代法庭的審判大廳,場上的軍旅人員參與構成了一副傳神的現代眾生相。而正與邪二元對立的思想觀念、國家榮譽與人道主義的分裂、文明與野蠻的模糊等問題,都得到了視覺化的闡釋和表達。影片中,當庫爾茲上校叛變的消息傳到美國,留居戰場的士兵是本能的恐懼,只有維爾德上尉在憂心忡忡地試圖抵御自以為即將面對的邪惡。可他真正踏上荒涼的河岸一角面對庫爾茲上校時,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鮮明地投射到了自己身上,讓這位昔日壯志滿懷,象征著秩序建立者、維護者的軍官黯然神傷,他同樣轉變為孤獨的離索者。影片里所透露出的現代軍旅世界,不再只是集中于正義戰勝邪惡的一元化陳述,而是轉化為自我拯救和自我揚棄的歷程,以及對現存社會秩序、價值理念與“理性”質疑的現代性敘事,當然還有“上帝死了”之后人們面對荒誕境遇無所適從的現代性焦慮。
二、話語權的爭奪
英美文化傳統向來注重從理性主體層面培植人性的完善和自覺,強調勇敢、忠誠、紀律,人道主義、個人自由、國家至上等基本品格,并將其構建為民族文化—心理結構,使之成為大眾化的生命價值觀。在此集體無意識觀念的影響下,軍旅題材電影很自然地成為其意識形態施展的主戰場,權力話語和電影制作者的自覺實踐成為宏大敘事的一個重要介體,明顯透露出承載中介價值的存在信息。
一方面,軍旅題材電影始終閃現著權力話語的影響。盡管在英美電影里,但凡涉及軍旅文化書寫時總不忘灌輸其意識形態價值理念,注重在軍人群像的審美表現上傳達出一種緣于偉大犧牲和無私奉獻的崇高美,擅長在一些充滿人道主義敘事的感人細節中托起其價值表現意圖,從而激發民眾強烈而純凈的審美情感和愛國情懷。但實際上,敘事總是無法全面覆蓋的,故而在對軍旅文化的遮蔽性講述中,依然無法掩藏其中權力之杖左右個體命運的現實。說到底,軍旅的生活世界是一個權力話語格外盛行的角落,個體的命運乃至精神實體都被灌輸完全服從國家、集體、隊伍的安排,代表集體主義話語的組織機器處處展露出“利維坦式”的真實面貌。電影《叢林雇傭兵》(CobraMisson,1989)就隱現出這樣的軍旅圖景。在影片的一開頭,就出現了殘酷的淘汰式訓練,對格斗、射擊場面及教官語言侮辱等場面的特寫,意在凸顯這是一個沒有個人選擇自由的空間。軍官們穿著象征階層界限標志的制服,趾高氣揚,而受壓迫的士兵們嚴肅的面部表情,不斷地印證著這一情緒表達:為了遠離閉塞、強權籠罩的軍旅生活,始終不懈地做出各種軍隊體制內的努力和抗爭,盡管抗爭過程令人潸然淚下,但在權威壓迫面前,士兵們總要付出悲愴性的代價。在這些影片中,軍旅世界成為權力王國的符碼,權力話語透過軍隊無可爭辯的層級制形式束縛和壓制著個人,個體身份在組織機器的巨大陰影下無可遁形。
另一方面,與權力話語壓制敘事對應的,是生命救贖審美情感的無處不在,軍旅電影以此構建軍旅文化的超越性色彩。英美電影中一個慣見的模式是軍旅文化的展現一般不會只停留在劇情的寫實性營造中,或者對各種軍旅現象單純地描繪,而是會把軍旅敘事上升到本體論的意義層面,思考其終極意義。這也是英美電影軍旅題材最顯著的敘事特征。在大衛·阿耶執導的名作《狂怒》(Fury,2014)里,刻意營造骯臟、虛幻、荒蠻、壓抑的軍旅環境,結尾處唐·柯利爾和劫后余生的兄弟帶著心靈的創傷準備逃離那個死亡縈繞的軍旅世界,導演卻出乎意料地讓他們逐漸走向生命毀滅的殘酷結局。柯利爾在荒原中,面對天地,悲愴而絕望地質詢,其所凸顯的戰爭、死亡、生命不再只是銀幕上的假設性的“存在主義”,而是內化為集體性的生存體驗和價值思考,民族國家的宏大敘事轉而為人類普遍性命題的探尋敘事,成為一種超越救贖的話語實踐。
三、國家形象的重塑
“史詩”性的內容和場景需要宏大的形式。面對軍旅、戰爭這些人類世界最集中、最殘酷的災難敘事,一般性、單一化的表現形式往往顯得單薄淺陋或力不從心。英美國家對這個題材的駕馭能力,所具備的經驗及創造性展示,與世界其他文化族群影像生產相比,是遙遙領先的。尤其是重建文化背后的心理動機,值得深入挖掘。電影史家蘭斯·莫羅認為,從國民意識形態的角度做“考古追究”,源自20世紀后半葉之后的英美的各種戰爭經歷,一元化的霸權地位受到挑戰,且隨著蘇聯的解體,他們失去了用來衡量自身品性的道德對立面,使得西方國民無法繼續“享受”長期以來的體面姿態和優越感。因此,英美國家只能借助對軍旅及其依附的文化形態不斷地反思,篡改民眾的記憶,繼而才能重新定義“自我形象和國家典型”。
第一,軍旅題材影片暗含著英美國家價值觀的“政治化”暗示。在這些題材影片里,觀者總能看到主角無論時空、財富、地位和處境如何變化,卻始終能堅守自己的理想和價值觀。而在影片的結尾,我們也慣常地看到,戰爭中最終的幸存者必是自覺維護英美式主流道德、價值觀之人,他們忠誠、樂觀、勇敢、重視家庭價值。這些電影表面上呈述的是一個軍旅文化面向,而實際上是傳達一種帶有強烈印記的英美傳統價值觀具有永恒性和普世性的暗示與實踐。《拯救大兵瑞恩》(SavingPrivateRyan,1998)是其中通過軍旅文化主題滲透英美價值觀書寫的經典樣本。影片在開場就書寫了戰場的殘酷,濺滿了水珠與殷紅鮮血的鏡頭,登陸士兵的痛楚和無畏犧牲,以及士兵尖叫或搜找斷肢的地獄般的景象。而充溢整個銀幕的美國國旗,則為影片打上了英雄主義和美國必勝的印記。而片中瑞恩的兄弟、母親聽到噩耗后癱倒在地的悲情場景,國防部工作人員兢兢業業在角落打印出陣亡通知書的嚴肅畫面,一位美國老人和家人默默走過令人肅然起敬的諾曼底陣亡者公墓的場面,又使得影片擺脫單純的現實主義和軍旅文化展示,而是沐浴著與英美價值觀有關的、崇高的愛國主義的光輝。
第二,軍旅題材影片肩負著英美國家形象重塑的重任。這是一個從電影藝術到現實現象的轉化過程,旨在通過直觀影像對戰爭文化的闡釋和美化,引發情感價值上的共鳴,并將此理念形象化,成為構建自我民族道德主體想象的“表述中繼站”(discursive relay station)。《阿甘正傳》(ForrestGump,1994)里,對美國軍旅文化的社會性表述,就明顯地傳達出這樣的意圖。影片將越戰歷史做了技術性修改,與其說是正面表現戰爭場景,不如說是通過美國軍隊里士兵的情感生活、精神風貌、價值體現,來灌輸一種傳統的普世文化體系和美德。影片中透過閃回行進的插曲性陳述,都由此觀念意圖所主導,組合創造出了一個個可愛可敬的美國大兵和可供重新利用的形象化敘事。如片中反復播放的反戰歌曲《幻想》,約翰·列儂原本賦予這首歌的是描繪物質主義、民族主義和宗教情懷,表達對和平的渴望,但在軍旅生活中,卻使之完全成為美國主義的宣言;丹中校在槍林彈雨中的勇敢、忠誠和對士兵的愛護,是對國家至上與個人價值同等重要的國家意識的書寫;阿甘與丹中校談話言辭中所流露的明顯是對美國軍人“所有的好品質”、美國消費主義和基督教信仰的熱愛,影片借助阿甘之口完成了從軍旅革命到美國道德主體頌揚的過程。由此,軍旅題材電影成為英美世界改造視覺記憶、歷史神話、凝聚國家信仰和價值觀念新的場所。
綜上,英美電影中的軍旅文化敘事背后,有著深厚的社會心理基礎。這些影片的敘事結構和審美特征,既有國家主流意識形態的滲透,也有著超越英雄主義、愛國精神灌輸層面的個人化、日常化體驗,以及對生命的思考的深沉意旨。英美電影對軍旅文化的展示,對我國電影人的創作無疑是一種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