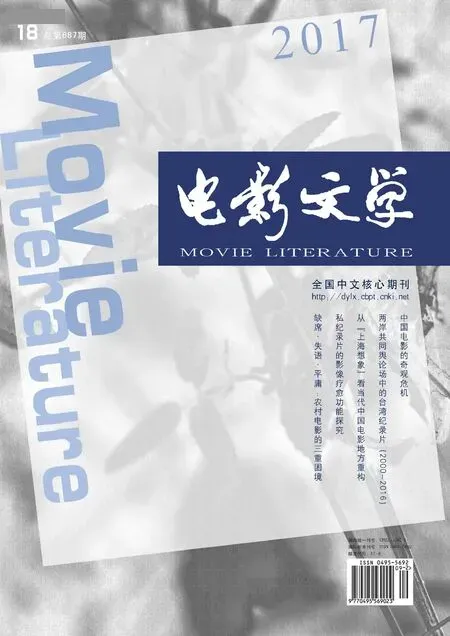《東京物語》的和式之美
于 勇
(中原工學院,河南 鄭州 450007)
已故日本導演小津安二郎被認為是最擅長表現日本“況味”的導演。在他三十余年的藝術生涯中,他留給了觀眾《晚春》(1949)、《秋刀魚之味》(1962)等一系列影響了一個時代的經典作品。而其中被認為是“經典中的經典”的則要數在2009年的評選中一度擊敗《七武士》(1954)當選日本電影最佳的《東京物語》(1953)。《東京物語》之所以膾炙人口,受到日本國內外觀眾的肯定,很大程度上在于小津安二郎根據自己對日本文化的理解在電影中體現了一種與眾不同的和式之美,當20世紀日本導演都在探尋本國電影出路的時候,小津與他的《東京物語》奠定了一種屬于日本的美學規范。
一、《東京物語》與物哀美
小津的幼年時代長期在松阪度過。松阪最為著名的人是日本復古主義的代表人物本居宣長(原名小津富之助),系統而完整地總結出了日本審美文化中的物哀美。而小津安二郎與本居宣長之間在具有親緣關系的同時,更繼承了本居宣長對物哀美的重視。小津于1959、1960年接受采訪時,曾反復表示,其電影的關鍵詞便是物哀。
早在8世紀的《古事記》、11世紀的《源氏物語》誕生的時代,日本人就有了對物哀美的自覺追求。《古事記》中的哀傷、憐憫以及由外物引起的共情等被《源氏物語》發展成了一種夾雜了贊美、喜愛、可憐的復雜情緒。本居宣長則認為有趣、可笑等也都可以算物哀。一言以蔽之,在和式美學中當人的理性退位于感性和直覺,人的心靈為強烈的情感所充斥,這種情感再經過一種藝術提煉,就上升為美感,也就是物哀美。但單純就小津安二郎在采訪中提到的物哀美而言,他所更傾向的物哀依然是一種憂傷,一種人在面對暗流涌動的人生時備感無力、滄桑的情緒。
從主題來看,小津電影中反復出現的便是日本的(或可說是儒家文化圈中的)傳統倫理以及它背后的文化美感,這正是小津電影物哀美的來源,也是小津電影最為迷人的地方。小津電影猶如精準的手術刀,讓觀眾清晰地看到,這個當代社會并不可能實現傳統倫理理想中的和諧,而正是在這種不和諧中,悲哀和無奈感便油然而生。
小津本人終身未婚,但是對于日式家庭的生態他有著深切的洞察。從他的其余幾部電影中不難看出,他能夠以極為巧妙的方式表現日本已婚男人在性上一邊高度壓抑,一邊高度放縱的矛盾狀態。在小津的絕大多數電影中,家長里短的、看似平平淡淡的瑣碎小事占據了電影的絕大部分敘事篇幅。但也正是在那些就戲劇沖突性來說毫無張力與激情的情節中,隱藏著太多溫情與悲哀,這些都是小津留給觀眾反復琢磨和回味的。在講述了平山周吉夫婦去東京和大阪探望子女這個簡單故事的《東京物語》中,一生沒有子女的小津精準地把握住了為人父母與為人子女的各種感受。單純從電影主干來看,《東京物語》可以總結為子女在成年后各自婚嫁成立了小家庭,離開了父母,而父母只能孤獨地度過自己的晚年。而細分下去又可以看到,小津對于這種“空巢老人”現狀的認識又不是片面的,比如有著不同生活狀態、生活經歷的子女,他們各自的“不孝”背后實際上有著各自的無奈之處。當年邁的父母生活在孤獨中時,這些人到中年的子女實際上也被孤獨和其他負面情緒所困擾。如長子幸一身為一個醫生,同時也是兩個兒子的爸爸,不僅有著職業責任,開著診所一有病人隨時就要出診,同時也有著家庭責任,即使只是為了撫養兩個兒子,幸一也要不辭勞苦地出去工作,因此不能按照約定陪父母。而在電影中最孝順的二兒媳紀子,為了陪公公婆婆去逛東京也要向自己的公司請假,這反而讓公公婆婆感到十分愧疚。即使是給觀眾感覺最不孝的二女兒繁,也有自己的苦衷,她開著美容院,沒有所謂的休息時間,只要客人上門就必須服務,且為了補償父母她也主動提出了出錢讓父母去熱海溫泉度假等。
而如果僅僅是將物哀停留在兩代人之間的矛盾上,那么《東京物語》還是不足以成為日本人心中20世紀最偉大的本國電影之一的。家庭僅僅是社會的小單位,但家庭也是受時代變革洗禮最明顯的一個社會縮影。電影拍攝于日本在二戰之后的恢復期,這也是日本從熟人社會(如平山周吉夫婦居住的鄰里之間互相問候的尾道)向市民社會(人們各忙各的,階層化已經逐漸形成的東京)的轉變時期。在這種轉變中,傳統的個體道德觀受到挑戰,而熟人社會正是受傳統道德約束的,工業化的入侵(電影中的工廠,紀子公司的米其林輪胎等都暗示了這一點)使人們不得不越來越麻木。這種時代洪流是令人悲哀的,也是無法抗拒的。老夫婦就意味著這個必將被遺忘的時代,承載著小津的哀嘆。
二、《東京物語》與幽玄美
幽玄美來源于日本古代文人對生活中種種不快、失意等情緒的審美,在藤原俊成、世阿彌等人的發展之下,幽玄美被發展成為從感官上升到精神的美,如和式的茶道、花道、能劇等都從不同的角度來展現幽玄美。而在文學和電影中,幽玄美則表現為近似禪宗的“不可說”“無即是有”,即以一種優雅的方式來表現一種深奧的、微妙難言的情緒,在表露的同時又有所遮蔽。正如世阿彌所指出的,用眼來觀察的是外行人,而用心觀察的才是內行人。在好萊塢敘事技巧大行其道的今天,小津對幽玄美的發揚無疑是別具一格的。在小津的電影中,跌宕起伏的情節以及直接剖露人物內心的語言經常是被舍棄的。情節看似死水微瀾,人物彼此彬彬有禮,語言內斂,不直接表露自己的情感,充滿暗示性,導演的鏡頭語言也十分婉轉,充滿暗示性。觀眾要想徹底了解導演的意圖只能“以心傳心”。
首先,就人物語言來說,電影中除了最小的女兒京子說話心直口快,在母親去世以后指責哥哥姐姐們失去了親情,表示自己以后絕對不要做這樣的人以外,其他所有的人說話都十分含蓄,一家親骨肉也在彼此的客套、禮讓中漸行漸遠。例如,繁是電影中一個類似于“丑角”的角色,其表情、動作都是幅度最大的,但是在語言上,當繁看到了提前回家的父母時,只是暗示自己安排了互助會,晚上會有其他人來家里。父母在聽到以后就收拾行李去了上野公園,默默等待太陽下山各自投奔他人。在電影中,即使是在喝醉的情況下,如處于“無家可歸”狀態下的平山周吉去找自己的好友服部先生喝酒時,在服部抱怨自己的兒子沒出息,羨慕周吉子女個個成功時,周吉也沒有表露自己的真實情感。又如在回家時,已經自感生命不長久的平山太太說的是“東京好遠哪”,而她來時說的則是“東京好近哪”,這位在整部電影中從未抱怨子女的老婦人以這樣含蓄的語言表露了自己對這次旅行的失望。
其次,就導演的鏡頭語言來說,小津在講述這個浸透悲哀的故事時,是以一種節制的語言來表述的。如平山周吉夫婦去到熱海時,原本他們沉浸在當地一片寧靜的風光中,但此時鏡頭中的遠景已經出現了來來去去的人影,而隨著夜幕的降臨,越來越多的青年男女來到旅館,并且開始打麻將、唱歌、尋歡作樂,甚至是進行肉體交易,吵得平山夫婦無法安眠。此時小津沒有直接表現夫婦兩人的煩躁,而是通過表現他們扇子扇風的頻率加快以及拍打蚊子等動作,告訴觀眾這一次旅行是他們想盡快結束的。又如,在紀子前去奔喪時,周吉家墻邊的一朵雞冠花反復出現在鏡頭中。一是因為雞冠花是在夏秋季開花,這表現了母親夏天去探望子女、秋天病故的時光流轉,此外,雞冠花的花語為永不褪色的愛,這也暗示的是無論子女如何對待父母,母親對他們的愛都不會改變。
三、《東京物語》與淡泊美
淡泊之美又可以理解為“閑寂”之美。在日本美學史上,將這種美感發揮到極致的代表人物便是“俳圣”松尾芭蕉,在松尾芭蕉的俳句藝術世界中不難看到,大自然之中的風花雪月等都可以激發審美主體的“有機的苦惱”。淡泊美與物哀美之間存在類似之處,但是相對于后者更偏重于對悲哀等情緒的詠嘆,前者便直接是一種與外物緊密聯系的悲哀與喜悅本身,并更強調人與外物的融合。正如松尾芭蕉在《笈之小文》中闡釋的:“然風雅者,順隨造化,以四時為友。所見之處,無不是花。所思之處,無不是月。見時無花,等同夷狄。思時無月,類于鳥獸。故應出夷狄,離鳥獸,順隨造化,回歸造化。”顯然,淡泊美并不停留在悲哀的境界,而是強調人在俗念的包圍下,應該盡可能地保留一種靜觀外物的態度,既能面對一年四季的風花雪月等自然風物,也能夠面對并不單純、浪漫的人生世相。在面對這些審美客體時,人的心態應該是孤寂而愉悅的,最終實現將人完全融入自然、物我合一的境界。
這種審美形態帶有非常明顯的孤絕感,在淡泊的背后實際上是一種空虛、寂寥和孤高。在《東京物語》中,紀子這一角色是淡泊美的替身。紀子生活在一種簡素而清貧的狀態中,在物質上,紀子的家是電影中出現的諸兒女家中最貧困的,在邀請公公婆婆前來的時候,紀子一再強調“如果不嫌臟就來吧”“很感謝你們沒嫌臟”。實際上紀子的家并不臟,但是卻最為逼仄簡陋,在招待公公婆婆的時候連酒都是向鄰居借的。心如枯井的紀子愿意在物質上過著一種最簡單的生活。而在精神上,在丈夫昌二生死不明的8年中,紀子無疑是孤寂的,但是她又是甘于、樂于堅守這種孤寂的。婆婆勸說她要是遇到合適的人,就改嫁吧,不然大家都會覺得很對不起她,紀子卻堅持不再改嫁。婆婆說:“當你老了以后,你會感到孤寂的。”紀子便說:“那我就努力不讓自己老。”這是在電影中始終溫柔、順從的紀子唯一一次沒有順著長輩意思的時候。紀子所珍視的是一種靜謐的、自我品味昌二點點滴滴的生活。盡管家中的一切都是會勾起人的感傷和凄然的,如婆婆提到的昌二睡過的床,公公婆婆一起看的昌二的照片等,但是紀子愿意用自己的下半生來維護這段感情的純凈和清澈。在婆婆死后,公公作為同樣失去了摯愛的人,將婆婆的遺物送給了紀子,這是小津借周吉對紀子身上這種淡泊美的肯定。
實際上,日本的傳統和式審美還包括諸多形態,比如“風雅”美等。眾多審美形態以及審美風格構成了一個復雜多元的日本藝術觀。即使是僅就《東京物語》這部電影而言,也完全有分析出其余和式美形態的可能。在表現日本的傳統審美方面,小津安二郎無疑是一位具有空前意義的導演。他高度重視日本的和式文化底蘊以及大和民族的精神品格,這些抽象而無處不在的意識被他以影像的方式具象化、可觸摸化,征服了在廢墟上重建家園的日本民眾,進而征服了世界其余地方的觀眾。在小津最為著名的電影《東京物語》中不難看出,小津擅長在表現當代日本人的平凡生活時,注入物哀美、幽玄美與淡泊美的和式審美,證明了電影的民族性是并不與世界性矛盾的。由小津所鞏固的這種日本古典美學傳統,也為后世的日本導演所繼承,并為中國導演也指出了一條可以借鑒的明路。可以說,小津安二郎對日本乃至同樣需要擺脫西方批評話語禁錮的東方電影美學,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