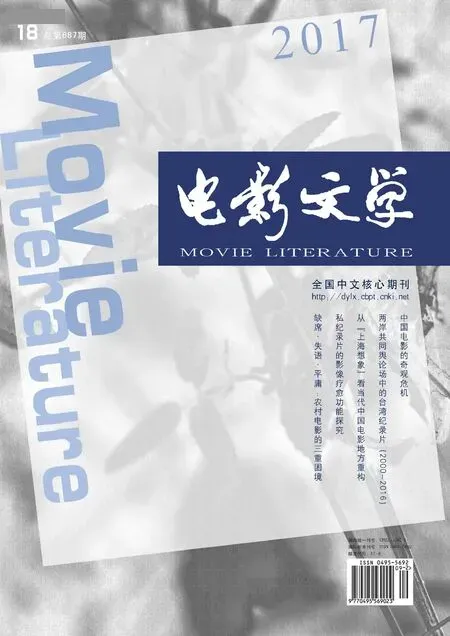《盛先生的花兒》:迷茫都市中的意志走向
欒莉舒
(吉林司法警官職業學院,吉林 長春 130000)
電影《盛先生的花兒》上映后憑借良好的口碑獲得2016年第19屆上海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獎。電影改編自美國華裔作家哈金的短篇小說《養老計劃》,講述了保姆棉花與得老年癡呆癥的盛先生一家人的故事。影片中棉花因不能生育的問題而被前夫拋棄,卻陰差陽錯地成了盛先生的保姆。在照顧盛先生的過程中,棉花與盛先生的人生交錯在一起。影片突出反映了女性在都市生活中的迷茫與堅強。同時,還引發了觀眾對男性社會責任與孩子內心真實需求的思考。
一、電影情節簡介
影片《盛先生的花兒》高度還原了原著小說《養老計劃》中的故事情節,講述了保姆棉花與盛先生一家之間的故事。出生在農村的棉花因不能生育而被丈夫拋棄。進城務工的棉花卻與自己的老板保持著曖昧關系。一次偶然的機會,棉花來到盛先生家,照顧患有老年癡呆癥的盛先生。在棉花照顧盛先生的過程中,盛先生一家的故事逐漸展現在觀眾視野之中。原來出錢請人照顧盛先生的女兒——盛琴,是盛先生拋妻棄子的孩子。盛先生插隊時與盛琴的母親相識相戀,卻在回城后有了新的家庭。為了城市里的兒子與妻子,盛先生拋棄了盛琴的生母。這也成為盛先生心中一直無法釋懷的隱痛。患有老年癡呆癥的盛先生甚至將棉花誤認為盛琴的生母——苗華,心心念念要與棉花結婚。而此時棉花也意外得知自己懷了情夫何順的孩子。盛先生的女兒盛琴卻以為棉花與自己的父親產生特殊情感。憤怒之下的盛琴逼著棉花墮胎,而逆來順受的棉花卻堅持選擇留下這個被醫生診斷可能會智障的孩子……影片將當代社會兩個較為敏感的話題(女性不孕與養老)融合在一起,將百姓的生活如實搬上大銀幕,用最真實的故事感染觀眾,用最積極的思想引導觀眾,引發觀眾對處于迷茫都市生活中的自己有了全新的認識與感知。
二、從人設角度分析都市人的意志走向
從電影《盛先生的花兒》的故事情節設計角度來看,影片情節樸素而真實,從人物安排角度來看,簡單卻具有各自的代表性。細數影片中的主要人物,每個人物都是當代社會中典型人群的代表。而片中主人公的故事發展,則體現出迷茫都市生活中人們精神以及意志的走向與選擇。
(一)棉花、盛琴——女性的獨立堅強與軟弱
棉花與盛琴兩位女性無疑是電影《盛先生的花兒》中重要的女性角色,兩位的人設也代表著都市生活中兩類典型的女性形象。隨著情節的發展,觀眾不難感受到女性的軟弱與獨立堅強。
棉花的形象簡單樸實,卻真實地反映了一個非常普遍的社會形象。來自農村的棉花因和前夫結婚多年不能生育而被丈夫趕出家門。內心感到恐懼與自卑的棉花選擇離開自己的家鄉逃避鄉里人對自己歧視的眼光。棉花的背景身份在影片中的設定則暗示并還原了當今社會中不孕女性受到不平等待遇的情況。而棉花的命運也正是大多數處于弱勢的女性的真實寫照。即使來到城市中的棉花似乎也逃脫不了內心的悲哀與恐懼,與自己的老板成為情人關系來尋找一份寄托感,即使本性善良單純的棉花知道情人是有家室的。然而自我認同感缺失的棉花卻對愛人的不忠選擇容忍與接受。棉花的“小三”身份是被社會所詬病的,然而觀眾卻無法對這樣一位女性產生過多的苛責。生性善良、吃苦耐勞的棉花可以全力照顧患有老年癡呆癥的盛先生,用一顆博愛的心去接受盛先生女兒的刁蠻與苛責,這都是這位女性身上的閃光點。當女性內心缺乏對自我的肯定與認知時,她們通常選擇將自己安置在相對安全的環境中,即使這份安寧是有悖于社會道德的。對棉花的遭遇觀眾不免投去同情的目光。然而棉花的轉變則讓觀眾感受到了女性內心的偉大與堅強。
當棉花得知意外懷上情人的孩子后,棉花的命運發生了逆襲與轉變。電影《盛先生的花兒》最經典的鏡頭莫過于棉花從醫院出來的場景。得知自己懷孕的棉花沖出醫院陰暗的走廊來到門口。棉花仰頭面對陽光,面部神情由恐懼轉向委屈,最終停留在燦爛的微笑上。棉花似乎終于走出了困擾自己多年的陰霾,心中那份禁錮已久的自信又重新拾回。當盛琴要求棉花打掉孩子、當情人威脅棉花選擇放棄、當醫生告訴棉花孩子極有可能為腦癱的情況下,棉花沒有選擇逆來順受,而是堅持生下了孩子。影片結尾,棉花離開情夫,帶著孩子和流浪的小狗回到自己的家中,面對滿地盛開的棉花,主人公棉花露出了幸福的微笑。而這個微笑背后則是棉花內心自我認同感的回歸。當然,從某種角度來說,棉花的救贖來源于孩子的力量。這暗示了女性的堅強需要憑借外力因素的推動,側面反映了女性處于社會弱勢的現實。
而盛琴的形象則是當代社會中另一類女性群體的代表。在影片中,盛琴的出現總是帶著對棉花的挑剔與苛責。從表面上看,盛琴風光無限,躋身上流社會。然而隨著影片故事情節的不斷發展,觀眾對盛琴有了更多新的認識。犀利刻薄的外表與語言僅僅是盛琴自我掩藏的盔甲。物質生活充實的盛琴其實是個被自己的親生父親拋棄的孩子;言語犀利的她同樣也是被丈夫背叛的女人;表面堅強的她也是一位被兒子埋怨的母親。無論作為哪個身份,盛琴都是不成功的。在父親臨終前,盛琴終于卸下自己偽裝堅強的外表,透露出內心的脆弱。而盛琴的形象則代表著社會中的一群女性,她們擁有光鮮的外表、充盈的物質生活,內心卻精神缺失,孤獨無助。當然,盛琴最終選擇放下對過去的怨念,重新生活,也展現了女性涅槃重生的勇氣與信心。
(二)盛先生、何順——男性的逃避與責任
在電影《盛先生的花兒》中,盛先生和何順(棉花的情人)的人物形象設計體現了劇作人對男性家庭責任感的思考。在棉花照顧患有老年癡呆癥的盛先生的過程中,盛先生口口聲聲念叨的都是盛琴的母親——苗華。甚至誤把棉花當成自己的妻子,總是半夜跑到棉花的床上與其一同睡覺。當盛琴與何順都逼著棉花打掉腹中孩子之時,一直將棉花誤認為妻子苗華的盛先生,卻明確提出要和棉花結婚。這甚至讓盛琴誤以為棉花肚子中的孩子是棉花與父親的孩子。然而,隨著盛琴說出父親曾為了同父異母的弟弟而拋妻棄子的往事,盛先生在晚年的那些奇怪舉動、口中重復的奇怪的對話也就都順理成章地解釋清楚了。
原來盛先生在年輕時,也曾犯下過拋妻棄子的錯,這份情感也成了他心中無法坦然面對與釋懷的愧疚。這也就解釋了為什么何順來到盛先生家要求棉花墮胎時,會被盛先生揍了一拳的原因了。與其說盛先生打的是何順,不如說盛先生教訓的是年輕時候的自己。
在影片中,何順的形象則代表著社會中那些沒有擔當與社會責任感的男性。何順因得知棉花沒有生育能力而放心大膽地與棉花保持著不正當的關系。利用棉花內心的自卑與逆來順受的性格,不負責任地玩弄棉花的感情。而當何順得知棉花懷上孩子后,膽小怕事的何順選擇犧牲棉花和自己的孩子,理由則是“我的老婆不會饒過我”。可見何順的無情與懦弱,缺乏身為男性的責任感。而影片在情節安排上的巧妙之處則在于,用患有老年癡呆癥的盛先生的行為與選擇來引導觀眾產生正確的價值選擇。
年輕時的盛先生與何順犯下同樣的錯誤,然而盛琴的母親——苗華,也像棉花一樣,堅強地生下了自己的孩子并撫養成人。時過境遷后,患有老年癡呆癥的盛先生放下了一切,卻對當初自己不負責任的行為悔恨萬分。盛先生在電影中的臺詞極少,卻句句停留在盛琴出生前盛先生與妻子苗華之間的對話中。面對奄奄一息的盛先生,棉花裝扮成了苗華穿著新娘裝的樣子,看到了“苗華”與自己成婚,盛先生最終也安詳地離開了。盛先生之所以能夠安詳地離開,是因為多年的悔恨終于釋懷。這便暗示了社會家庭責任感缺失的男性會隨著時間的流逝產生對自我的反思與救贖。在浮躁的當今社會,人們選擇將自己犯下的錯誤掩藏,卻無論如何也擺脫不了自己內心的譴責與反思。而盛先生的轉變則與何順的懦弱與責任感缺失產生強烈的對比,亦是對當今社會存在同樣問題的男性的諷刺與警醒。
(三)盛琴的兒子——孩子的需求與呼喚
在電影《盛先生的花兒》中,孩子的形象也同樣反映了當今社會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孩子的真實需求與呼喚。在影片中最明顯的線索則是盛琴兒子這個人物形象。物質生活豐厚的盛琴為兒子的生活提供了良好的保障,然而卻忽視了孩子內心最真實的想法。孩子的精神世界是極其敏感與脆弱的。
在影片中,盛琴的兒子僅僅出場了兩次。第一次出場時,盛琴的兒子戴著耳機,坐在電腦旁睡著了。當盛琴用寵溺的聲音呼喚兒子,拿下耳機,并告訴他明天和自己一同去姥爺家,孩子卻冷血地吼道:“要去你自己去,他太臭了。”而盛琴卻對孩子的回答毫無反駁。這不禁讓觀眾打了一陣寒戰:面對患有疾病的老人,本性純真善良的孩子卻變得沒有絲毫情感,僅考慮自身感受,哪怕是面對自己的至親。而作為一位母親,對孩子的反應卻不能給予正確的引導。第二次出場時,盛琴帶著父親、棉花與兒子一同來到騎馬場。當盛琴的兒子因為過于肥胖而不被允許騎馬時,盛琴與工作人員發生激烈爭執,而此時孩子又一次爆發:“我就是太胖了,你們從來都不知道關心我,張德順(盛琴的老公)也從來不回家……”隨后便甩手離去。
影片發展到這里,孩子的真實需求與呼喊引發了人們對孩子的情感教育的長時間思考。殷實的家境彌補不了父母給予孩子的陪伴;豐厚的物質條件填滿不了孩子孤獨的心。孩子本該是最單純柔軟的樣子,然而當孩子存在感缺失時,則會用最為簡單暴力的方式來引起大人的關注。而令人感到可悲的是,奔波在追求豐厚物質生活道路上的大人們,卻不能夠體會孩子內心最真實的渴求與呼喊。
在影片中,盛琴與盛鼓(盛琴同父異母的弟弟)也同樣是在這種社會環境和家庭背景下成長起來的孩子。為了盛鼓,盛先生拋棄了已經懷有身孕的苗華,陪伴盛鼓長大。然而當盛先生晚年得了老年癡呆癥后,陪在身邊出錢出力的卻是盛琴。甚至在盛先生彌留之際,盛鼓都沒有出現。背后的原因不難推測:終日活在對盛琴母女的愧疚與悔恨之中的盛先生,無法全身心地去陪伴盛鼓的成長,更缺乏對孩子在思想上的引導與培養,盛鼓對父親選擇放棄和抵觸。而盛琴的選擇則表現出在缺失關愛家庭中成長的孩子內心的另一種想法:從小沒有得到父愛的盛琴,任勞任怨,對父親的照顧無微不至,一直陪伴父親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路。因為她知道即使父母癱瘓或麻煩重重,孩子們最需要的,仍然只是父母的陪伴與關懷。
影片《盛先生的花兒》通過明暗兩條線索來反映當代社會中孩子的情感走向,體現出影片傳達的另一層主題思想——傾聽孩子最真實的心理需求,關注孩子的內心情感建設,重視孩子的德育與發展。
三、結 語
電影《盛先生的花兒》改編自美國華裔小說家哈金的短篇小說《養老計劃》。2016年11月4日在中國上映后,影片憑借良好的口碑獲得2016年第19屆上海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獎。影片將當代社會兩個較為敏感的話題(女性不孕與養老)融合在一起,將百姓的生活如實地搬上大銀幕,用最真實的故事感染觀眾,用最積極的思想引導觀眾,引發觀眾對處于迷茫都市生活中的自己有了全新的認識與感知。棉花與盛琴作為影片中的重要女性角色,代表著都市生活中兩類典型的女性形象,她們的意志走向體現了女性的軟弱與獨立堅強。而盛先生的轉變則與何順的懦弱與責任感缺失產生強烈的對比,亦是對當今社會存在同樣問題的男性的諷刺與警醒。最后,影片通過明暗兩條線索來反映當代社會中孩子的情感走向,體現出影片傳達的另一層主題思想——傾聽孩子最真實的心理需求,關注孩子的內心情感建設,重視孩子的德育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