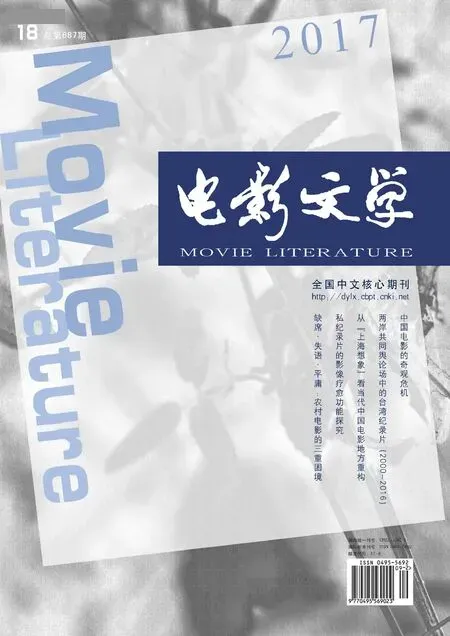倫理批評視域下的《太平輪》
張永軍
(河南交通職業技術學院,河南 鄭州 450000)
由吳宇森執導的影片《太平輪》以20世紀中葉中國戰爭年代為背景,以不同人物的視角,講述了動蕩年代之下小人物的不同選擇與命運走向。影片中的太平輪海難取材于真實的歷史事件,即1949年1月由大陸駛往臺灣的“太平輪”因超載與夜航撞礁沉沒,造成千人罹難。雖然這是一部以災難為題材的電影,但影片的敘事卻并未局限于此,而是以“太平輪”海難為引,將戰爭、愛情、家與國等命題融于其中,構筑了一個宏大的,既具有真實感,又富于詩意性的歷史空間。
很多評論者以歷史的真實與藝術想象關系的視角去探討《太平輪》拍攝的得失。而影片的戰爭背景、相對復雜的敘事線以及眾多的人物設置,加之海難這一并不突出的凝結點,增加了整個影片的敘事難度。對于觀眾來說,在把握與解讀上也就相對困難。但拋開宏大紛繁的史詩性敘事,單從倫理批評的視域去分析影片的人與事,卻能發現《太平輪》相對清晰的情感走向與敘事意圖。本文從影片的倫理命題及其具體表達形式出發,分析影片的審美特色。
一、苦難之下的生存
《太平輪》“大時代”背景的過于龐大反襯出生活在當時的人們的渺小,在這種背景當中,無論身處何種社會階層與生活境況中的人們,命運都有著一定的相似性,命運同樣不曾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是被時代所牽扯、激蕩甚至扼殺。因此,苦難是影片的主基調,面對苦難,不同人的生命選擇構成影片敘事展開的推動力。1949年的中國,政治與軍事格局漸趨明朗。而塵埃落定前的陣痛,卻是分外清晰和深重的。苦難不僅導致了個體的生存危機,也導向了人的道德困境。影片通過幾個不同階層與文化背景的主要人物,展現了這種困境,揭示了人性的復雜。
雷義方作為國軍將領,他在職責與愛情、生與死之間做出了艱難的選擇。在內戰爆發前,作為軍人的雷義方可以說達到了人生的頂峰。與日寇的對決中,雷義方率軍大獲全勝,在回到上海后,被擁戴為英雄的雷義方加官晉爵,在慈善舞會上他結識了大家閨秀周蘊芬,二人相互傾慕且一見鐘情,并結為夫婦。此時的雷義方可以說志得意滿,愛情與事業上都達到了令他滿意的程度。但內戰的爆發使雷義方的生活掉進了深淵,趕走日寇后,雷義方本來認為生活會歸于平靜,但他不希望看到的中國人打中國人的戰爭還是打起來了。作為軍人,服從命令是天職,雷義方只得投身戰場。在戰爭形勢越來越向對國民黨不利的一方傾斜時,雷義方做出了與大多數人同樣的選擇,讓自己懷有身孕的妻子周蘊芬乘船去臺灣。雷義方對妻子的愛是無私的,他將生活中美好的一面展示給妻子,卻從不把戰爭帶回家。但職責所致,他只能與妻子天各一方。當國民黨一方大勢已去,曾經的部下劉志清出現在雷義方面前,作為共產黨的代表,劉希望雷投降。但作為軍人的倔強和愚忠使雷義方放棄了與共產黨合作的機會,這一次他放棄了生存而選擇以死效忠。從雷義方對待手下逃兵的態度(放過逃兵讓他們回家)可以看出,他已經認清了時事,但愚忠使他明知上方無措的命令時仍舊執行。他殺死心愛的戰馬來填飽士兵的肚皮,足見其對手下人的珍視。這也促使了一批向他效忠的將士一起走向了死亡的結局。
于真作為漂流于亂世的善良女子,為了生存輾轉流離。白天作為看護戰士的白衣天使,晚上則淪為街頭攬客的廉價妓女。于真的漂泊是出于她對愛情的堅守,國民黨九旅五十五團的班長陽天虎與她在戰火中相愛,于真抱著一線希望在傷兵中苦苦搜尋。去做看護戰士的護士,并不能得到報酬,只能獲得夠糊口的糧食。但這樣的工作卻給了于真一個機會,那就是見到各個兵團的傷兵,從而找到陽天虎,或者知曉關于他的消息。在苦尋無果后,于真了解到傷兵大部分被運往臺灣,于是,她努力賺錢,希望獲得通往臺灣的船票。但是,目不識丁的她很難在混亂的上海找到工作。起初,于真找到了同鄉的夏珊,希望她幫忙介紹工作。夏珊建議于真去舞廳當舞小姐,但趕上了國民黨上海政府倡導節約,舞廳首當其沖被停業。于是舞小姐做不成了,無奈之下,于真淪落為街頭妓女,靠出賣肉體來賺錢。面對各色嫖客的踐踏和刁難,處于社會底層的于真只能忍氣吞聲。從對待饑餓孩子的施舍和對傷兵囑托的踐行,可以看出于真的善良,但個體的命運已經裹挾在時代的潮涌中,于真身不由己,去臺灣尋找陽天虎,成為支撐她活下去的信仰。
二、苦難之中的愛情
愛情是倫理批評中常見的審美客體。愛情以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和依戀為前提,是兩性關系的理想狀態。愛情既包括精神上的吸引與依托,也涵蓋了性愛上的滿足。在《太平輪》中,愛情是影片所表現的核心命題。在極端的生存環境之下,愛情作為一種精神支撐,賦予了人存活下去的勇氣和毅力。影片描述了幾個主人公對愛情的堅守,賦予了影片溫情的色調和濃郁的浪漫主義氣息。同時,《太平輪》所展現的愛情又并非僅限于兩性之間的情愛,而是包含了更多難能可貴的、超越了愛情的崇高情感。
首先來看于真弄假成真的愛情。于真放棄尊嚴、出賣肉體并非為了物質性的生存,而是為了尋找愛人。白天幫助受傷的戰士,也非出于民族大義,而是私利。但于真為一個垂死的陌生戰士所做的事情,卻超越了愛情的界限。雖然沒有轟轟烈烈的事跡,但其純潔與善良的品格卻清晰可見。在碰到佟大慶后,兩人照了一張結婚照。有了這張照片,佟大慶可以上報自己有家眷,從而冒領軍糧;而于真也可以憑借這張照片說自己是軍屬,從而擺脫單身女人的身份,為其在上海棲身提供方便。于真在拍照之后,不久就將佟大慶忘記了,而佟大慶則在戰友面前夸口自己與妻子(于真)在老家鄉下的幸福生活,在軍長雷義方的面前,他同樣撒了謊。但命運的遭際使于真和佟大慶再次相逢,在太平輪上,作為傷兵的佟大慶坐在甲板上,看著他與于真的合影,而于真則在傷兵中尋找陽天虎。飄飛的照片讓二人的命運再次匯流,視線模糊的佟大慶吵嚷著讓人幫忙找他和媳婦的照片,而于真則拾到了照片并與佟大慶相認。在太平輪沉沒過程中,于真與佟大慶生死相依、不離不棄,他們之間產生了真正的愛情。
嚴澤坤的愛情則是不為當時人所容的,是被指責的愛情。在日據時期的臺灣,嚴澤坤與日本女子志村雅子產生了真摯的情感。但二人的情感無論對于日本人,還是對于中國臺灣人來說,都是不被認同的。在日本進攻中國后,嚴澤坤被強制作為日軍軍醫充軍,他與雅子的愛情也被迫告一段落。在被國軍俘虜后,嚴澤坤再次回到臺灣,并繼承祖業成為一名醫生,但他對雅子始終無法忘懷。可以看出,在時代大潮的裹挾中,嚴澤坤更多的是身不由己,而雅子亦是如此。從雅子給嚴澤坤的信件殘存的片段中,可以窺見雅子對嚴澤坤的思念以及她在日本度日的艱難。而嚴母希望嚴澤坤娶自己長子的遺孀美芳為妻,這樣方便照顧孫子,嚴澤坤明白美芳對自己頗有情意,但自己心中已有雅子,再容不下他人。在沉船事件中,嚴澤坤為保護一個素不相識的小女孩兒而身重刀傷,在他瀕死之際,導演以寫意的鏡頭,讓嚴澤坤與雅子在一片殘陽照射下的如血一般的水域中見面,雖然生不能重逢,但死也要見到雅子,這為嚴澤坤被世人所指責卻仍堅守的愛情畫上了圓滿的句號。
三、《太平輪》倫理命題的表達方式
不同的電影創作者的倫理關注與倫理立場不盡相同。《太平輪》以大時代為背景,但并沒有過多波瀾壯闊的畫面,沒有英雄主義式的敘事,也沒有劇烈復雜的矛盾沖突,導演只是以一種樸素與內斂的方式,從容地書寫著普通人的生存困境。在表現影片不同的倫理命題上,導演吳宇森采用了多種藝術表現手段,使其成為一部頗具個人風格的電影作品。
首先,多線程敘事構成亂世浮世繪。吳宇森在汲取傳統敘事理論的同時,又運用了現代的敘事策略,讓電影在保證有一個清晰明了的主干的同時又有諸多微小事件,在事件的發展過程中暗合了觀眾的審美期待,使得觀眾對于《太平輪》所營造的影像世界具有高度的認同感。在電影中,貫穿始終的主題是亂世中的愛情,而這種愛情又分為三段,分別是雷義方、于真、嚴澤坤三人的情感。這樣,影片的主干就圍繞三人的愛情穿插展開。而戰爭、災難以及形形色色的人與事,則成為主干的補充。這種敘事的好處是,時代氛圍十分濃烈,人物所處的時空以異常清晰的面目呈現在觀眾面前。影片中的人物成為歷史的見證者與建構者,人物的形象由此有了敘事背景的依托,從而形成一種歷史的厚重感。例如,在雷義方的愛情主線中,時代背景成為其選擇的重要依托。當中日戰火正濃時,作為軍人的雷義方被人稱為“雷瘋子”,此時的他不需要愛情的映襯。而在日寇被擊敗后,難得的短暫和平時期,雷義方的愛情則實現了從萌發到瘋長。內戰爆發后,雷義方放棄了愛情而重返戰場,這是他作為軍人的義務。而親自沖鋒陷陣炸掉日軍彈藥庫、槍殺戰馬給士兵充饑、讓佟大慶給妻子捎去筆記本等事件,使雷義方的形象更加豐滿。在吳宇森的指導下,一個有血有肉的國軍將領形象呈現在觀眾面前。
其次,詩意內斂的敘事風格。電影中影像風格的詩意性被認為是導演“比較注意把畫面、鏡頭和蒙太奇的表現功能、抒情功能、敘述功能結合在一起”的產物,它使影像更“重抒情而輕敘事,重表現而輕再現,重主觀性而輕客觀性,并在藝術表現的境界上趨向于純粹、含蓄蘊藉、言有盡而意無窮的境界”。在影片中,最能體現詩意性的,就是嚴澤坤與周蘊芬來到海邊的橋段。周蘊芬在家中看到了一幅芒草中彈鋼琴的少女的畫作,并偶然發現了雅子的日記,于是,她約嚴澤坤來到海邊的燈塔旁,向他講明了真相。嚴澤坤看到雅子的日記后百感交集,他回憶起了與雅子的點點滴滴。影片以暖色調的鏡頭,講述了嚴澤坤和雅子的愛情故事。在充滿詩意的情調中,嚴澤坤與雅子相識、相戀,但戰火將二人分開,畫面也由此轉為冷色,嚴澤坤只能將對雅子的思念付諸筆端,彈鋼琴的少女的畫作也就此完成。雖然嚴澤坤和雅子的分別就此成為永別,但影片并沒有刻意煽情,而是以內斂詩意的敘事手法,帶給觀眾深沉的思索。類似的,影片最后殘陽下嚴澤坤與雅子的相見,也充滿了詩意和憂傷,在此不贅。
綜上所述,倫理學研究現實社會中各種道德現象,以及在社會活動基礎上形成的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道德關系和道德原則、規范,并用這些原則規范去指導人的行動。電影作為一種敘事藝術,通過藝術虛構,將現實生活轉變為藝術世界,但其并沒有脫離真實的社會,而是通過藝術處理,以獨特的視角,將現實中的各種道德現象轉化為藝術中各種道德矛盾與沖突,去揭示生活的真實。因此,電影能夠成為倫理批評的對象。以亂世與海難為底色的《太平輪》亦是如此。它既展現了特定環境之下的道德沖突,也是電影創作者道德思考形式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