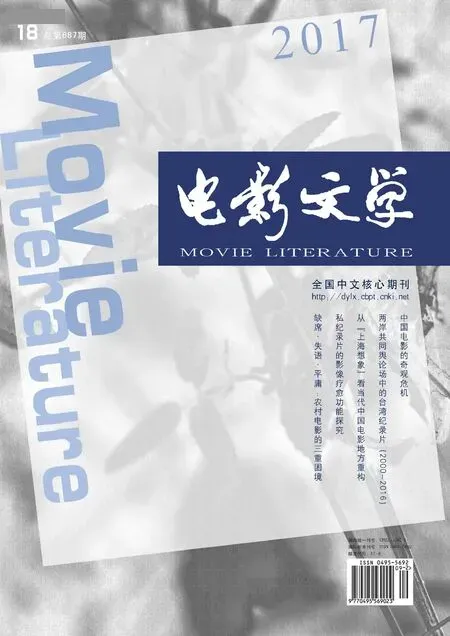電影《送鄉人》:西部空間書寫女性悲歌
平方園
(上海大學,上海 200444)
2014年,湯米·李·瓊斯自編自導自演的影片《送鄉人》,入圍戛納電影節主競賽單元。影片群星薈萃,由梅麗爾·斯特里普、希拉里·斯萬克和海莉·斯坦菲爾德組成的奧斯卡演員陣容引起極大反響,再加上呂克·貝松助陣制片人,為影片宣發及口碑帶來非凡的影響力。然而,交涉于多種因素,影片的殊榮在觀眾的視野中漸行漸遠。但在筆者看來,影片不管從敘事結構與故事編排,還是敘述視角與影像呈現等方面,都堪稱佳作。
從始至今,西部片成為盛產男性英雄的基地,塑造了一個個槍法如神、勇敢正義、頗具冒險精神、有著“神”一般的強健體魄與堅定意志的西部牛仔形象,無論是精神氣質還是外在服飾裝扮上,都在精心建構著“蓋世英雄”的神話想象。相較而論,西部片中的女性則長期處于邊緣狀態,基于歷史及創作者繁復建構等多種因素交織糅雜,其存在的價值在有意無意中忽視和淡化,并逐漸淡出觀眾視域。然而,在電影《送鄉人》中,導演完美逆襲傳統西部片的敘事模式,極富創造性地運用女性視角展開敘事,首次將女性設置為西部空間中的主角,加之戲劇化處理,女主角卡迪在影片后半場結束了自己的生命,由喬治·布里格斯來接替卡迪的任務,如此頗具震撼力的情節設置為女性命運增添了幾分悲愴色彩。此外,導演別出心裁地將荒蠻的西部空間外化為油畫般唯美、詩意,伴隨節奏緩慢、低沉的古典音樂演繹出一曲獨特的生命哀歌。可以說,卡迪以及三個瘋癲的女性是西部地區最為典型的范例,體現出來的精神特質構成典型的二元對立,卻不同程度地因為社會、自身、空間的因素造就了相似的命運悲劇。導演巧妙借助女性悲劇命運捕捉與展現女性的生存狀況及悲劇表征下的精神特質對男性的反思與救贖,更為突出的是,對促進美國民族性格的形成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
一、西部空間中的女性主角
在電影《送鄉人》中,導演一反常態地將女性推向銀幕中央,塑造出兩種性格鮮明生動而又引人注目的女性形象:一種是以卡迪為代表的“女漢子”式的女英雄,不僅具備英雄的獨立和勇敢特質,同時散發著極致的藝術氣息且對婚姻極度渴望;另一種則是三個精神異質的女性,極端不可救藥。不同性格特征及情感體驗促使女性突破傳統角色期待成為西部空間中的主角,也造就了她們的命運悲劇。
(一)堅硬的丑女人
電影《送鄉人》中飾演女主角卡迪的希拉里·斯萬克,憑借精湛的演技創造了奧斯卡史上屈指可數的摘取兩屆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獎的神話。在所飾演的電影《男孩別哭》《百萬美元寶貝》中都是以“男性硬漢”的形象在觀眾的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在電影《送鄉人》中,希拉里·斯萬再度演繹獨特的“硬線條”形象特質,將女主角卡迪的克制、剛烈、獨立和勇敢發揮到極致。可以說,精準的角色定位使得卡迪成為影片中最富有性格特色的女性,也是最能反映西部氣質的女性代表。
西部空間是影片敘事的主要場景,同時擔負著女性性格生成的機制。影片中卡迪以獨立、勇敢的女性形象出現在公眾視野,與荒蠻、逼入絕境的西部空間環境相得益彰,堪稱西部空間孕育下的女性英雄。從外表特征來看,臉形線條分明、緊蹙眉峰、眼神剛勁有力;在肢體動作的塑造上,對卡迪井旁提水的動作以夸張化處理,一腳接地,一腳騰空,雙手由上而下呈現最大的弧度,透露出她男性般的粗獷、干練和力量。在生產關系中,影片突破傳統生產關系中的勞動分工,把卡迪設置為勞動力的“主角”,遼闊惡劣的西部語境中卡迪只身一人在農田里耕地,勇敢地與荒蠻的西部地區環境做斗爭,同時將卡迪的男性化氣質刻畫得生動獨特。此外,從行為選擇上,卡迪主動承擔護送三個精神異質化的女性回鄉,面對惡劣的西部環境和路途中隨即可能遭遇的印第安人的威脅,卡迪還是迎刃而上,絲毫沒有退卻,充分體現了她超越常人的勇氣和氣魄。
然而,影片中的女英雄并非男性評價中“專橫”“獨斷”的負面形象標簽,而是一個富有藝術情調、渴求婚姻家庭的傳統女性。影片對卡迪的生活空間做了細節化處理,凸顯卡迪的獨特之處。影片中卡迪的房間布置是最具生活氣息的呈現,整齊簡約的家具擺設、桌子上白色的紗布、窗臺的盆栽、典雅的妝臺等,這些極具生活化的布景和道具賦予了觀眾對卡迪性格的想象。從另一側面來看,卡迪是鎮上唯一一個擁有手簧風琴的女性,音樂不僅是排遣孤獨的工具,也是卡迪藝術修養的外化。此外,導演對卡迪的年齡和心理夙愿以戲劇化處理,大齡單身而又極度渴求婚姻,巧妙借助三個精神異質的已婚女性作為參考對象,加速卡迪身份認同的焦慮感與挫敗感,為之后的悲劇命運埋下伏筆。
(二)美麗的瘋女人
相比“正常”的女性卡迪,三個精神異質的女性則是西部空間另一獨特的“風景”。時裝造型與容貌特征符合傳統視野對女性的期待審美。姣好的容貌如“天使般”美麗純情,又不失“女神”的優雅與高貴,具備真正的女性氣質,卻不同程度地陷入了瘋癲的狀態。外部視覺與心理扭曲的反差建構傳遞著導演的創作意圖和情感的深層次思考,試圖博得受眾意料之外的情感體驗。拋開直觀的視覺呈現,極端不可救藥則是同質性的表現。無論是迫于現實目標毀滅還是精神支柱的喪失,都采取一種頗為極端的方式來發泄自我絕望與煎熬,也成為悲劇命運的殺手锏。影片中年紀最小的蘇爾整日飽受喪子之痛的煎熬,拒絕與外界的一切交流,用失語的方式對抗殘酷現實。失語,相當于精神自殺,看似溫柔,也最極端;北歐女性格羅·斯文森則沉浸于蠟燭灼燒手掌、針尖刺扎全身的快感之中,在撕裂衣物、瘋亂咬人中反抗丈夫的百般性侵;瑟奧萊則是在牲畜和農作物都接連不斷死亡的刺激下,對現實生活感到深深的絕望,以至于把自己的新生兒扔在茅草坑里。這一行為并非“心狠手辣”而是對生活絕望之后不想牽連無辜,死亡或許比活著更好。
二、女性走向悲劇的泥潭
電影《送鄉人》中塑造的獨特的女性形象與西部環境的影響是密不可分的。惡劣的西部空間環境造就了她們在西部地區呈現出來的獨特精神氣質。在西部荒無人煙的蠻荒之地,不管是獨立的卡迪還是精神異質的女性都成為西部環境的犧牲品,也是構成女性悲劇的客觀原因,而女性飽受男性褻瀆而產生的絕望也是不容忽視的主觀因素。
(一)惡劣的西部空間
荒蠻的西部空間是推動影片敘事的重要角色。詩意盎然而又奇觀化的空間造型完成觀眾對西部的想象。而歪扭、變形、破舊的建筑物以及漫天黃沙、層次分明的地平線等空間內部形態真實再現,也是女性悲劇命運生成最為直接的熔爐。
電影《送鄉人》中,西部空間構成人物主要的活動場所,擔任著塑造人物形象不可或缺的精神載體。影片開始,多組空鏡頭連續疊加出現,不僅是西部環境的一次唯美景觀呈現,暗示著敘事發生的場所及與人物將產生的互動與摩擦。影片中,卡迪笨拙地使用簡陋的鐵犁在農田里驅牛耕作,借用廣角鏡頭將女性與西部環境緊密聯系到一起,暗喻環境與人物的關系;鏡頭緊接著從下面耕作的鐵犁特寫慢慢移向卡迪臉部的特寫,由此來暗指惡劣空間影響下,女性在西部空間中生存狀況的艱難,并對卡迪的悲劇命運做了鋪墊。“在影片的敘事中,空間其實始終在場,始終被表現。”①可以說,空間與敘事是不可剝離的一個整體。空間是構成人物行動的場所,也是人物走向悲劇的間接利器。在影片中,卡迪在整理被印第安人毀亂的墳墓后,踏入了尋找“伴侶”布里格斯的征途,此次的尋找是卡迪與西部環境最為“親密”的接觸。其中,運用全景的形式,將人物置身于空間環境中,以空間環境為背景,突出卡迪的渺小、無助和掙扎。深黑的夜色、寒風呼嘯、紛紛雪花、逆風、枯萎的野草,天空的明暗變化等空間意象無形之中為環境的惡劣做了鋪墊。卡迪在找到布里格斯之后號啕大哭,暗示著西部荒原環境給卡迪帶來生理和心理雙重折磨已經達到極致。在這種情況下,卡迪不惜做出了喪盡尊嚴的求婚舉動,而且也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法國哲學家吉爾·德勒茲說,影像并不只為了被觀看而存在,它不僅可以被視見,同時是可閱讀的。”②影片中對西部環境的惡劣采用隱喻的方式表達,殘酷的外部空間環境作為人們賴以生存的空間場所,同時,也給影片中的女性命運蒙上一層悲劇色彩。卡迪及三個女性為代表的拓荒者,背離文明的東部來到荒蠻的西部空間,謀求生存是西部環境中最為本能也最為突出的生活目標,此種情景中,作為生存之本的農作物存亡對生活顯得尤為重要。從瑟奧萊的境遇來看,牲畜與農作物在惡劣的西部環境下頻繁死亡,她在無法接受又無力改變的情況下而瘋癲。農作物和牲畜作為維持生活必不可少的物質基礎,尤其是在19世紀中期物質貧乏的年代,農作物的死亡意味著物質資料的毀滅。此外,牲畜也是作為生活資料買賣的必需品,擔任獲取經濟來源的重要通道。牲畜的死亡意味著經濟來源斷送,在生活與經濟的雙重打擊下,作為弱者的女性群體成為直接的受害者。從而暗喻女性在現實生活破裂之后的悲慘命運。
(二)男性對女性的褻瀆
惡劣西部空間環境促使女性褪去與生俱來的精神氣質與男性審美期待。在生產力低下、勞動力極具需求的西部地區,婚姻與家庭的功能延伸對于生存來說尤為重要。此外,女性從屬地位及天然弱者形象,都在無形之中飽受男性的褻瀆,喪失生活的信心與勇氣,從而走向悲劇的泥潭。
19世紀50年代,美國舊西北地區的生存環境異常惡劣,農業機械設施簡陋,純粹依靠手工勞作和體力勞動成為生產資料運作的主要方式,土地、自然生長的植被、獵物作為獲取生活資料的基本。此種情境中,求生的本能作為個體在西部空間存活的必要因素,傳統性別分工的界限被打破,延展分裂了女性傳統的角色使命,成為家庭兼具男性勞作的輔力。日積月累的煩瑣內務及西部空間下的艱辛勞作,促使女性漸驅褪去建立在男權之下的女性氣質規范。毫無例外,影片中女英雄卡迪展現出的特質與西部地區的需求相得益彰。然而,在19世紀中期獨特的歷史語境中,男性較青睞于具備真正女性氣質的女性,粗線條“女漢子”式的卡迪與男性的審美期待背道而馳,成為小鎮上男性望而生畏的對象。影片中,極度渴望婚姻的卡迪對鮑勃主動出擊,卻遭到鮑勃的諷刺和輕視,并對卡迪的品格給予否認,再次觸痛卡迪長久不被認可的心理屏障,促使卡迪對婚姻近乎絕望,并對小鎮上的男性不再抱有期望。也就不難理解卡迪“主動求婚”有悖于男性的主流認同,不符合當時男性對女性的角色期待,也是其悲劇命運的一個節點。
對小鎮上的男性極度失望之后,卡迪把新的希望投注于外來者布里格斯。影片中布里格斯是以小鎮上罪惡的“闖入者”身份出現的,他是卡迪得力的“助手”。他的出現,重新點燃了卡迪對男性的期待。影片中,卡迪第一次帶布里格斯回家的情景,卡迪在房間內透過鏡子凝視外面的布里格斯洗臉,運用主觀鏡頭將兩人洗臉的行為對接在一起,在鏡像的作用下,將主觀視角以客觀形式呈現,充分映射出卡迪對布里格斯的期待。送鄉途中,卡迪主動尋找話題,試圖拉近與布里格斯的距離,想方設法來感化布里格斯,在行程即將結束之時,再次喪盡尊嚴地向布里格斯求婚。盡管卡迪百般勸說,布里格斯還是堅決否決,再加上獨自在荒原中尋找布里格斯承受的折磨與煎熬,終于掐斷了卡迪最后一根稻草,百般絕望之中,卡迪決定獻身來突破不斷被否定的格局與需求,并為此付出生命的代價。
有關西進運動兩性關系的研究中,“法拉格認為婦女是被剝削的、屬于從屬地位而且是無權的”③。由此可見,拓荒時期的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并未得到認同,自我認知能力模糊,是男權社會下純粹的附庸品。影片中北歐女人格羅·斯文森的命運悲劇來自于與其朝夕相處的丈夫,她長期受到丈夫的性侵犯,丈夫把她當作生育的工具肆意褻瀆,不管是與母親共處一室,還是在牛羊圈內,都會對她展開喪盡尊嚴的性攻擊與侵犯。而她缺乏獨立的自我意識,一味地委曲求全、唯命是從,不知反抗,任由丈夫肆意地侵犯。在這個意義上,影片借助母親的主觀鏡頭來審視斯文森“被侵犯”的行為,圈養牲畜的場所則暗指丈夫把斯文森當作牲畜一樣不加尊重地隨意侵犯,從而對丈夫徹底絕望,以瘋癲對抗對婚姻生活的不滿。從她的遭遇來看,她的悲劇實際上是西部地區女性群體的范例,也是拓荒時期女性命運的經典寫照。
三、女性命運悲劇的意義
導演湯米·李·瓊斯最大力度地將拓荒時期的女性推向了美國歷史舞臺的中央,并且挖掘了一系列富有精神氣質而又不可超越的女性形象。力圖再現西部空間中女性的遭遇,來肯定西部空間下女性的精神氣質對男性的影響與熏陶,以及美國民族性格的塑造產生的深遠影響。
(一)被救贖的男性
影片中的主角卡迪在后半場意外死亡,如此獨具一格的敘事模式在電影作品中實屬少見,而這也正是影片脫穎而出的魅力所在。卡迪的死亡并不意味著敘事的停止,故事的結束,恰恰是故事的開始,也是卡迪精神氣質產生影響的關鍵環節。影片中卡迪離開,后半場的敘事交由影片“第二主角”布里格斯來支撐,并把三個精神異化的女性如約送到了愛荷華州,布里格斯也借此完成了自我的成長與救贖,從而對女性群體表現出深切的關懷,充分反映出卡迪的精神品質對布里格斯帶來的深刻影響。影片中,在食物缺乏、無法保證三個女性溫飽的情境中,布里格斯把希望投注在旅館老板身上,不料遭到老板的拒絕,并對三個精神異質的女性冷嘲熱諷,如此不尊重女性的行為,為之后布里格斯放火燒掉旅館做了鋪墊。此外,布里格斯為赤腳的女服務生買鞋、為卡迪買墓碑,都傳達著對女性的深切關照。與此同時,從墓碑上的字——“親愛的瑪麗比·卡迪,上帝愛她,請帶她回到他身邊”和旅館女服務生的交談中布里格斯對卡迪的評價“她是世界上最棒的女人,可惜你已沒機會再見到她了”“你就是那個讓她活生生存在的理由”中,卡迪的精神品質最終得到接受與認可。然而,卻以生命為籌碼,無形中蔓延而來的悲哀再次宣揚著卡迪存在的意義與價值,謳歌頌揚了以卡迪為代表的女性群體的力量,讓男性重新審視自我行為的漏洞,改變以往對女性的認知與論斷,對女性進行了全新而又深刻的讀解。
(二)促進美國民族性格的形成
經久不息的西部片源源不斷地流淌著美國精神的血液,成為傳遞美國精神的寫照。西部片中對男性的塑造更是如此,勇敢正義、英雄情結、開拓荒野、征服自然等力量和氣魄把美國精神演繹得淋漓盡致。同樣,作為西部電影的《送鄉人》也不例外,盡管影片中借助女性來建構英雄神話,把女性推向西部空間的中心,除性別差異之外,影片中女性卡迪所體現出來的精神內核與西部男性英雄如出一轍。在惡劣的西部空間環境及近乎原始的生存背景下,鑄就了以卡迪為映射的、特別能反映出美國獨立精神的群體力量,憑借驚人的勇氣和不折不扣的信念主動挑起送鄉的重擔,與西部地區勇敢地抗爭,不惜付出巨大的犧牲。作為一個形單影只的女性,獨自應對各種困難和挑戰,在生產力極其落后、生產工具有限的情況下,運用自我力量收獲每一份良田,將生活裝飾得猶如田園般詩意,并將東部文明孕育下的無私、善良的品質融入西部空間之中,不惜付出善良與愛心溫暖每一個體。除此之外,以卡迪為代表的西部女性身上所體現出來的個人主義、平等及獨立意識,都不約而同地滲透到美國人的血液之中,并深刻影響著當今美國人的行為習慣和價值取向。可以說,這樣的性格和精神品質是美國人性格形成的重要源泉,也是美國歷史進程中具有深遠意義的精神文化遺產。
四、結 語
電影《送鄉人》以獨特的女性視角對19世紀美國拓荒時期的女性進行了一次全新書寫,以卡迪以及三個女性的悲慘命運為出發點,反思西部空間語境下女性真實的生存語境,并對女性的命運給予一定的觀照,從而表達出深切的人文關懷。更為重要的是,積極肯定女性在拓荒時期的貢獻與價值,以及反映出的精神特質對美利堅民族性格的建構,乃至當今美國的繁榮發展有著不可忽視的意義與影響。
注釋:
① [加]安德烈·戈德羅、佛朗索瓦·若斯特:《什么是電影敘事學》,劉云舟譯,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第107頁。
② [法]吉爾·德勒茲:《電影1:動作—影像》,黃建宏譯,遠流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46頁。
③ 鄢可然:《19世紀美國西部婦女地位研究》,復旦大學,2002年。